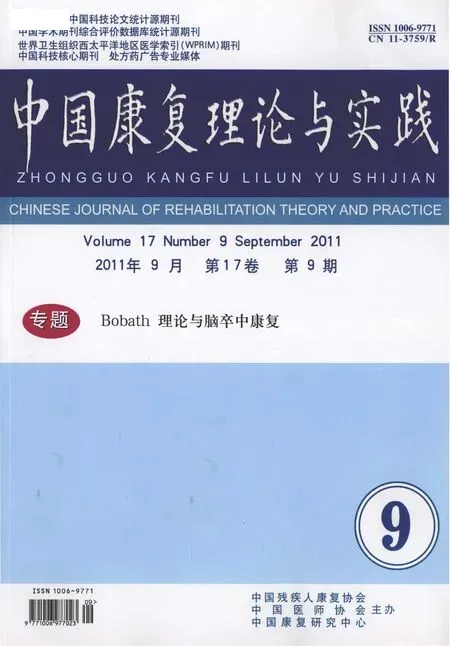地塞米松對內毒素休克大鼠腦組織細胞因子含量的影響
王新芳,張宇忠,任麗薇,賈旭,龐丹丹
感染性休克是臨床上常見的危重病癥,細菌內毒素和由內毒素刺激單核-巨噬細胞等釋放過量炎癥介質是該型休克的主要發病機制。微循環障礙仍然是目前解釋休克發病機制的主要學說,其中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和代償性抗炎反應綜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平衡失調是學術界的共識。探討休克發生發展中產生的各種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作用是闡明SIRS和CARS的關鍵[1]。與感染性休克有關的炎癥介質的研究資料主要涉及血液的各種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
雖然感染性休克是一種可能累及多器官的全身性炎癥反應,但往往依據病情嚴重和處理方法的不同表現出器官的選擇性損傷。肺臟和腎臟是最易受損傷的器官,心腦在一定條件下也易發生損傷性變化[2-4]。本課題組以往的實驗已發現,休克病程中腦損傷的發生是一個關鍵事件,腦組織局部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過量產生在腦損傷起關鍵作用[5]。本實驗觀察腎上腺皮質類藥物地塞米松對內毒素休克大鼠的平均動脈壓(MAP)和腦組織含水量的影響,同時測定腦組織白細胞介素-4(IL-4)、白細胞介素-10(IL-10)以及TNF-α的含量,探討休克病程中腦組織局部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與腦損傷相關的變化規律以及皮質激素在防治內毒素休克腦損傷中的保護作用與相關機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實驗動物 54只健康成年Sprague-Dawley大鼠,雌雄各半,體重180~220 g,由北京維通利華實驗動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合格證號:ZCXX(京)2008-0003。
1.2 試劑與儀器 內毒素(E Coli O 127B8):SIGMA公司;地塞米松注射液:北京雙鶴藥業有限公司,批號311818A;水合氯醛:北京化學試劑公司,批號20050528;IL-4、IL-10、TNF-α測定試劑盒:武漢博士德公司;BL-420E+生物機能實驗系統:PHILIPS公司,MP20/junior。
1.3 動物分組和實驗方法 54只大鼠隨機分為3組:假手術組、脂多糖組、地塞米松組,各18只,每組再分為休克后1 h、3 h和6 h組3個觀測點,每個觀測點6只大鼠。各組動物不足時,隨時補充。實際補充44只大鼠。參考文獻[5],手術時所有動物用10%水合氯醛0.35 ml/100 g腹腔麻醉,分離左頸總動脈,插入肝素化PE50管,與三通管連接,并經YH-100型壓力換能器與BL-420E生物機能實驗系統連接,監測MAP。分離右頸外靜脈,穿線插入肝素化PE50管后接輸液裝置。動物血壓穩定后開始實驗,每10 min記錄1次血壓,直至6 h實驗結束。假手術組給予生理鹽水20 ml/kg,脂多糖組給予脂多糖8 mg/kg,地塞米松組給予脂多糖8 mg/kg+地塞米松5 mg/kg。靜脈輸注脂多糖后,以MAP比基礎值降低25%~30%作為急性內毒素休克模型成功的標準。在模型成功10 min之后,地塞米松組給地塞米松。總輸液量控制在20 ml/kg。
1.4 取材 各組動物斷頭取腦,選取左側大腦中部皮質,用生理鹽水冰浴勻漿,4℃ 900 g離心10 min,取上清制備為10%勻漿,-70℃保存待測。
1.5 觀察指標 記錄動物一般情況及存活率,并觀察以下項目。
1.5.1 MAP 以注射生理鹽水或脂多糖之前為0 h,記錄0 h、l h、3 h、6 h時間點的血壓。
MAP=舒張壓+1/3脈壓。
1.5.2 腦組織含水量 取左側大腦皮層組織約100 mg,用電子天平(分度值<0.l mg)稱取標本濕重;恒溫電烤箱105℃烤2~3次,每次24 h,直至兩次標本干重相差小于0.2 mg,即恒重為止。
腦組織含水量=(濕重-干重)/濕重×100%。
1.5.3 TNF-α、IL-4、IL-10測定 采用ELISA法,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
2 結果
2.1 動物一般情況及存活率 假手術組動物一般情況良好,呼吸平穩,四肢溫度正常,實驗前后無明顯變化;脂多糖組動物在注射內毒素后即出現呼吸急促、口唇紫紺、體溫下降、四肢厥冷、寒戰;與脂多糖組相比,地塞米松組動物呼吸急促明顯減輕,有萎靡、腹瀉、豎毛表現。地塞米松組各觀察點的死亡率均低于脂多糖組,其中6 h時脂多糖組死亡率83.3%,地塞米松組死亡率53.8%,低于脂多糖組(P<0.05)。
2.2 MAP 假手術組MAP無明顯變化。脂多糖組MAP在注射脂多糖后迅速下降,30 min內有所回升,于90~120 min后逐漸緩慢下降,直至死亡。地塞米松組血壓降低程度明顯減輕(P<0.05)。
2.3 腦組織含水量 休克6 h時,脂多糖組腦含水量較假手術組增加,地塞米松組腦含水量低于脂多糖組(P<0.05)。見表1。
2.4 腦組織IL-4、IL-10和TNF-α含量 與假手術組比較,脂多糖組腦組織TNF-α含量在1 h已升高(P<0.05),3 h和6 h升高更明顯(P<0.01);與脂多糖組比較,地塞米松組腦組織TNF-α含量在1 h時有降低趨勢,3 h和6 h降低(P<0.05)。與假手術組比較,脂多糖組3 h和6 h時腦組織IL-4、IL-10含量明顯降低(P<0.01);與脂多糖組比較,在3 h和6 h時地塞米松組IL-4、IL-10含量明顯升高(P<0.01)。見表1。
3 討論
本實驗復制大鼠內毒素休克模型,觀察地塞米松對動物生命體征的作用以及與腦組織細胞因子水平改變的關系,以期了解感染性休克腦損傷以及激素抗休克發揮腦保護作用的病理生理特征。
內毒素是感染性休克發病機制中主要致病因子,MAP是反映休克最有效的血流動力學指標之一。本實驗中,注射脂多糖后,開始5 min MAP下降至基礎血壓的20%,30 min時血壓略有回升,至240 min時血壓持續下降,未見回升,表明我們成功復制了內毒素休克模型。
內毒素休克模型是目前最接近臨床感染性休克患者病情的動物模型[6]。內毒素能否通過血腦屏障,一直存在著不同見解,目前仍不能排除大劑量內毒素或腦內疾病削弱血腦屏障時,內毒素直接作用于腦神經元的可能性。目前多數學者認為,隨著感染性休克引起的腦缺血、缺氧和腦能量代謝障礙的出現,離子泵功能失調,鈉、氯離子大量從細胞外進入細胞內,導致腦細胞水腫,血管源性腦水腫是感染性休克腦損傷的主要病理變化。血壓下降是休克引起各器官缺血、缺氧以至微循環障礙的主要機制,而各型休克中后期血壓均已明顯下降,故可把監測MAP作為了解休克病情最有效的血流動力學指標之一。
感染性休克時血壓下降和腦微循環障礙的分子機制可從信號傳導和抗損害因素角度總結為兩方面。
脂多糖首先引起炎性介質的過量釋放,這些炎性介質中有些是促炎介質,另一些是抗炎介質;合成和釋放這些炎性介質的第1類效應細胞應該是血液中的單核-巨噬細胞,它們是脂多糖最初作用的靶細胞[7]。本實驗中,脂多糖組動物腦組織TNF-α含量在1 h已明顯升高,3 h和6 h進一步成比例升高,且與腦含水量變化相一致。相對于大分子脂多糖,血液中升高的TNF-α更容易透過血腦屏障。至于腦組織局部神經細胞、膠質細胞、微血管內皮細胞是否也產生TNF-α;如果產生,是對脂多糖的直接反應還是僅僅作為最初的促炎介質TNF-α的第2類效應細胞繼發性生成,尚不能詳細區分。但可以肯定,腦組織局部促炎介質TNF-α的含量顯著增加在脂多糖引發的腦損傷中是最重要的受體前信號。理論上,上述促炎介質的相應受體在功能和數量方面也會有相應的變化,但這方面研究資料不多。

表1 每組各時間點觀測指標比較(n=6)
從抗損害因素角度看,主要是血液單核-巨噬細胞和腦內各細胞對以TNF-α為代表的促炎介質的代償性失調。當病情輕微時,適當水平TNF-α的反應性升高可以通過相應水平抗炎介質的生成而維持促炎介質和抗炎介質的平衡。但當病情危重時,TNF-α的病理性升高則不能引導靶細胞合成釋放足量的抗炎介質來對抗促炎介質對腦組織的損害性作用[8]。本實驗中,脂多糖組動物腦組織IL-4和IL-10含量在1 h已明顯下降,3 h和6 h進一步降低,也與腦含水量變化相一致。IL-4和IL-10作為主要的抗炎介質應該主要在腦局部起保護作用。IL-4和IL-10的合成細胞可能包括腦內主要的細胞類型,如神經細胞、神經膠質細胞、微血管內皮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等。本實驗顯示,除腦局部TNF-α大量生成外,抗炎介質的大量減少也是造成內毒素休克腦損傷的另一原因。
感染性休克中發生的腦損傷相當于臨床上的膿毒性腦病(septic encephalopathy,SE)。SE目前無特效治療,預后較差[9]。糖皮質激素可誘導脂皮質蛋白生成,抑制磷脂酸A2、抑制單核-巨噬細胞產生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謝物,抑制IL-1β和TNF-α等細胞因子的產生,在多種腦病中通過抑制炎癥介質合成及炎癥細胞活性,穩定溶酶體,修復血腦屏障等起重要作用[10]。以往有報道顯示,激素可加重腦炎癥反應[11];也有研究表明,激素可減輕腦水腫及神經元損傷,但對炎癥反應無明顯作用[12]。本實驗中,地塞米松表現出良好的抗炎、抗休克作用。與脂多糖組比較,地塞米松組促炎介質減少、抗炎介質增加,起到了調節炎性介質平衡的良好作用。
[1]尹旭,張宇忠,楊瑩.四種炎性遞質與休克的關系[J].中國全科醫學,2010,13(3C):1014-1018.
[2]van Amersfoort ES,van Berkel TJ,Kuiper J.Receptors,mediators,and mechanisms involved in bacterial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Clin Microbiol Rev,2003,16(3):379-414.
[3]Fitch SJ,Gossage JR.Optimal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rapid re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 of therapy are crucial[J].Post Grad Med,2002,111(3):53-64.
[4]Cavaillon M,Adib-Conquy M,Fitting C,et al.Cytokine cascade in sepsis[J].Scand JInfect Dis,2003,35(5):535-544.
[5]張宇忠,吳海燕,任麗薇,等.加味生脈飲注射液對內毒素休克大鼠腦組織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α含量的影響[J].世界中醫藥,2010,5(4):289-291.
[6]Fink MP,Heard SO.Laboratory models of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JSurg Res,1990,49(2):186-196.
[7]Dellinger R,Carlet J,Masur H,et al.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Crit Care Med,2004,32(3):858-873.
[8]Dellinger RP,Levy MM,Carlet JM,et al.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J].Crit Care Med,2007,36(1):297-327.
[9]陳弘,盧洪洲.糖皮質激素在治療感染性休克中的應用[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2009,29(7):656-658.
[10]Margriet M,de Jong FC,Beishuizen A,et al.Relative adrenal insufficiency as a predictor of disease severity,mortality,and beneficial effects of corticosteroid treatment in septic shock[J].Crit Care Med,2007,35(8):1896-1903.
[11]Ho A,Al-Musalhi H,Chapman M,et al.Septic shock and sepsis:a comparison of total and free plasma cortisol levels[J].JClin Endocrinol Metab,2006,91(1):105-114.
[12]Sprung CL,Annane D,Keh D,et al.Hydrocortisone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J].N Engl JMed,2008,358(2):1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