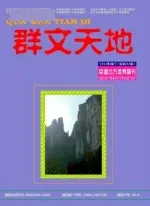淺析杜甫詩歌的“風骨”美
■李清娟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中提出的“風骨”理論尤其被后人所重視。初唐時期,陳子昂倡導“漢魏風骨”,并且對“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齊梁頹靡詩風持反對態度;盛唐時期,李白“雄渾豪放”和杜甫“沉郁頓挫”的詩風對“風骨”理論又加以闡釋。他們為“風骨”在唐代甚至后代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盛唐時期是中國詩歌文化發展的最高峰,其對“風骨”的發展具有唐代獨特的時代精神。特別是“詩圣”杜甫,由于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生活環境和人生際遇,形成了他獨有的創作風格,在詩歌內容、創作語言和創作思想上都對“風骨”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總之,唐代詩人對推動“風骨”的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唐代詩歌獨有的“風骨”之美。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也是我國歷史上對百姓最關注的詩人之一,他崇尚“凌云健筆意縱橫”,是當之無愧的“風骨”繼承者和發展者。杜甫論詩贊揚“骨氣”、“骨力”,內容上要求抒寫現實,關注百姓疾苦,批判統治者的昏庸,旗幟鮮明地繼承了《詩經》和漢魏以來詩歌的慷慨之氣,發揚了劉勰的宗經、崇古思想,反對綺靡的詩風。杜甫的詩,不僅內容極為豐富,而且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杜詩中充溢著熱愛祖國和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的詩被公認為“詩史”,無論是詩的內容還是創作思想,無不體現著“風骨”的魅力。
一、從杜甫詩歌內容看其對“風骨”的繼承
從杜甫詩歌的內容上看,他不僅寫宴游詩、山水詩,而且寫羈旅詩、詠懷詩,更重要的是,杜甫用他的詩,記敘了安史之亂時很多的重要事件,寫了人民在戰爭中所承受的苦難,用生動飽滿有血有肉的形象,展現了戰亂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因此,杜詩被稱為“詩史”,對史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很多為人所知的歷史事件,在杜詩中都有反映。風骨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文章思想內容要充實,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這也是“骨”的具體體現,而杜甫的詩歌不僅是對客觀世界的描述,而且融入了他個人強烈的思想情感。從杜詩中,我們看到了四個字“為民請命”,即儒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
杜詩不僅廣泛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反映出各個階層的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遇的苦難;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中的黑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在這首詩中夾敘夾議,表達了錯綜的內容和復雜的情感。在《麗人行》中,他先描繪麗人體貌、服飾,然后由“就中云幕椒房親”轉到描寫楊氏姊妹的窮奢極欲上,與她們的外表形成鮮明對比。在《春望》中,他表達了對國破家亡的深憂巨痛,是傷春感時,更是對國家對人民的深切憂慮。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愿,并寧愿以“凍死”來換得廣大饑寒士人的溫暖,這種崇高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杜甫的詩歌是極具內容的,并且內容豐富,劉勰在論風骨時提到:“捶子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文心雕龍·風骨篇》)可以看出劉勰反對內容貧乏、空洞且辭句堆砌冗長的作品。而杜甫在創作中正是避免了這樣的缺陷,從而具有“風骨”之美。
二、從杜甫詩歌創作的語言看其對“風骨”的繼承
從杜甫詩歌創作的語言上看,他在煉字煉句上是相當成功的。“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文心雕龍·風骨篇》)在劉勰看來“風骨”和“采”都是很重要的,如果“風骨”乏“采”,就會象鷹隼那樣,雖能翱翔于天,卻因沒有采羽,不能逗人觀賞。如果“采”乏“風骨”,就會象野雞那樣,雖然好看,卻不能高飛,只有“風骨”和“采”兼具,能披著絢爛的文采在高空翱翔的,才可以稱為文章中的鳳凰,達到理想的境界,才會產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當然“風骨”和“采”仍然是有主次問題的,他認為“采”只能是“風骨”的補充,為“風骨”服務,不能主次顛倒。杜甫在語言上精于用字,刻畫細微,運用了多種表現手法,但并沒有影響詩歌的“風骨”,反而是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他煉字的獨到之處在于表現人的神情韻味,運用動詞使整個詩句充滿生命,運用副詞使詩句婉轉而疏暢,運用顏色字來強化情感色彩,運用雙聲疊韻以使詩的聲調更加和諧悅耳,運用俗字口語使詩的內容更加貼近生活。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全文章法、句法、字法嚴謹,但法極無際,曉暢自然。這首詩不僅純熟的運用格律,更可貴的是詩中用字極為準確生動,寫得繪聲繪色,作者欣喜之情躍然紙上,“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再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句既是當句對又是流水對,“巴峽”、“巫峽”、“襄陽”、“洛陽”連用四個地名,累累如貫珠。可見,杜甫創作時在煉字煉句上下了很大功夫,而對章法、句法、字法的嚴格要求并沒有影響詩歌內容,反而使詩歌內容更加豐富多彩。
他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屬語遣詞,必極盡意之所至,以求在形神上符合所寫的實際。而七古不似五古,可以從容委曲敘寫,文詞更須有強健的骨力,乃能振起氣勢而不致庸沓軟弱,所以杜甫七古風格,大致是沉著雄健的。相對于五古而言,杜甫的各種語言特色,使他的詩歌內容豐富多彩,充滿風骨意蘊。可見,杜甫在煉字煉句上是相當成功的。
三、從杜甫詩歌的創作思想看其對“風骨”的繼承
從杜甫的詩歌創作思想上看,他也符合了“風骨”的要求。劉勰認為文章應該“風清骨峻,篇體光華”,怎樣才能做到這樣呢?他又說到,“若夫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風骨》)可見劉勰認為必須善于學習,從諸子百家的著作中廣集創作方法,從中吸取營養,豐富自己的經驗。杜甫對前代的文學遺產就采取了正確的態度,他的原則就是“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既要繼承風雅傳統,“別裁偽體”(別,是分別,鑒別;裁,是裁去,革除。“偽體”指思想內容不健康,格調卑下的,便是“偽體”)。又要“轉益多師”,這才是對待文學遺產的真正態度。詩人對于豐富的遺產不是兼容并蓄、全盤吸收,而是有所批判,有所選擇。在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中論述得最為充分。他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杜甫指出齊梁文學有很多不足,不愿作其“后塵”,但是又認為齊梁文學不能全盤否定,對齊梁文學的認識要一分為二,既要充分吸取齊梁文學的精華部分,即“清詞麗句”,接受其有價值的藝術經驗,又要舍棄其卑下、輕艷的一面。從而糾正了陳子昂、李白等在矯枉時出現的偏頗。除了《戲為六絕句》,他還在《解悶十二首》、《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等詩中,談到了詩歌的創作主張。
對于庾信的評價也可以看出杜甫對前人的態度,他充分肯定了庾信在詩歌上創作的成就,對當時一些后進之輩的簡單否定很不滿意。杜甫說過:“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在其他很多詩中,他也對庾信給予肯定的評價。劉勰認為創作要有敢于沖破舊的束縛、不斷繼承和革新的精神,“體必資于故實”,“數必酌于新聲”(《通變》),文體及其要求是古今相承有一定規定的,所以必須借鑒前人。而語言文情是隨時代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就要獨創新聲,這樣,才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通變》)。杜甫不但學習了前人有益之處,而且很多方面都有所發展,律詩、敘事詩都有改革和創新。杜詩的出現呈現出兩大轉折,一是詩歌由抒情轉為敘事,一是詩歌由歌唱理想轉為寫實人生。所以,可以說杜甫是處于中國歷史轉折時期的一位繼往開來的偉大詩人。
綜上所述,杜甫的詩歌創作體現了“風骨”的特征和要求,而且在各方面也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在內容領域的拓展、文學思想的繼承,語言創作的錘煉和藝術風格的多樣等各方面,都繼承并超越了前人。杜詩形式多樣、內容豐富,不僅是唐朝更是我國詩歌史上一篇華彩的樂章。
[1]蕭滌非.杜甫詩選注[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施蟄存.唐詩百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張忠綱,孫微編選.杜甫集[M].鳳凰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