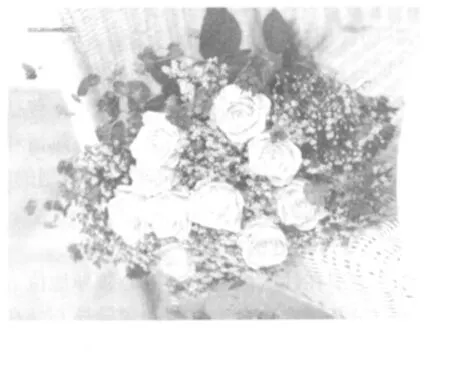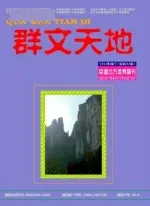探析美國對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地位的影響:以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名稱之爭為例
■晏子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國際政治結構的深刻變革。國家間相互依存度加深,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踏入世界舞臺,其功能、作用和影響日益增強。與此同時,廣泛參與國際組織是中國走向世界,維護和實現中國國家利益以及承擔國際責任的重要途徑。然而由于國際國內形勢,歷史政治原因,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影響力的發揮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其中,尤以美國主導的臺灣與大陸“在國際組織中的名稱之爭”較為顯著。從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爭奪到在政府間國際組織中的名稱之爭,臺灣當局與大陸經歷了長期的較量與斗爭,主要就圍繞著臺灣是以“中國臺灣(中國臺北)”還是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自古以來,中國人都講究“名正言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思想中,“正名”被放在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上,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為名稱和利益緊密相關。詞語的名稱存在大量的可操作空間。
一、受美國影響下的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地位回顧
(一)1949-1970年前,國際組織中的局外者
新中國成立后至冷戰結束之前,中國與國際組織的關系因受國際和國內因素的影響,經歷了一個曲折、艱難的發展歷程,主要表現為中國爭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上。由于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不到恢復,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關系也受到限制。通俗地說,這個時期中國相當于國際組織中的局外者,完全被排除在了國際組織之外。
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聯合國的創建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按照國際慣例,理所當然地取代舊政府享有在國際組織中的合法地位。然而,由于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的原因,中國卻不能恢復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合法地位。
國際上,新中國成立時,東西方冷戰已經開始,以美蘇為首的兩極格局尖銳對立。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操縱西方大國及其控制下的國際組織同社會主義陣營尖銳對抗,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更是采取敵視的立場和政策,在外交上發起不承認新中國的運動,美國這種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必然使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時遭遇巨大的障礙。另一方面,聯合國的權力分配仍然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害怕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地位會壯大社會主義的力量,威脅到自己的霸權地位,因此以種種借口對聯合國施加壓力,并用操縱表決機器,玩弄表決程序等手法阻撓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不僅如此,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組織和其他被以美國為首的大國控制的世界性國際組織都排斥中國,拒不承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美國還在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中推行“兩個中國”的陰謀,以此來阻撓中國和國際組織建立正常的關系。
國內,由于中國當時是以中國國民政府的名義參加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所以臺灣拒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仍堅持“中華民國”為唯一代表。退守臺灣的國民政府,一直未曾放棄“反攻大陸”的政策,認定中共為偽政權。初期由于韓戰爆發,聯合國認定中共為侵略國,國際形勢向“國民政府”傾斜。后期,雖然隨著“中共在大陸統治的日益鞏固,“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性、正當性逐漸動搖。但由于美國與中國對峙,安全理事會否決了蘇聯的提案。美國的對策變為在不排除“中華民國”的條件下,同意中共參加聯合國。雖然后來,美國費盡心機,不斷勸使“國民政府”接受大多數會員國所同意的雙重代表制,但蔣介石不為所動,不與中共并存。
可見,這一時期,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控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之爭,即是中國在國際組織中“局外人”的最佳體現:想要積極融入卻受到百般阻撓。
(二)二十世紀70年代——至今,從“有限參與”到“創造共贏”
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以恢復聯合國席位為標志,中國選擇性地加入了一系列聯合國專門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1978年,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體戰略。對經濟利益重視程度提高并在這個目標指導下,中國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并為恢復關貿總協定的創始會員國地位做出了積極努力。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基本態度由有限參與逐漸轉變為積極參與。其中較為典型的如:APEC和WTO。下面將對兩岸在上述組織中的名稱之爭,展開分析美國在其中的影響:
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政府間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最初對中國加入持積極態度。但美國則希望中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同時加入。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風波后,對中國加入又轉入消極態度,并將中國加入與臺、港加入直接掛鉤。作為目前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亞太地區也是大國較量的重要地區。美日兩國并不愿看到中國大陸主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而是希望繼續維護他們在這一地區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盡管之后經多次談判與磋商,終于達成共識,但不難看出美國在中國加入APEC整個事件上的態度。即希望通過臺灣來牽制中國,實現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經貿主導權。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當今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其前身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中國是關貿總協定(GATT)的創始會員國之一。聯合國于1971年恢復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后,撤銷了臺灣在該組織的觀察員資格。然而,在中國正式提出恢復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后,臺灣當局也以“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領域”的名義申請加入,于是出現海峽兩岸同時申請加人WTO的情況。在這整個過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海峽兩岸之間的矛盾不斷向大陸或臺灣施壓,要求在市場準入等方面讓步,從而使得中國的入世問題從最初海峽兩岸之間的斗爭,演變為大國之間的利益爭奪。雖然GATT曾達成“臺灣不能在中國之前先入會”的共識,但臺灣始終沒有放棄這一圖謀,在國際上特別是美國國內出現一些有利臺灣的形勢后,臺灣當局便一改過去被動加入的策略,重提臺灣加入不受中共影響的口號,希望能在新一回合多邊談判之前加入。并為此積極做美國的工作,在臺美談判中做出了較大讓步,給予美國部分市場開放“頭期款”的特殊待遇。美國為了從大陸入世問題上獲得更大利益,一度放出支持臺灣先加入的風聲。盡管自1997年以來中美關系得到改善,但美國仍堅持對華雙軌政策,加上美國國內政治斗爭,美國國內出現一股反華的聲浪。美國不僅試圖將臺灣納入美日安保體系與戰區導彈防御體系中,而且在臺灣加入WTO問題上態度出現變化,鼓吹兩岸“分開處理”。美國國會中要求支持臺灣加入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甚至美國幕后支持的WTO一些會員也開始表態,認為臺灣應該先加入。
從加入APEC,WTO的一系列較量,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加入國際組織與以適當名稱保留臺灣在國際組織的問題上,美國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直接進行干預和阻撓,將中國排除在外。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一方面,在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下,美國態度是有所變化的。海峽兩岸加入APEC,WTO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中美關系發展的重大問題。在中美關系沒有出現重大倒退及美國在國際事務中仍需要中國合作的情況下,美國還不會犧牲與中國的關系,破壞臺灣海峽的穩定局勢,美國這樣做其實只是個策略的運用,企圖逼中國在中美入世判斷中做出更多的讓步,獲取更多的利益。后來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在大陸的堅決反對下,美國政府的態度發生了明顯變化,最終,臺灣企圖率先加入的努力也都宣告失敗。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影響力的上升與國際地位的提高,美國已無法完全主導國際組織的運行機制,直接影響中在國際組織中的合法地位。所以,最終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下相互妥協,海峽兩岸創造了同時存在于一個國際組織的共贏模式。
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應對和策略
(一)進一步發展與國際組織的關系
目前,由于國際組織中還存在霸權主義,以及中國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和臺灣問題的掣肘,致使中國在國際組織中還處于弱勢地位,在國際組織中進一步發揮作用還存在障礙。因此,中國需要進一步發展與國際組織關系的策略:
首先,中國要以更加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組織,包括調整國際組織策略,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加強國際組織專業人才的培養等。其次,還要在地區國際組織中發揮積極作用,以地區國際組織力量為依托,在國際社會充分發揮大國作用。再次,在國際組織理論的發展方面,中國應該積極創設中國的國際組織理論,爭取國際社會的話語權。
(二)面對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特殊關系積極應對,創造共贏
首先,國家主權神圣不可侵犯,絕對不允許其他任何國家以任何名義通過國際組織進行國家分裂的活動。我們看到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名稱之爭,美國始終“如影隨形”,對臺灣也總是給予“適時的支持”。因而,中國政府在國際組織中一定不能放松對于國家主權的堅持,堅決阻斷一切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制造“一中一臺”事實的活動。
其次,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防止臺灣通過參與國際社會活動,塑造臺灣的“主權國家”形象。臺灣當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和一系列國際活動的一個重要動機,即希望通過參與而塑造臺灣“主權國家”形象,提升其國際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際社會對臺灣的認知與政策。在這一點上,大陸不應盲目打壓,而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社會的一系列活動,彰顯中國的大國姿態,消除一些國家的誤解。允許臺灣在不觸及國家主權的情況下,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以“中國臺灣”或“中國臺北”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或參加其活動。
再次,增強自身實力,國家實力是一國外交的重要保障。美國的對臺政策的實質是,在維護美國首要地位的前提下,平衡兩岸的力量,兩邊得利,最大限度地謀求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我們只有在增強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通過兩國的關系進行相應的制衡,約束國際組織中“臺獨”勢力的發展。
我堅信,上升中的中國,將會勇于承擔國際責任,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同時,兩岸關系也會隨之得到更加妥善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