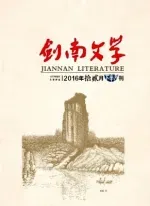從《繡襦記》與《玉玦記》看鄭若庸與明中期傳奇創作發展
● 王 楠
從《繡襦記》與《玉玦記》看鄭若庸與明中期傳奇創作發展
● 王 楠
明代傳奇作家鄭若庸是以一部《玉玦記》進入戲劇戲曲學研究視野的,就現有材料可知,他還曾創作過傳奇《大節記》一部、雜劇《五福記》一部,但均已佚失。明代呂天成《曲品》將鄭若庸列為僅次于湯、沈的八位傳奇作家之一,允為上之中,相比較梁辰魚、張鳳翼等這些作品膾炙人口,研究探討也比較深入的作家,僅憑一部三十六回的傳奇就確立了他在戲曲學史上的特殊地位,鄭若庸在戲曲創作和戲曲形態發展中的獨特貢獻是值得我們繼續深究下去的。長期以來,學界對于鄭若庸的研究僅局限于兩個方面,一是《繡襦記》作者的考辨問題,一是將鄭若庸定位為明代中期傳奇創作流派文詞派(也稱駢儷派、駢綺派等)創作風格的奠定者,把他置于文詞派的發展流變當中進行研究。現今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深入,本文將從《玉玦記》與《繡襦記》的比較入手,探尋明代曲家鄭若庸真實的創作生涯。
鄭若庸所作傳奇《玉玦記》演的是王商和秦慶娘之事,傳奇前半部分類似于唐代傳奇小說《李娃傳》,而后又有一部《繡襦記》也演述士子鄭元和與妓女李亞仙故事,且兩部傳奇風格均以典麗雅正取勝,而《繡襦記》作者又一直眾說紛紜,難以確認,于是就有《繡糯記》的作者是鄭若庸之說。明呂天成的《曲品》中將《繡糯記》列為“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十七種中,明謂無名氏之作也。但其中《繡糯記》后,又附有鄭虛舟作,有前后矛盾之嫌,吳書蔭先生提出“鄭虛舟作”四小字注在清河本原無,后用朱筆添出,可見應是后人增添進去的。而且《曲品》在羅列鄭若庸傳奇時,已明確提出《玉玦記》和《大節記》兩部,不應該把《繡襦記》再另作說明為鄭所作。加之根據徐朔方先生考證的鄭若庸年譜看,《玉玦記》應該作于嘉靖年間,《繡襦記》成于成弘年間,生于1489年前后的鄭若庸應該只是少年之齡,是無法寫出藝術價值超出于他于嘉靖年間所做《玉玦記》的傳奇《繡襦記》的。
根據種種資料表明,《繡襦記》作者為鄭若庸之說是沒有準確史實根據的。但從明清以來《繡襦記》作者之辨我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玉玦記》與前者的緊密關系,曲論家總是將二者并列而談。呂天成《曲品》云:“嘗聞《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及此記(指《繡糯記》)出而客復來。詞之足以感人如此哉!” 清人阮葵生《茶馀客話》中載:“昆山鄭若庸,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系馬者。群伎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薛近兗,為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 《繡襦記》是否真為群伎聚金聘薛近兗所作來恢復秦淮舊觀的今已無法考知,但從清人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這兩部戲在當時劇壇和社會的影響之大。
作家的創作動機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本人的生活經歷和內心情感抒發的需要是動機主要來源之一,尤其是在向來有以詩文抒懷寫憤傳統的中國文人身上,作家的作品中總是潛藏著創作者本人的影子。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著述?類雋類函》云“少粗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 鄭若庸被開除士籍,大概與他流連風月之地有關。《曲品》中對他的品評也是“虛舟落拓襟期,飄飖蹤跡。侯生為上座之客,郗郎乃入幕之賓。買賦可索千金,換酒須酣一石。” 虛舟本身的性格就是狂放風流,任性為之,所以由風月之事有感而寫傳奇以發胸中之怨也在情理之中。而《繡襦記》的主旨則是贊揚青樓女子的有情有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繡襦記》也不大可能是鄭若庸所作。
兩部傳奇的主題有很大的區別,《玉玦記》的首出標題已鮮明的表明了創作的主旨:“日月跳丸,黃花綻了,幾番重九。英雄袖手,阻風云,困圭竇。閑將五色胸中線,雜組懸河辯口。貴坐間談虎,悚然神變,試教沾袖。和璧悲瑕垢,恨紅殞啼花,翠眉顰柳。揚州夢覺,是非一笑何有?從來敏德多畦徑,為看盤銘在否?這優孟諷諫君聽取,謾嘲悠謬。”
作家創作動機和戲曲的主題已昭然若揭,希望觀戲諸君能夠聽取諷諫“戒煙花”,重歸道化“表貞烈”。明代初年,《琵琶》,《拜月》風行,名人雅士爭作傳奇皆以《琵琶》為典范,以宣揚忠孝節義的倫理綱常。《玉玦》也未能免俗,整部傳奇正副兩條線索,王商在京為主,慶娘在家為副,主線為“戒煙花”,副線為“表貞烈”,線索清晰連貫,但也趨于程式化,過于簡單,未有創新。而《繡襦記》的思想內涵則更加多層次化,主題也由純是懲勸規化演變為對李亞仙與鄭元和真摯愛情的歌頌,對門第觀念的不滿。但總體而言,相比較《玉玦》而言,《繡襦》的創作主旨的更加人性化,文學意蘊表達的深入化,思想內容的多層次化傾向是毋庸置疑的。
但兩部傳奇同時也都由于時代和作家身份的局限,仍然還保留著回歸封建倫理綱常的主旨,戲劇本身情節的設置和人物的結局也都不能脫離倫理綱常規范之外。產生此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是明代的文化專制政策的控制作用。明代的文化專制政策對文學藝術的發展設置了重重障礙.《大明律》明文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節烈、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但“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這是宋明理學思想陰影籠罩文化領域的明顯表現。戲曲活動被強制納入整個封建思想文化控制系統之中,促使了明前期戲劇創作道學家風氣的形成。與《玉玦》同時期創作的《曇花記》、《玉合記》等都以宣揚忠孝節義的封建倫理規范為重要創作目的,雖然這些作品不乏文采俊麗之作,但都因主題的陳腐為后人所詬病。但在任何時代的思想史上,所有缺乏活力和生機的思想文化禁錮在長期的發展中必然走向反向的極點,所以在稍后的嘉靖萬歷年間才有強調恢復人性、人情,沖擊理學禁欲主義的以王學為代表的新文學思潮的產生,才有湯顯祖等主情的戲劇家的創作問世。鄭若庸戲曲的理學化傾向是傳奇發展演變中的一個必經的階段,時代和當時的文學創作潮流限定了戲曲創作的主題,鄭的傳奇以及以后與他類似的理學化傳奇的問世使這種創作潮流達到發展的頂端,物極必反,從而才有后世更趨于人性化人情化的作品的涌現。其次就是作家本人經歷和情感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列《類雋》三十卷,載:“明鄭若庸撰。若庸字虛舟,昆山人。少為諸生,以任俠不羈見斥”。 鄭若庸早年曾因為流連煙花風月而被開除學籍,這種慘痛的人生經驗反映在作品中就是鮮明的勸諷傾向。
另外,《玉玦》與《繡襦》的語言風格、關目設置等方面也有不同。《繡襦記》語言比較通俗平易,人物語言與身份的轉換和環境的變遷相適應,例如鄭元和在青樓揮霍金錢時語言文雅典麗,加入很多典故,符合他富貴公子的形象。而當他落魄到要乞討為生時,唱詞風格大變。第三十一出《襦護郎寒》中鄭元和行乞時所唱的“蓮花落”:
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的《拜月亭》條他又說:“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镕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見古詩孔雀東南飛。哪哪復卿卿并驅。予謂此必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 此說確為中肯。與《繡襦記》元人語相比,《玉玦記》則純是文人語。《曲品》稱贊《玉玦》“典雅工麗,可歌可詠,開后人駢綺之派。” 整部傳奇語言以使事用典見長,通本皆作儷語,對仗排偶,形同八股。這也是萬歷以后的曲論家對《玉玦記》評價不高的原因。
而從戲劇關目的設置上看,鄭若庸精于冷熱場的調節,同時借鑒《琵琶》的雙線結構和《拜月》的戰爭離亂背景寫法,吸取了之前戲曲創作的精華并將其妥帖的融為一爐,但由于過于求面面俱到,不免顯得頭緒繁復。《繡襦記》改編自《李娃傳》,但賦予了原著題材更鮮明的傾向,突出了婚姻須以愛情為基礎,反對門第觀念的主題思想。為此,劇作對原故事題材作了必要的加工處理,有刪棄,有增補,有對重點關目的著力渲染。如刪去了女主角參與策劃“倒宅記”的情節,改為亞仙對騙術一無所知,與后來的拒客、護襦、剔目、欲別等情節交相呼應,造就了李亞仙這個對愛情忠貞不二、善良高潔的女主人公形象。與《玉玦》有些關目只是為了顯示作家博學不同,《繡襦》的情節設置與戲劇沖突發展和人物形象塑造息息相關,戲劇情節連貫,針腳細密,前后關聯照應,就連只是客串登場的崔尚書、曾學士,也在后文設置情節,通過二人再邀李亞仙賞桂花而揭示出鄭元和的窮困境地,從而使李亞仙決心“青樓顰笑從此都收拾”,脫離風塵,情節設置的甚為合理。曾經出場的人物全都一一交代結局,可謂圓滿收場。相比較而言,《玉玦》的總體結構和情節則顯得有些單薄。
從《繡襦》到《玉玦》,語言風格和戲劇情節設置上的差異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僅僅是作者寫作水平高下所致嗎?筆者認為這與明代初期南戲到傳奇的演變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明代初期,統治者沿襲元代的做法,有意貶損戲曲藝人的地位,徐復祚《曲論》記載了當時民間藝人的窘迫:“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系紅褡膊,足穿布毛豬皮靴,不容街中走,止于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繡衣服。” 由此引發的對戲曲文學的不重視在社會上形成了風氣,使得戲曲創作和演出只能在下層平民百姓中開展,這必然對戲劇語言和情節有了特殊的要求和限制,平民化,通俗化成為流行的趨勢。而在繼邵燦以駢儷語作《香囊記》之后,文人士大夫開始染指戲曲創作,一掃戲曲創作沉寂不振的境況,在當時影響甚大的《玉玦記》就是以文人身份創作戲曲的典型。士子作戲成為吟詩作文之外的另一自我表達途徑,但這一作家群體的特殊性又不可避免的給他們的創作涂上新的標記。這些文人大都是參加過科舉考試,熟讀四書五經理學經典,作八股文是他們的看家本領。不論是否獲取過功名,他們所受到的文學方面的訓練是如出一轍的,反映在所作之戲中就是以時文手法作曲,大量使用驕四儷六的對偶句。凌濛初在《譚曲雜札》說“今之曲既斗靡,而白亦競富。甚至尋常問答亦不虛發閑語,必求排對工切。” 八股文間接影響著傳奇的結構和語言形式,結構上的起承轉合、語言上的駢儷對仗等是《玉玦》誕生時代傳奇創作的共同特性。
除八股取士的影響之外,明代文學復古潮流的推動作用也是形成鄭若庸劇作風格的重要原因。從弘治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至嘉隆中,李攀龍和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高潮產生期也恰是文詞派劇作大量涌現之時,時間上的重合并不是巧合。據徐朔方鄭若庸年譜考證,王世貞之弟王世懋曾與鄭若庸有過密切的交往,而其兄也曾為鄭若庸所編《類雋》作序,八十九歲時還曾探訪王世貞。王世貞也曾“以維桑之誼”替梁辰魚等人“盛為吹噓”,以致于從者甚眾。前后七子提倡復古,要求文學創作風格、欣賞趣味上趨向于典雅綺麗,而文詞派孜孜以求的駢儷風格正是對復古口號的最佳實踐,正是二者的學說和實踐推動了明代文藝的典雅化,南戲文人化也就在此種文藝浪潮中完成了。
以鄭若庸為代表的一批駢儷派作家是較早進入戲曲創作領域的文人階層,他們將文人雅士特有的風雅情趣帶入當時為統治者所貶斥的地位低下的戲曲文學樣式,從而將散發著民間泥土氣息的南戲逐漸浸染成氤氳著雅風文韻的文人之作,完成了明代中期由南戲向文人傳奇的轉變。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