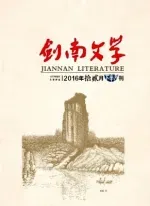西方文論視角下的《山居秋暝》解讀
● 阮亞奇
西方文論視角下的《山居秋暝》解讀
● 阮亞奇
《山居秋暝》這首詩是我國盛唐詩人王維的代表作之一“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歷來被人稱頌,在這首描寫自然的山水詩里,創造出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靜逸明秀的詩境,興象玲瓏而難以句詮,在清新寧靜而生機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萬物生生不息的生的樂趣,精神神化到了空明無障礙的境界,自然之美與心境的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創造出空靈般的純美境界。現在我們換一個視角,把這首詩放在西方文論的角度下,能得出什么樣的境界呢?
一 柏拉圖的創作靈感論
“靈感論”在希臘古已有之,柏拉圖則是集大成者。他說:“凡是高明的詩人,無論在史詩或抒情詩方面,都不是評技藝來做成他們的優美的詩歌,而是因為他們得到靈感,有神力配合著。”①也就是說,優秀的詩歌都是靈感的產物,而靈感則來源于神力。這種說法固然充滿了神秘主義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觸及了靈感所具有的亢奮性、非理性、非自主性和創造性等特征,在柏拉圖心目中,他認為有一種詩完全訴諸作者的內心世界和超驗的東西。而獲取這種東西的過程就是真善美的統一。這王維的這首詩中,作者在一場雨過后,空氣清新,面對著明月、清泉、女子、漁舟,詩人有了創作的靈感,有了內心世界的涌動,才有這種柏拉圖所說的“見到塵世的美”而回憶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在《山居秋暝》中,作者把這些景物和諧的構建起來,在大自然這個“神”下,我可以做這樣的解讀:作者眼前的景物是真的,作者內心是善的,各種食物構成的畫面是美的。這種真善美的解讀有些牽強,但是不論中西方作家,都揭示出藝術創造離不開現實美的觸發,但是又不停留在對現實美的摹寫上,而是從不完善的現實美去追求理想的美,由此王維在最后兩句寫此景美好,是潔身自好的所在,表達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操。
二 朗加納斯的崇高論
朗加納斯在他的《論崇高》中認為崇高的來源有五個方面:莊嚴偉大的思想、強烈激動的感情、運用辭藻的技巧、高雅的措辭和結構的卓越。朗加納斯把崇高的思想看作是崇高的首要條件,“一個毫無裝飾、簡單樸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沒有明說出來,也每每會單憑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嘆服。”②在《山居秋暝》中,作者崇高的理想在最后兩句得到闡發:他在貌似“空山”中找到了一個世外桃源,找到一個心靈的皈依之地,所以他感嘆“王孫自可留”這樣的話語。本來,《楚辭?招隱士》說:“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但是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舍棄官場,遠離官場來潔身自好。王維曾官至尚書右丞,后又屢次遭貶,長期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在封建社會中,多少人想通過科舉走上仕途,但是王維卻表現出和別人不一樣的理想,他這種遠離仕途,歸隱田園的理想,正式是朗加納斯推崇的崇高思想,也是這首詩“崇高”的基礎。在這首詩中,強烈激動的感情的確沒有多少表現,但是作者營造的一個秋山雨后黃昏的迷人景色,娓娓道來的景物,含蓄的情感描寫也不失“崇高”。在朗加納斯《論崇高》中,他還強調情感的表達要恰到好處,感情的表現貴在真實、自然、得體、恰如其分,過分的矯情、濫情智慧產生相反的結果。因此這樣看來,《山居秋暝》在感情上也是崇高的。在他后面三個條件中,“藻飾、措辭和結構”都是屬于技術形式方面的條件。除了思想和情感外,形式技巧的運用也是看一個作品是否崇高的條件,“藻飾”就是根據表現的內容選用適當的詞格。在《山居秋暝》中首句一個“空”字,渲染出天高云淡,萬物空靈之美,而后的“照”與“流”,一上一下,一靜一動,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照”字光色兼備,狀態逼真,展示了一種月光瀉下,透過樹葉,光斑迷離恍惚的狀態;而“流”字更顯示出一種生機勃勃,一個“流”字活靈活現,盡顯風流。在結構上,作者描敘的事物跟隨著作者的視線而動,由近及遠,從上到下,由陸地到岸上,有時間的推移:“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有空間的更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時間、空間完美的結合,使整首詩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說把五個方面的前面兩個來自作者的天賦,那么后三者則是人為的。總之,王維的這首詩從這五個方面看都屬于朗加納斯認可的崇高的作品。
三 盧梭的“返回自然”觀
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提出“返回自然”的觀點,這里的自然,顯然是指他所肯定贊美的原始、古樸的生活,是盧梭基于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理想。這種觀點和王維的觀點不謀而合,王維開元九年進士擢弟后調大樂臣,后貶為濟州司倉參軍。這一年,王維初次嘗到官場失意的打擊。而張九齡執政后,王維屢得升遷,而王維已無心從政,一直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王維的歸隱有他消極避世的頹廢傾向,但是在君權主宰一切的封建王朝里,這種半官半隱的生活恰恰是一種溫柔的抵抗。盧梭的人生經歷和王維也有相似之處,他十四歲變開始流浪謀生,做過徒弟、差役、樂師、私人秘書等。1750年發表的《論科學與藝術》一舉成名,從此專事著述。從少年期起,盧梭便酷愛自然,十六歲時的一次遠游讓他沉醉在自然的美景之中。成名后的盧梭接受朋友的饋贈——一座環境優美的鄉村小房子,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活。在這里,他文思泉涌,寫了許多著名的著作,如政治學名著《社會契約論》(又譯《民約論》),這是世界政治學史上著名的經典著作之一;教育學論著《愛彌兒》,簡述了他那獨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不但對后來的教育學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動力。這種“返回自然“的觀點,在相隔達一千年的時空里,在王維和盧梭那里得到了完美的契合。
四 席勒的《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
席勒說:“詩的精神是不朽的,它絕不會從人性中消失“,”詩的概念不過是意味著給與人性以最完滿的表現而已。”③現代人與古代人的人性不同,因而詩的類型也不同,他認為,古代的詩都是素樸的詩,現代的詩是感傷的詩,但是他有解釋道: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都是人性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又都是表現片面人性的產物,素樸的詩表現人的感性經驗,感傷的詩表現人的理性情感,而理想的人性應該是感性和理性的統一,因此詩的理想應該是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的結合。那么《山居秋暝》這首詩,是素樸的詩還是感傷的詩呢?在這首詩中,作者為我們創造一個清新寧靜的自然之美,各種事物在作者的眼中完美的結合,構成一幅和諧溫馨的自然風景圖。在對景物的描寫上,作者是感性的,是有感而發,從這一點上看,《山居秋暝》這首詩是感性的;但是末句的“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卻是作者面對這些美好景物的理性思考,是對自己現實生活前途的一種詮釋,以自然美來表現詩人的人格美和一種理想中的社會之美,實際上他的行動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一種理性的情感。從這兩個方面考慮,《山居秋暝》這首詩既是素樸的詩又是感傷的詩作者在這首詩中表達的理想是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的結合。
五 浪漫主義觀
浪漫主義作為人文精神的一種,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像空氣一樣彌漫于文學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浪漫主義文人贊美大自然,歌頌人性,強調個性的獨立,用熱情奔放的語言和想象來塑造形象,歌頌自然,自然在浪漫主義者心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在他的《愛彌兒》中全力肯定自然的意義:“無論何物,只要出于自然的創造,都是好的,一經人手就變壞了。”他的“回歸自然”的口號,是為了打破封建等級制度而提出的。然后經過德國、英國、法國浪漫派的發展,自然成為他們歌頌的主題之一。在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在盛唐時期得到長足的發展。王維的抒寫隱逸情懷的山水田園詩,在西方文論中,就屬于浪漫主義文學的范疇,在華茲華斯那里,他認為“詩的目的是抒發情感,歌頌自然和人性,詩是神諭的東西。”④這個觀點在這首詩上也是適用的。而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詩學則強調詩是人創作的,能給人以審美快感的對立統一的事物,也就是詩歌要有統一物我的功能。在這首詩里,作者將景物完美的結合,給人以清新寧靜的自然之美,作者又詩人通過對山水的描繪寄慨言志,將自己的理想融于山水之中,達到詩人與自然思想上的交融。這也符合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詩學觀點。總之,這首詩在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理論下解讀,依然符合西方浪漫主義的基本觀點。
六 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依德認為,白日夢者和藝術家創作有很多相似的,首先是兩者都不是樂天派,王維仕途不順,肯定不是樂天派;其次是白日夢者的幻想起于現實中不能獲得的滿足,藝術創作起于藝術家潛意識中種種受壓抑的欲望和沖動,藝術活動是種種欲望的替代滿足,這里不能說是王維的官場不得意而創作作品,但是他創作隱逸情懷的山水田園詩確實是他一方面對當時的官場感到厭倦和擔心,但另一方面卻又戀棧懷祿,不能決然離去,于是隨俗浮沉,長期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的寫照,把自己的對社會,對仕途的情感通過田園詩的方式表現出來,或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通過這樣來滿足自己在仕途上的不幸遭遇。再次就是兩者都和時間有關系,游移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王維把對過去的遭遇的感情,對眼前的景物的感情和對未來的生活感情結合起來,王維這首詩,正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通過自我觀察,將“他自己精神生活中沖突的思想在幾個主角身上得到體現,”在他看來,山、水、明月、石頭、竹林、漁舟都是他思想感情的主角,然后用幾個動詞“照”、“流”、“喧”、“動”把他們串聯起來,賦予他們生命,把自己對自然生活的向往有所寄托。
弗洛依德還認為,弗洛伊德還認為,人除了有對權力、財富、名譽、地位追求的野心外,還有對欲望的發泄以及性欲的排遣的要求,藝術家通過自己的天賦和運用藝術的手段把壓抑的性欲轉化為藝術品。在這里,我們把《山居秋暝》看做是王維對性欲得不到滿足的一種解讀,他當時被貶,遠離繁華喧鬧的長安,在這里沒有友人相陪,沒有侍女服侍,肯定是空虛寂寞,只能寫這樣的田園詩來排遣自己的壓抑。
總之,用西方文論的很多觀點都可以重新解讀這首詩,例如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瓦萊利的象征主義等等,每一種解讀都賦予這首詩新的魅力和內涵。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