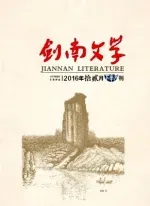歷史?神魔?現實——淺論《封神演義》中“武王伐紂”的現實意義
李愛紅
山東經濟學院 山東濟南 250014
神魔化歷史是歷史藝術化的獨特方式之一:用神魔的外衣來裝扮歷史,放任藝術想象在歷史的畫卷上隨意潑墨,但核心的歷史框架依舊清晰可現——神魔小說《封神演義》可謂是一部另類的歷史演義,歷史人物的主角地位被神魔人物取代;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由神魔人物主宰;改朝換代之際,封侯與封神同行。但既然演繹了歷史便同時關照了現實。因為歷史題材的文學雖然以往昔歷史為表現對象,但它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精神與當代思想精神應是息息相通的。正所謂“過去未來皆現在”。所以《封神演義》的神魔描寫不是終極目的,盡管我們常常駐足、沉迷于“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神魔斗爭,而將“武王伐紂”的史實擱置起來。但我們萬不可忘卻歷史與現實這對孿生姐妹的存在。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美學家克羅齊曾經說過:歷史“假如它有什么意義而不是一個空洞回聲的話,那么它也是現代的”,“因為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只有一種對現在生活的興趣才能推動人去查考過去的事實。因為這個緣故,這種過去的事實并不是滿足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為了滿足一種現在的興趣”。為此,他認為現實感是一切歷史“固有的特點”,歷史和現實生活的關系是“統一性的關系”。
“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于千載”,中國自古以來的信史傳統和“史貴于文”的價值觀念,對中國文學的最大影響當是歷史演義小說的興起,出于慕史、重史的文化心理,文人們紛紛操觚演史,大量名為《……志傳通俗演義》、《……史演義》、《……志傳》的歷史演義小說問世。生活在農業生產社會,受封建制度鉗制的民眾對英雄創業、豪杰爭鋒、賢相安邦、權臣誤國等改朝換代、朝政興廢之事尤為矚目。盡管這類家國大事與他們熟悉的日常生活相隔甚遠,但滲透在歷史演義中的“歷史感”深深吸引著他們。所謂“歷史感”,通常指歷史實錄的逼真性、客觀性以及獨特性。但“歷史感”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離不開“現實感”的參預催化。過于淺薄的歷史感,未免會陷入矯情、幻滅之中。但如果沒有具有社會功利性的現實感作為依托,歷史感就會因單調的講述和陌生、晦澀的人事與話語而顯得過于厚重。那么歷史感也就失去了歷史本該給予我們的無可辯駁的思想哲理和認識審美功能。歷史感與現實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使普通大眾讀者,在歷史中可以看到他們熟悉的鏡像,甚至捕捉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封神演義》作者為何選擇這樣一段歷史來關照現實?首先是史實本身的原因。“武王伐紂”是討伐暴君,遵循了歷史前進的規律,而成為歷代君王的警示牌;但又因其是以下伐上,違背了封建倫理的大道,而成為敏感話題。這一段帶有雙重性的歷史,一直以來是被作為反面教材,強調其警示性,所以盡管有悖君臣之禮,反暴政的合理性卻給予其在夾縫中生存的理由。甚至某些帝王或真誠或虛偽地以此自省,作為自己仁慈愛民的明證。明嘉靖皇帝就曾面對毅然等待死亡的海瑞說過:“此人可方比干,然朕非紂耳”。可見紂王始終是盤旋在歷代統治者頭上的陰影。所以作者選擇了這段歷史作為演繹對象,憑其合理性可以堂而皇之地“指東罵西”,宣泄心中的不滿,大快讀者之心;其敏感性,則給人以啟示,生發出無限的想像——關于當朝帝王,關于自己的宗廟社稷,關于自己的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題材的文學是和現實“對話”的文學,作家選擇哪段歷史,如何對歷史事實增刪取舍,主要取決于“對話”的需要,取決于主體的自覺創作活動的驅動。面對生生不息、不舍晝夜的歷史逝川,作家的藝術思維必有褒貶臧否的選擇取舍。因為并非一切歷史都能適應與現實“對話”的需要,都能夠“肆其胸臆”。當已然的歷史變成了作家心目中的“歷史”,它標志著作家已經投注了“現實感”,用現代意識同歷史進行“對話”而達到了古今統一。黑格爾對此更是做了很好的闡釋,他說:“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即對于一種歷史,不論它的題材是什么,都應毫無偏見地陳述事實,不要把它作為工具去達到任何特殊的利益或目的,但是像這樣一種空泛的要求對我們并沒有多大幫助。
《封神演義》中“武王伐紂”的歷史事實掩埋在神魔斗爭的光影中,但剝離了神魔的外衣,歷史感依然會撲面而來,作者投注的現實感也清晰可現。被夸大化的紂王的惡與文王的仁,是作者極力彰顯的一個對立面,肯定仁政、痛貶暴政,抨擊弊政奸惡,頌揚圣君賢相的思想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反觀現實,小說恰如當朝的一面鏡子。魯迅曾說:“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足見出明朝統治者的殘暴。明朝自朱元璋始,廷杖、剝皮、凌遲、抽腸等各種酷刑也不曾停歇,其暴虐程度絕不遜于造炮烙、蠆盆、酒池肉林的紂王。成化以后,最高統治集團漸趨墮落,王朝生活奢靡、腐化,武宗、世宗、神宗等,都是不務政事,恣肆胡為,酒色財氣俱全的昏君,政治失控,思想文化統治趨于崩潰。然而,面對這樣讓人痛心疾首的政局,即使在“肆其胸臆,以為自得”的文網疏弛時期,文人學士的言路也沒有暢通無阻,直言君之過尤其要慎之又慎。恰恰得益于“武王伐紂”這段歷史的特殊性和小說的神魔外衣,作者做到了真正的“肆其胸臆”。商容在九間殿悲泣而奏的一段話,可謂懇切的忠良之言,足見出作者對當朝者的忠肯以及曾經心存的那一絲希望:“臣昔居相位,未報國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饞逐正,紊亂紀綱,顛倒五常,污蔑彝倫,君道有虧,惑亂已伏。臣不避萬刃之誅,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納。真撥云見日,普天之下瞻仰圣德于無疆矣。”諄諄話語,肺腑之言。等到聞太師條陳十策時,已是在危急關頭的“救時急著”,但至少希望還在,忠心不滅。“子牙暴紂王十罪”是國勢傾頹后天愁民怨的暴發,憤恨可以發泄,但失望至極的悲哀、落寞成為沉重的十字架永遠壓在心頭。《封神演義》的作者是不幸的,因為他生逢末世;他又是幸運的,因為《封神演義》給了他言說的機會。同樣幸運的是同時代的小說讀者。小說抨擊弊政、歌頌仁德是帶有相當程度的人民性的,這不僅反映了作者開明的政治觀念,進步的歷史觀,同時也是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普通民眾的一種精神寬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不再是虛無縹緲的理論,因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足以削去倒行逆施的失道之君的冠冕。堯舜之治是中國古代民眾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對于這樣的社會,早在二、三千年前,人們就夢寐以求了,但直到整個封建社會結束也沒有實現。自然,善良的人們決不會放棄美好的理想,他們將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的身上,這對于災難深重的華夏民眾來說,無疑是一種理想之光,它至少可以作為一種標準或參照,以此來對黑暗的現實統治進行有的放矢的批判。《封神演義》中風景雍和,民豐物阜,行人讓路,老幼不欺,市井謙和的西土社會實際上就是堯舜之治的現實縮影,讀者在小說中體會到了他們期待已久的生活,也找到了踏入理想社會的革命路徑。
毋庸置疑,《封神演義》托古諷今,曲折地反映了明代的社會現實。借古諷今歷來是歷史題材文學的題中之義。顧名思義,借古諷今是借歷史來諷喻現世,其中必然有強烈的功利性與目的性。借古諷今的基本美學特征是諷喻,因而歷史本身的含義隨著文學歷史世界中內容重心偏離了歷史的具體存在,而逐漸暗淡下去,愈來愈清晰的是它的喻義所在,即作者賦予它的特殊的現實價值。“先欲制今而后借鑒于古”往往是歷史題材文學作者的創作出發點,為了曲折地吐露對現實世事不便說明或不欲明說的看法,必須合理地選擇一段歷史將其看成某一現實生活或情感形式的對應物。在這里,作者首先關注的是作品對現實具體事件或“諷”或“諫”的隱喻效能;而對用以諷諫的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則通常頗為隨意,大多情況下無非妄作“假借”或“假托”之用。“有時甚至為了特指的需要,不惜夸張乃至全然改變歷史真相。……使被諷喻對象哭笑不得而又無可奈何,而讀者方面則心領神會,直接從中受到聯想和啟發。”正如夏衍所說:“諷喻史劇的性質上就需要能使讀者(觀眾)不費思索地從歷史里面抽出教訓來的‘聯想’。”果戈里也說“借過去來鞭撻現實,這樣的話,會獲得三倍的力量”。《封神演義》的隱喻最先來自“武王伐紂”這段歷史與明朝的隱秘關系。小說中大肆宣揚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中的言論被反復提及、引用,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曾罷祀孟子,刪節《孟子》,而且其中刪節的言論都是由“武王伐紂”的歷史引發出來的,所以歷史本身對于現世就有著特定的喻義。此外,《封神演義》中紂王集諸惡于一身,文王成為仁政的化身,雖然遠遠偏離了史冊記載,但諷諫的效能卻大大增強了:公道自在人心,稱揚王道、仁政,反對暴君、暴政的思想傾向自然地滲透到讀者心中,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勞苦民眾讀者,共鳴之感尤為強烈。再者,小說中描寫了幾類驚人之舉:臣叛君、子殺父、妻休夫,這些在當時有悖彝倫的傷風敗俗之舉,不是作者的主觀臆想,而是現實激發的想象。明朝的“靖難”、“奪門”、“議禮”三件大事,都是封建宗法制所嚴令禁止下強橫發生的篡逆、背叛行為,隨著統治階層對宗法制的沖擊,下層民眾的信仰也開始動搖,儒家倫理道德的矛盾性和虛偽性被越來越多的人嘲弄。《封神演義》中這些驚人之舉隱喻的正是當時倫理道德缺失后,是非黑白的顛倒,以及時人的茫然和困惑。
確切而言,《封神演義》是一部歷史題材的神魔小說,由題目即可知道小說重心在于“封神”,神魔描寫是重點。但神魔外衣沒有阻滯小說現實意義的發掘。一方面,借神演史的歷史藝術化方式有著“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武王伐紂”是關涉革命與叛逆的敏感歷史話題,高明的作者找到了神魔這個擋箭牌,為自己撐起了保護傘,因此可以卸卻所有約束與顧忌,大膽地直擊現實要害。另一方面,神魔小說的浪漫主義本身有著現實主義的基礎。高爾基曾經說:“神話乃是一種虛構。所謂虛構,就是說從既定的現實的總體中抽出它基本的意義而且用形象體現出來,這樣我們就有了現實主義。但是,如果從既定的現實中所抽出的意義再加上依據假想的邏輯加以想象——所愿望的和可能的東西,那么,我們就有了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就是神話的基礎。”《封神演義》不是神話小說,但神魔形象與神話里的形象有相同的本質和生成機制,都可以視作一種概念的化身和思想的象征,對現實的概括、抽象和幻化。舉例來說,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背叛正義和棄暗投明的現象,神仙中就有申公豹的卑劣活動,也有長耳定光仙的正義行為,這兩個具體形象就概括了現實中某一類人的思想品質。再如申公豹外形描寫,也是對現實生活的幻化。作者賦予他以一個面朝脊背的形象,這種超現實的外在標志,正是他助紂為虐、倒行逆施的象征。
誠然,歷史多彩地塑造了我們,而又是我們人自身構成了歷史。歷史是我們生活的航舵,規范著我們的行為,規定著我們的話語,而又是我們以自己的話語宣布著歷史的規定,用自己的行為延續著這種規范。歷史是我們在時空舞臺上表演的一幕幕故事,而又是我們記錄、講述著歷史,把它變成我們的敘事。現實之于歷史不是簡單的影射或比擬,相似的歷史進程給人同樣的感慨,歷史的重現或者時代化的演繹、摹寫,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眼前的人和事。“重蹈覆轍”的悲劇常常發生,但有了像《封神演義》作者這樣有敏銳體察力的先知先覺者,及時提醒、驚醒世人,悲劇也許就可以避免,至少是讓人有備而戰。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完整歷程來看,現實是歷史的發展,不可能不留下歷史的痕跡;歷史是現實的由來,也必然能從中找到現實某些事物的淵源,它們兩者必然相互涵蓋著某種超時空的,帶有恒定性、普遍性的本質意蘊,相似稟賦。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真正深層的原因,似乎還應該到歷史文學內在機制中去尋找。我們應該謹記愛?霍?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一書中所說的:“我們既不是愛過去,也不是從過去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過去,理解過去,把它當作理解現在的一把鑰匙,由此才能構成發展、豐富著的對話”。
[1][意]克羅齊,“歷史和編年史”,轉引自《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35頁.
[2][魏]李康,《運命論》,[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296頁.
[3][德]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頁.
[4]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頁.
[5] [明]黃佐,《翰林記》卷十一“禁異說”,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47頁.
[6]《封神演義》第九回“商容九間殿死節”.
[7]《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影印版,第2680頁.
[8][9]郭沫若,《從典型說起》,《郭沫若論創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年版,第543 頁.
[10]夏衍,“歷史與諷喻”,《文學界》,1936年(創刊號).
[11]高爾基,《蘇聯的文學》,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頁.
[12][英]卡爾著,吳柱存譯,《歷史是什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