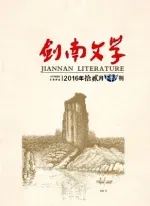《說文》部首字的轉喻造字模式
周運會 吳世雄
福建師范大學 福建福州 350007
一、轉喻的認知功能和分類
在傳統修辭學中,轉喻被認為是一種詞語替代現象,英文metonymy(轉喻)源于希臘語 metonymia(改名),指一事物被用來指稱與之相關的另一事物。Lakoff &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 中提出,轉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而是我們日常思維方式的一部分。[1]隨著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深入,Lakoff(1987) &Johnson(1987)認為抽象概念的產生有兩條途徑:(1)從具體域到抽象域的隱喻投射;(2)從基本層次范疇到高層次范疇和低層次范疇的借代(metonymy)投射。[2]有些語言學家認為,轉喻可能比隱喻更為普遍和基本。Radden & Kovecses提出,轉喻是一個概念現象和認知過程,并且在 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內運作。Kovecses對轉喻的定義如下:轉喻是同一個域中的一個概念實體(源始域)為另一個概念實體(目標域)提供心里通道的認知過程。與隱喻不同的是,轉喻涉及同一個域的整體和部分或部分和部分的關系,源始域和目標域的關系是臨近性,源始域的功能是為理解目標域提供心理可及性。[3]近年來,轉喻的認知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認知語言學框架內,Radden & Kovecses對轉喻提出了較系統的分類。他們根據同一理想化認知模型中本體與喻體的關系,將轉喻的概念構形分為兩種:1)整體與部分轉指;2)整體內部分與部分之間轉指。[3]
二、認知轉喻與漢語研究
轉喻是一種認知方式,是構建抽象概念的重要手段。“認知語言學更適合于對漢語進行分析,因為漢語是象形和形聲文字發展而來的,對其字形、本義以及引申義的研究有利于發掘文字產生與發展的歷史。”[4]本文擬將認知轉喻理論和漢字文字學相結合,對漢字的形義聯系進行研究,發掘其中的轉喻思維,并參照Radden &Kovecses[3]對轉喻的系統分類,對結果進行總結歸類,從而驗證轉喻的認知性和普遍性,并從新的視角審視漢字的文字結構。之所以取《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的部首漢字為研究對象,是因為部首漢字的成字時間早,構字能力強,使用頻率高,是基礎性的漢字。同時還因為《說文》成書于東漢時期,是古文字學的經典著作,其訓釋多參照古文經典文獻的相關用法,理據充分。
三、《說文》部首字構形體現的轉喻
筆者通過對《說文》540個部首的研究,總結出了以下的轉喻方式:
同一個ICM中,以整體代部分
①:以具體場景表其特征。相關字例有:品,半,正,中,是,,夭,多,,,桀,先,黃,北,,至。分析如下:
品:《說文》:“品,眾庶也。從三口。”眾庶指眾多意,甲文中“口”表物,從三“口”表示器物眾多。“眾多”是“品”這個場景的抽象特征。
半:《說文》:“半,物中分也。從八從牛。牛為物大,可以分也。”則“半”以分牛的場景來指代“中分”的動作。
正:《說文》:“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其中“止”是腳的象形,“一”指目的地,以向目標直線前進構形,來表達不偏斜的抽象意義。
冓:本意為遘遇,甲文以上下相對的兩條魚構形,“遘遇”之意,蘊于其中。
齊:《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齊”字本意為整齊,以整齊的禾麥形象為之,體現了漢字構形“近取諸身”的方式。“整齊”正是一片莊稼的鮮明特征。
桀:《說文解字精讀》:“形體示人登于木上,本意即高,杰出。”[5]
黃:《說文》:“地之色。從田,從炗。炗亦聲。炗,古文光”。“黃”從田,從古文光,以日光下的黃土地來表征黃色這一抽象概念。
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北”的本義為違背。《戰國策· 齊策六》:“士無反北之心。”
此外,“是”訓為“直”,以太陽直射當頭會意;“夭”訓為“屈”,是一個曲頸歪頭的人形;臠肉相疊為“多”;食器充盈為“豐”;足立人前是“先”;雙人并立為“竝”;箭落地面是“至”。
②:以物象代其特征。相關字例有:大,小,幺,叀,玄,死,皀,高,員,晶,明,赤,方,黑。分析如下:
大:“大”象正面站立的人形。《說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則以人形示“大”與中國傳統思想有關,“大”是人的特性之一。
小:甲文象沙子之形。馬敘倫認為,小即沙之初文。沙從水,少聲。少,小本為一字。沙子是微小之物,用來表示抽象的“小”意。
叀:《說文》:“專小謹也。”按“叀”為紡磚,用以紡線,執之可轉,作圓周運動;故有專一之意。
皀:《說文》:“皀,谷之馨香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此字以谷之形象示其馨香之意。
高:“高”字甲文象一個樓閣的形象。《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以高聳的臺觀形象來表達“高”。
晶:《說文》:“晶,精光也,從三日。”此字甲文象三個太陽,或有一說是星星,以發光體來指稱光明。
黑:《說文》:“火所熏之色也。”“黑”以火上的煙囪構形,火所熏的煙囪,其色黑。此即以煙囪代其特點。
此外,“幺”為絲形,訓“小”義,“死”左為殘骨象形(右像人形),指稱其無生命特征。“赤”是站在大火里的一個人,被燒“紅”了。
可以看到,以上字例絕大部分都表達了抽象的概念。漢字起源于圖象形文字,寓意于象是其特點之一。但抽象的概念無象可形,先民們就借助與這些抽象概念相關的具體形象對其進行表達,這就是以物象表其特征的轉喻造字法。
(二):同一個ICM中,以部分代整體。
①:以構成部分代整體。相關字例有:牛,羊,臣,民。
“牛”“羊”字甲文皆取其頭部象形,“臣”甲文為一豎目之形(俯身臣服時的特征),“民”取相于錐刺失瞳之目(“民”本指“奴隸”);此皆是所表征概念的突出特征。
②:以顯著特征轉指該范疇。相關字例有:男,女,士,父,巫,史,君,后。
士:《說文》:“士,事也。”吳承仕說:“事謂耕作也。…所謂物插地中也”耕作插苗古為男子之事,故“士”有男子意。
父:甲文像手拿工具之形。郭沫若認為手拿斧頭從事野外勞動的男子為“父”。
史:《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右持中。中,正也。”“史”字甲文上部的
“中”指捕捉禽獸的長柄網,下部是右手之形,本義為管理狩獵或記錄獵獲物的人。其造字用到了以所為代指人的轉喻思維。
君:“君”甲文上部是一個執杖的手,其下的口表示發布命令。《說文》:“君,尊也。”
此外,用“力”(耕作之具)耕田為“男”,交手跽坐為“女”,長袖善舞是“巫”,施令四方為“后”。
③:以場景代相關時間。字例有:晨,夕,旦。
晨:《說文》:“晨,早昧爽也”。篆文“晨”上為“臼”,指雙手;下為“辰”,指農具。以天將亮時勞動的情景指代這個時段。
“夕”為傍晚時分的月亮之形,代指晚上;“旦”是日出地平線,代指清晨。
④:以范疇成員轉指范疇。“犬”部字中的“犭”可指代獸類,如“狼”,“獅”;“巾”部在構形時,可用來表示布帛,如“布”,“帷”。
正如所料,這一小節的字例都是表達范疇概念的名詞。事物的概念通常是比較復雜的,一字之力難以表現完全。但語言受到經濟原則的支配,這就使能夠以簡代繁的轉喻思維大行其道。事物特征和范疇中心成員更具有認知凸顯性,因此,通過對事物特征或范疇中心成員的描摹來喚起整個概念就必然成為漢字的構字法之一。
(三):同一個ICM中,以部分代部分。
①:以事物代動作。相關字例有:卜,入,用,行,干,心,口,手,目,耳,足,釆(讀若“辨”)。分析如下:
卜:《說文》:“卜,灼剝龜也。…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卜”取形于占卜時龜甲上的裂紋,字義為“占卜”。
入:甲文上尖下寬,象矛鋒之形。《說文》:“入,內也。”“內”即進入內里之意。“入”字以矛鋒之形指其用途。
釆:《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釆”為獸跡,表“分辨”意。古人狩獵時常據足印分辨獵物,“釆”為辨識的對象
此外,“用”字是木桶之形;“行”甲文象四達之道,義為“走路”;“干”本是一種武器,表“干犯”義;“心”部,“口” 部,“手” 部,“目” 部,“耳” 部,“足” 部在構字時,這些象形部首常用來表示相應的功能。如“思”,“懷”;“吃”,“唱”;“撫”,“拍”;“見”,“相”;“聞”,“聽”;“跳”,“踴”。
十:甲文象側視的手掌之形。郭沫若說:“中國以掌為十…(金文)一豎而鼓其腹,亦掌之象形也。”“十”字構形的經驗基礎即人有十個手指,故以掌為十。
力:甲文像耕田的農具,耕田要用力氣,因而用以指代力氣。
弜:“強”的本字,意為強大。弓為強者之物,與強大有關。
勿:《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勿”本為召集民眾的雜色旗,民眾看到旗幟,則匆匆趕去,故“勿”有急意。
③:以原因表結果。字例有:克,甘,兇,喜。
克:本義為“勝”。《爾雅·釋言》:“克,能也。”甲,金文“克”象人戴甲胄之形,一個武裝好的人能夠取得勝利;故“克”有“能夠”,“戰勝”意。此則以原因表結果。
甘:甲文以含有食物的嘴巴構形;吃著美食,所以感到甜美的滋味。
兇:《說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兇”意為兇險,地面下陷,不便行路,所以兇險。
喜:甲文上為鼓形,下為口,“鼓”指音樂,聞樂則喜。
④:以結果代動作。
“生”甲文下面一橫表示地平面,上面是出土的一棵小草芽。《說文》:“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生”指草木萌芽,動詞,則此字的構形體現了以結果代動作的轉喻思維。
“亡”金文以一個隱匿在角落里的人構形,《說文》:“亡,逃也。”“亡”本義為逃亡,奴隸逃亡后就要躲藏起來,好不被發現。
以上字例表達的概念相對字形來說也都比較抽象。在表達這些概念時,先民們借助了與其有邏輯關系的具體相關物象,利用轉喻思維化抽象為形象,創造了相應的漢字。
三、結語
漢字的基礎是象形文字,具象性是漢字的特征之一。而事物的屬性和動態概念無法直接描繪,必須要借助相關的事物形象進行表達。因此,此類漢字的構造就要用到基于臨近性的轉喻模式,在同一個理想認知模型(ICM)中,用可視性強、凸顯性高的部分來指代直觀性弱,相對抽象的概念。這既符合認知的省力原則,又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這使轉喻在漢字的創制中大顯身手,比隱喻更為普遍。基于以上研究,漢字轉喻造字法可分為:(1)物象表其特征;(2)事物特征轉指事物;(3)范疇中心成員代指范疇;(4)邏輯關系轉喻。
《說文》部首字所體現的轉喻方式共分為三大類:1)同一個ICM中,以整體代部分;2)同一個ICM中,以部分代整體;3)同一個ICM中,以部分代部分。其中前兩類屬于整體與部分轉指,則這三大類正與Radden & Kovecses的總體分類相符。[6]在具體的轉喻方式上,則有四種無法納入Radden & Kovecse的詳細分類,這四種方式是:1:以具體場景表其特征;2:以物象代其特征;3:以場景代相關時間;4:以相關物指稱概念。這說明轉喻思維既有普適性(universal),也與特定的文化環境相關。
[1]Lakoff, 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37
[2]藍純.認知語言學與隱喻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57-58.
[3]Radden, G.& Z.Kovecses.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C].In Klaus -Uwe, Panther.& G.Radden.(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17 - 59.
[4]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196.
[5]殷寄明.《說文解字》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112.
[6]陳楓.漢字義符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7]束定芳.認知語義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8]臧克和,王平.說文解字新訂[M].北京:中華書局,2002.
[9]左民安,王盡忠.細說漢字部首 [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