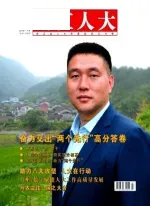地方創新需與制度對接
■特約記者 蘆 垚 特邀嘉賓 楊雪冬 李 凡
地方創新需與制度對接
■特約記者 蘆 垚 特邀嘉賓 楊雪冬 李 凡
地方創新為何會出現“孤本”現象?如何給地方創新輸送動力,使其貢獻于中國的整體改革?專家指出,越是草根的、民間的,創新性越強,但也正是這些很容易變成改革孤本,除了因為它的影響力和自身獲得的支持最弱,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和制度的對接程度也是最弱的。
政府被社會“包圍”
□地方創新的動力主要來自哪里?
■楊雪冬:創新的動力來自很多方面,比如追求更好的政績(比我們批判的政績觀更高一些的政績),希望做出些成績對社會有好處;希望回應當地面臨的發展問題,地方政府在這方面的第一目標往往是改善投資環境,獲得更多資金;還有回應上級,特別是中央精神,這和追求政績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政績必須是在體制里。
我們研究發現,創新獎(中央編譯局推出的地方政府創新獎)大部分不是原創的創新,都是回應中央的,價值理念都在中央文件里體現出來了,地方政府做了一些創造性的改善。這是地方改革很重要的一個特征。到今年為止,我們評出了5屆地方政府創新獎。在總共113個入圍項目中,落實型的占到88個,純粹原創型的只有12個。雖然如此,敢于回應的還是少數。
當然,還有一些地方改革是偶然因素促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改革動力和地方發展情況有很大關系。經濟結構和文化對改革的影響是很大的,不同的經濟結構產生的政府行為是不一樣的。
□改革的地方因素,具體表現是什么?
楊雪冬:比如廣東,文化很低調,政府面臨最緊迫的是投資環境問題,所以廣東的改革大多是針對這個問題。但在勞工關系等方面,他們就比較落后。
■李凡:中國的地方改革主要出在3個地方:廣東、四川、浙江。這3個地方的改革各具特色。但現在廣東的改革面子上的東西比較多,實質性的改革還是出自四川和浙江。
浙江的改革特點是社會發達,自主獨立。浙江的很多官員,家庭成員或者親戚都是經商的。他們背后有這個背景,和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人很了解社會在想什么。政府被公民社會“包圍”,浙江的改革就有社會基礎和社會需要,是在社會推動下進行的自發性改革。這些改革者大多也不求升官,他們認為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
浙江的社會高度發達,大家覺得不當官也照樣活得好好的,而且將來退休了我也不指望你,所以眼睛不盯著升官。反觀四川,社會相對不發達,所有人眼光都盯著政府。官員都想著升官,不升官我干什么?
所以從2000年開始,四川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各級組織部門在那兒做的試驗,形成了一個四川模式:上面要求做,下面就找一個機構來做。凡是做得好的,就升官。因此四川的改革比較反映高層意見,或者是省委或者是中央,基本上是黨內民主的模式。
改革要和制度對接
□但是眾多地方政府創新人走政息的現實表明“升官激勵”并不能為創新提供持久的動力,很容易使改革成為孤本。
■李凡:對,這也是地方改革成為孤本的一個主要原因。地方改革大部分都是地方官員自己做的,這樣就有一個問題:我是縣委書記,這是我做的改革,等我走了,下面的人認不認?個人做的,又沒有得到上面的認可,一般到下一任的書記都不承認。這是上一任書記的政績,我干嗎要承認你?中央和省里都不承認,我干嗎要承認你?不承認,接下來就不做了。
地方改革成為孤本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都是地方探討,沒有上級政府或中央的政策支持。而且,一些改革是跟現行法律相沖突的,得不到法律的配合。如果這些改革能納入到中央的試驗范圍,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楊雪冬:從上級來說,對下面的試驗往往還是不評價,不發表意見。但有時候下面做事情需要支持,沉默反倒變成否定。這取決于官員的政治技巧,所以這也變成了個人化而不是制度化的東西。
□地方改革成功的關鍵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人走政息”和“曇花一現”?
■楊雪冬:所有的改革,個體需要制度配合才能進行下去。我們回訪發現,地方政府的創新很矛盾,一方面沒有新理念問題解決不了;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認為只靠自己創新沒有前途,中國的改革必須要由上往下改。如果有了更多層次、更高的黨委部門參與進來,對改革的推廣是更有價值的。
綜觀這些年的地方改革,會發現越是草根的、民間的,創新性越強,但也正是這些很容易變成改革孤本,除了因為它的影響力和自身獲得的支持最弱,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和制度的對接程度也是最弱的。
地方改革和整個大的制度環境是有關系的,必須要和整個制度對接,不然很難做下去。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海南建省改革。我看1988年海南建省時的文件發現,當時提出的理念都是最新的。比如當時明確提出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整個海南省的政府結構設計都是小的,相當于現在的大部制。但是這幾年海南的部門越來越細,人員越來越多,都在回潮,向原來的體制靠攏。為什么?因為所有資源分配的方式還都是按照原來舊的體制分配的,你必須要跟它對上才行。
■李凡:地方改革要想獲得成功,很重要的一點在于是否符合現有體制。為什么溫嶺的改革能生長?很重要的原因是放到了現有的體制內。不管哪任領導來了,人代會都得開。像洛陽的改革,把網友選為人大代表,這個就不合理,個人因素太大,換個領導就可以不要。
很多地方改革都想在體制外搞一套東西,這是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因為制度沒有,領導在的時候可以讓這個東西活下來,一旦領導走了就不行了。溫嶺這個就是跟現行制度結合,改進了現行制度。
社會的倒逼
□既然如此,制度上需要給地方改革以怎樣的支持?
李凡:在目前的體制下,中央不同意,地方改革就進行不下去,必須要有中央和地方的聯合改革。地方要有自己的積極性,但就有一個問題,地方的積極性從哪里來?中央不承認,地方活不下去,就沒有戲了。
■楊雪冬:現在公眾對中央充滿期待,所以中央必須在宏觀層面上發揮應有作用。國家社會關系要重新調整,這種調整主要是在地方政府行使權力時做出的。如果地方政府調整不好,矛盾就會累積起來。所以大家誰也離不開誰,都很重要。
地方改革,既需要上面的認定,也要有社會的發展。對于中央政府來講,主要就是給地方政府創新提供授權支持,同時提供法律支持,以此為改革創新營造環境。
□近些年,社會的土壤對地方改革的影響如何?
■楊雪冬:真正的地方改革應該是更多民眾參與、民眾支持的。我們的調查顯示,從官員角度來看,他們也認識到創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民眾的參與。從這個標準看,廣義上地方改革的土壤正變得越來越好。現在參與渠道雖然有很多限制,但實際上還是擴大了。一些舊的渠道被封掉又產生了新的,比如網絡,這些都推動政府做事情。政府老講倒逼機制,實際上就是社會的參與。沒有社會的倒逼,政府不會產生壓力。
(楊雪冬: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李凡: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
相關鏈接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浙江獲獎情況(2001—2010)
創新獎:
浙江省金華市干部經濟責任審計
浙江省溫嶺市“民主懇談”
浙江省湖州市“戶籍制度改革”
浙江省義烏總工會: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
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政府: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
浙江省杭州市政府:開放式決策
入圍獎
浙江省衢州市“農技110”
浙江省臺州市“鄉鎮團委書記直選”
浙江省椒江區“縣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
浙江省長興縣“教育券制度”
浙江省紹興市“政府辦公室導入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
浙江省武義縣“村務監督委員會”
浙江省溫州市“效能革命”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農村合作協會
浙江省慶元縣委組織部:技能型鄉鎮政府建設
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參與式預算改革
浙江省湖州市委組織部:干部考核機制創新
浙江省松陽縣政府:農村宅基地換養老
——張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