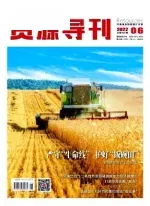故鄉(xiāng),從記憶深處走來
□王邦賢
故鄉(xiāng),從記憶深處走來
□王邦賢
長途大巴飛快奔馳。窗外,是青青的麥田,金黃的油菜花。這一溝一渠,一樹一草,讓人倍感親切。看著眼前的春色,故鄉(xiāng),一點(diǎn)一點(diǎn)從記憶深處走來。
童年的記憶,是一個(gè)胖乎乎戴著肚兜,一搖一擺走過長長的土路,來到村頭豆腐坊里喝豆腐腦的小男孩。小男孩拖著長長的鼻涕,被外婆牽著,口齒不清嗚嗚啦啦說著誰也聽不懂的話,但磕磕跘跘的腳步始終伴隨著外婆慈愛的目光。
長大一些,是和父母姐弟一起回老家。坐了一天車,傍晚才到故鄉(xiāng)。黑黑的夜色,斑駁的土墻,裊裊炊煙,伴著看家狗的狂吠,神秘而陌生。恰恰此時(shí),我和姐姐與父母走散了。無奈之下,我們闖入一扇灰黑的柴門問路,年幼的我們說找不到外婆家了。這家大娘問我們姓什么,姐報(bào)的是媽的姓,我報(bào)的是爸的姓。老大娘笑了,從黑乎乎的鍋臺(tái)里摸出兩個(gè)熱騰騰的紅薯遞給我倆。“餓了吧,吃個(gè)紅薯。走,我送你倆回家!”多么淳樸的故鄉(xiāng)人!
故鄉(xiāng)三間簡陋土坯主房,兩間配房充當(dāng)廚房。由于偏遠(yuǎn),直至上世紀(jì)90年代還沒有用上電。晚上,點(diǎn)上油燈,屋內(nèi)所有擺設(shè)都變成墻上碩大含糊的投影。每晚,我們盯著油燈跳躍的火苗,聽舅舅講民間傳說進(jìn)入夢鄉(xiāng),夢里是離奇的廝殺和夜鳥的輕啼。
故鄉(xiāng)有高高的木門檻,幼小的我進(jìn)出時(shí),得費(fèi)力地跨來跨去。那滿坡遍野的黃土地,就是跌一跟頭也不疼。外婆家門前是成行的老樹,鄉(xiāng)親們總把牛兒羊兒拴在樹身上,院前頭還有一個(gè)大大的池塘,夏天時(shí),鴨啊鵝啊在里面唱歌。晚上,我們就和勞累一天的大人下水嬉戲玩耍……
告別故鄉(xiāng)多年了,眼前的麥田,連帶著有關(guān)故鄉(xiāng)的記憶碎片噴涌而出:夏日頂著荷葉赤腳走在曬得滾燙的鄉(xiāng)間小道上;夏夜點(diǎn)一截蠟燭去照蟬兒脫殼;或者陪舅舅坐在一望無際的麥田看他苦悶地吸煙;或在打麥場,聽老漢講稀奇古怪、上下五千年的傳奇故事……
從父母親口中得知,現(xiàn)在的故鄉(xiāng)成了“空心村”,青壯年都在外打工,村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屋前池塘已填平,修成了水泥路,土坯房也早改成了磚瓦房,小時(shí)天天光顧的豆腐坊也擴(kuò)大了規(guī)模,機(jī)械化使得磨豆腐更加省力。疼愛我的外婆早已作古,靜靜地躺在村頭麥地里,只剩下記憶里的綠樹蔭涼,訴說著思念和哀婉。
不知為什么,故鄉(xiāng)在我腦海中依舊是20年前的樣子:沉默而寂靜,就像黑夜中的星星,遙遠(yuǎn)而明亮。
我知道,我的根屬于那兒。
(作者單位:河南省第一地質(zhì)工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