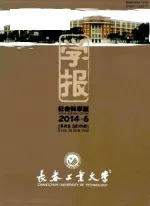社會變遷視野中的城市女性擇偶觀探討
林麗芬
(集美大學 政法學院,福建 廈門360000)
社會變遷視野中的城市女性擇偶觀探討
林麗芬
(集美大學 政法學院,福建 廈門360000)
本文首先梳理了關于女性擇偶的動機主要理論觀點,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實證資料的分析,探討了不同時代背景下生活在城市的適齡女性擇偶觀的的主導模式:50年代的英雄模范、文革時期的政治至上到改革開放后的學歷為重,90年代的經濟實用主義以及當前的多元化趨勢。論文最后探討了建國以來我國城市女性擇偶觀變遷的理論意蘊及其啟示。
擇偶觀;社會變遷;城市女性
一、女性擇偶動機:已有理論的解釋
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1]在選擇配偶的過程中,女性傾向于選擇能滿足自己在生理、心理、經濟等各方面需求的對象來組成家庭,并一起撫養后代,而在這些方面女性則較為稀缺或無法過多投入去獲取。因此,配偶能否滿足自己的的需要,在意識或潛意識層面成為女性擇偶時的出發點。
同樣的,資源交換理論和溫奇的要素互補理論也支持這樣的解釋。資源交換理論認為,“人們為某一特定的異性所吸引,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資源決定的。假如某一資源不足,可以更多的提供另一種資源作為補償”。[2](P223-226)例如,男性在身高上不足則可從社會地位來彌補。溫奇的要素互補理論認為“雖然擇偶同諸多因素如年齡種族血統住宅的臨近,社會經濟地位教育或先前的婚姻地位等相一致,但是當擇偶表現為心理需求和個人動機時是互補而非同一的。”[3]這兩個理論指出擇偶過程中,人們傾向于考慮對方與自己在各種需要和資源上的相輔相成。
進化心理學理論認為“在生理上年齡與生殖力的差異導致男女在擇偶時對年齡偏好的不同。由于男性在生殖上消耗的健康代價較小,因此他們容易接受與多個伴侶保持短期的關系,和男性不同的是,對女性來說,與異性發生關系意味著懷孕和撫養后代。因此,她們更忠于長期的兩性關系,傾向于選擇有責任感并有能力對她們自身和后代負責的異性”。[4]同時,這也是由于生理差異而導致的擇偶性別差異的主要體現。
擇偶梯度理論認為“男性傾向于選擇社會地位相當或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的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職業階層和薪金收入與自己相當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對的‘男高女低’模式。”[1](P223-226)這個理論與男權為主導的社會文化有關系,這些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在各個時代中女性的擇偶觀中有所體現。
二、城市女性擇偶觀:不同時代中的主導模式
新中國成立前,女性的社會地位較為低下,被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所壓制,在婚姻方面是實行“買賣、包辦婚姻”,在擇偶這一人生大事上基本沒有自主選擇的自由。建國以后,伴隨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浪潮,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較大的提高,城市女性開始在擇偶方面有了自主性。而擇偶的時代主導特色主要從五十年代開始,本研究隨機選取共三十名在各年代處于適婚年齡的城市女性和國內知名交友網站的工作人員作為訪談對象。
(一)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中期:“英模崇拜”成為擇偶主流
在新中國成立后,政府用了十年的時間對中國的女性進行了整體性的解放,使女性擺脫了封建倫理道德牢籠,提出男女各頂“半邊天”,即賦予女性與男性同等的公民權力和地位。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了較大的提高,并在擇偶上獲得了自主權,建國以來到六十年代中期,城市女性的擇偶標準主要是注重對方的政治出身和家庭成分,而這個時期的城市女性理性擇偶對象是英雄、勞模和軍人。那個時代的“英雄”主要是捍衛祖國尊嚴的軍人;建國初期,在全社會都興起“勞模”和“工作積極分子”的評比,勞模則為生產工作中的模范;“英模崇拜”成為當時的主流文化,也成為城市女性擇偶的主導模式。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劉女士出生于1935年,在福建廈門生活了六十幾年,現居住于思明區洪文小區。據劉女士回憶,當時的戰斗英雄、勞模和解放軍是那一時期女性心目中的偶像。建國初期的女性在選擇配偶的時候,只要對方的政治條件好,經濟、長相、年齡方面差一點也沒有多大的影響。當時的夫婦,還很少是通過自由戀愛而結婚的。主要還是通過熟人或媒人的介紹來認識對方,進而雙方再繼續發展。所以當時父母的意見對她們在擇偶中也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她本人也是通過別人介紹與當時是軍人身份的丈夫結為夫婦。
(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文革十年):政治決定一切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上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反右斗爭嚴重擴大化,政治標準成為唯一的標準,城市女性的擇偶觀也受了影響而形成了單一的標準。當時的女性在選擇對象時,主要是看對方的政治條件。城市女性的理性擇偶對象是工人或干部、黨員,那時女性不太考慮文化和經濟條件,當時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社會地位低,而且當時除一些高級干部的收入略高一點之外,同一年齡層的男性在經濟收入上幾乎相差無幾,更多關注的是政治面貌和家庭出身,比如貧下中農、“紅五類”。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根據現居住于福建廈門市蓮興社區已經64歲的嚴女士回憶,當時的女性對對方的外貌、文化條件都不太考慮,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最不受歡迎的,大規模知識青年都投入了上山下鄉運動。由于文化大革命吃的是“大鍋飯”,因此當時的女性也不太考慮對方的經濟因素,主要的還是考慮對方的政治出身和政治條件,如果政治條件不好,隨時都有可能會被批斗。這樣的情況持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上的學歷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與此同時,經濟的繁榮帶動了中國學術界的進步。隨著社會問題、人口問題研究的深入進行,對婦女問題的關注逐步增多。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城市女性的獨立性和自主意識隨之發展。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知識分子被全面平反,當時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現代化建設對知識的迫切需求使社會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地位進行了重新認定。相應的,“工農兵大學生”成為城市女性擇偶中的理想對象,政治面貌與家庭出身曾在60年代為主導取向的條件已逐漸淡出擇偶的首要考慮因素,有文化有學歷則成為那個年代城市女性擇偶因素里最重要的條件。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城市女性逐漸走上工作崗位。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據現居住于廈門市洪文小區出身于1960年的許女士的陳述,在20世紀80年代,城市女性擇偶時,把知識分子擺在了較高的位置。文化因素成為了當時女性擇偶考慮的第一因素,經濟因素其次,政治因素成了較為不重要的因素。許女士當時是在一家工廠上班,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在她選擇對象時對對方的經濟要求不是很高。許女士雖然只是小學的學歷但對對方的學歷要求至少要高中以上。通過熟人的介紹,許女士與當時在某中學教書的陳老師結為夫婦。
(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實用主義與注重“人本”的多元化標準
20世紀90年代,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循規與變革、守舊與開放共存的多元體。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也受到影響。而城市女性的擇偶觀也經歷了從90年代的實用主義向現代的多元化趨勢發展的漸變過程。
隨著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入,人們逐漸發現個人價值體現方式雖然呈現多樣化,但結果卻是一樣的,即創造價值的多少或經濟效益的多寡,城市女性的擇偶觀也開始越來越務實,90年代流行著這樣一句話:干得好不如嫁的好。在本研究過程中,筆者在與我國知名婚戀網站“世紀佳緣”工作人員的訪談中了解到,很多城市女性都知道人品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擇偶過程中往往被外部條件如經濟和家世背景、外貌等外部條件所干擾而忽視了,此外還存在著沒有進行深入了解只因為對方“條件優越”就“閃婚”的現象,這些都影響著城市女性擇偶之后的婚姻生活質量和家庭穩定。
80后的適齡城市女性大都是獨生子女,大多有著良好的教育環境、在許多崗位上也和男性一樣具有較好的職業能力,甚至更為出色,有不少更是才貌并存,更為優越的生活環境讓她們對擇偶也有了更多的考慮。本研究中對當代80后女性訪談中顯示,收入水平雖然被看中,但與此同時,男性的人品修養、道德觀念、社會責任感、事業心、職業、教育水平等許多因素也是女性擇偶非常看重的因素,另外,她們還很注重兩個人彼此的“感覺”,訪談對象稱之為“眼緣”、“順眼”,不僅僅是“適合”而是真正的兩廂情悅、心靈相通。總的來看,人品,性格,能力,感覺等的綜合多元化標準是當代城市女性擇偶的主要趨勢。城市女性的獨立使她們可以和男人一樣平等的站在社會舞臺上,理直氣壯的依照自己的擇偶觀挑選伴侶。
三、城市女性擇偶標準的理論探討:變遷與回歸
通過以上對建國以來我國城市女性擇偶觀的變化的實證分析,本研究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論探討:
第一,擇偶觀的變化,體現了所處時代的大多數社會成員期待的社會資源取向。在歷史發展變遷的過程中,社會資源和利益獲取所應具備的條件和身份各不相同,它受制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各個年代所呈現的身份:50年代的英雄模范、軍人群體、80年代的高學歷群體,當代擁有較好社會經濟地位的富裕群體等,他們都占據著他們時代的主要社會資源,而比較明顯的趨勢是擇偶條件中的社會經濟因素逐漸被強化;各個時代的城市女性擇偶的主導模式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期待婚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滿足自己的需求。這一點也遵循著本文前部分所提到的擇偶需求和動機規律,如擇偶梯度理論、資源交換和要素互補理論。
第二,在婚姻選擇中,個體自由度不斷增加,并有從單一趨向多元化的趨勢,與此同時,來自外界的影響則不斷地的削弱。以往把顧及外表形象和物質基礎貶為低級、庸俗的資產階級擇偶觀,此外也可能來自單位組織、家庭等外部因素的多加阻撓,具有壓抑人性和正常需求的傾向。如今擇偶標準具有多重性,同時考慮各類條件,反映了當事人對婚姻的多元需求,由于每個人的價值取向、自身條件及擇偶時所處境遇的不同,對婚姻的要求也各異,因此,擇偶標準各有側重。對經濟條件和外貌的重視并無過多批判、“丁克”“忘年戀”等的多元化標準,當擇偶從以物質需求的互相補充、支持、輔助為主,轉向以個人吸引力及相互滿意程度為主,其家庭背景、年齡、婚否等因素則被淡化。這些變化體現了馬斯洛需求理論里對高層級的精神需求的追求,反映了社會文化的寬容度和多元化,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并體現了女性社會地位和自身素質的發展。
第三,隨著社會的改革開放時代的發展,傳統的人的性格、道德因素在婚姻選擇中的重要性逐漸得以回歸。在個性方面,女性對對方修養、人品的要求呈上升趨勢。北京大學學者錢銘怡等人在一項調查報告結論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末人品排序已躍居第一位。[5]說明城市女性擇偶在注重“物”的同時,更加注重“人”本身,這反映了傳統觀念在婚姻選擇中的重要性逐漸回歸,經濟條件固然重要,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的改變,城市女性的自身素質的提高,她們越來越認識到品行的重要性,道德水平較高的男性更具有較強家庭責任感,能在婚姻生活中體貼和關愛家人,約束自己的不利家庭和諧的行為,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
四、結論與啟示
擇偶觀的變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總體的變遷趨勢和格局。城市女性擇偶觀的變遷,是社會變遷的有機組成部分。家庭作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既有隨著社會發生變動的因素,又有超越社會變遷的某些恒定不變的因素,如對誠實、孝敬、有責任心等傳統價值要素的堅守。本研究通過分析認為,影響人們擇偶取向的因素是多元和復雜的,諸如社會的發展、地區的特定文化、對方的個人條件等都可以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城市女性在擇偶過程中,在考慮主流的社會思潮和主導價值取向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美德在婚姻中的特殊價值,畢竟,這些因素才是決定今后婚姻生活能否幸福的關鍵所在。
因此,城市女性在選擇對象時應盡可能地建立理性的擇偶觀,避免盲目地跟隨社會潮流而忽視自身的實際情況,從而導致過于追求物質價值而拋棄婚姻中真正重要的傳統美德因素。
[1]黃希庭.普通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張海鐘.現代女性心理學導論[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
[3]林勝.從擇偶的理論到擇偶理論——從社會學方法論的爭論看擇偶研究[J].社會,2002,(9).
[4]張海鐘,劉慧珍.女性擇偶標準的社會歷史變遷及當代走向[J].邯鄲學院學報,2010,(12).
[5]錢銘怡,王易平.十五年來中國女性擇偶標準的變化[J].北京大學學報,2003.
林麗芬(1981-),女,碩士,廈門集美大學政法學院社會學系講師,集美大學女性研究中心成員,主要從事女性發展、社會工作與心理健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