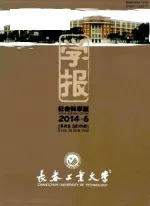論網絡環境下的隱私權保護
——以“人肉搜索”為研究對象
李 瑞 計 楠
(長春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論網絡環境下的隱私權保護
——以“人肉搜索”為研究對象
李 瑞 計 楠
(長春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人肉搜索”案件展示了不同方面對于網絡環境下隱私權保護問題的不同理解。但綜合來看,由于都是體現了權利主體的私人性和秘密性,互聯網隱私的內涵與現實中的普通隱私相同。同時,互聯網隱私權也與網絡言論自由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我們應當加強對隱私權保護和互聯網監管制度的立法工作,從而調和這種沖突。
隱私權;人肉搜素;言論自由
隱私權對人們的生活安寧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隨著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人們在享受越來越便利生活的同時,卻越來越難以保護自己的隱私。所以,盡管現代的人類生活品質已遠超前人,卻并不一定更幸福。因此,研究互聯網環境下的隱私權保護問題,對于提升人類幸福、促進社會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在當下因互聯網而引起的隱私權眾問題中,以“人肉搜索”現象最為突出。通過對該現象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厘清對相關問題的模糊理解。
一、從“死亡博客案”探討對隱私保護的不同理解
目前,學界內公認的“人肉搜索”第一案,應屬在2008年發生的“死亡博客”案。在該案之前,“人肉搜索”已經成為互聯網中的常見現象,并出現了如“陳自瑤事件”(2001年)、“虐貓門事件”(2006年)、“銅須門事件”(2006年)以及“馬六事件”(2007)等典型案件。但在“死亡博客”案之前,這些案件大多以網絡民意的勝利而告終,而這也是“死亡博客”案引人矚目的關鍵。
“死亡博客”案的案情本身并不復雜:某公司女白領姜巖在家中跳樓身亡,在生前的博客中,她將自殺歸咎為丈夫王菲的不忠,其博客之后被稱為“死亡博客”。博客的內容在姜巖死后,由其友人張樂奕通過自己注冊成立的網站“北飛的候鳥”全程轉載。此后,“大旗網”也對該事件進行了實名報導,另有網友將整起事件轉載于“天涯論壇”。在這種情況下,網民的不滿情緒被激發,開始自發的尋找王菲的個人信息。而隨著相關信息的披露,王菲也因此遭到了網友從網絡上的謾罵到現實中的暴力。在這種情況下,王菲對“北飛的候鳥”、“大旗網”與“天涯論壇”的經營者或管理者以侵害名譽及隱私權為由提起訴訟,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在2008年底做出判決,確認“北飛的候鳥”網站的管理人張樂奕,“大旗網”經營人北京凌云互動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相關行為構成了對王菲名譽權和隱私權的侵犯,應承擔相關責任;而“天涯論壇”的經營人海南天涯在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在事件發生后及時刪帖,已盡監管者義務,不構成侵權,不需要承擔責任。
對于本案的判決結果,法學界與網民出現了兩極化的評論。法學界普遍認為,此案中原告的隱私權確實受到了一定侵犯,該侵犯事實并不因其在先的不道德行為所導致的輿論關注而改變,原告隱私權也不應因此受限;而網民們則普遍認為,網絡中原告的個人信息已經案外人(姜巖)披露,應屬公開的社交信息,不屬于隱私。同時,違法與違背道德的行為應當受到公論,即使涉及隱私,該行為主體的隱私權也應當受到言論自由的嚴格限制。由此可見,雙方的分歧點無非有二:第一,在網絡環境下隱私,是否與現實環境中的隱私具有相同含義;第二,網絡環境下,網絡言論自由與民事主體隱私權的沖突如何解決。
二、網絡隱私的內涵與現實隱私相同
所謂隱私,即隱私權的客體,是主體行使權利必然指向的對象。目前,學界內普遍認為,所謂隱私,無外乎生活安寧和生活秘密,[1](P563)前者是獨處的權利,后者是保有的秘密。[2](P272-273)此二兩者,是對生活中所有隱私事物的高度概括,不但涵蓋現實,也同樣可以適用于虛擬世界中對隱私的確定。
筆者認為,網絡環境和現實生活中的“隱私”內涵在下列方面都存在相同之處:
首先,不論在現實生活還是網絡環境中,隱私都是權利主體私人性的體現。從生物學的意義上來說,人類也是一種動物,具有多數動物都具有的保有自身領地的本能。這種領地本能要求作為個體應當取得并管理一定的自有空間,并以這該空間為安全保障,完成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過程。因此,對于任何一種動物來說,領地的占有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在生物界中,肉食動物的領地行為一般要強于素食動物,或者說獵食者對獵場占有欲要強于草食者對草場的占有欲。[3](P37)而人類作為靈長類中最早的獵食者(250萬年前),其領地本能較其他高等動物更為強烈。這種本能伴隨著人類歷史的進步,并經歷了一萬余年農業文明的鍛化,最終上升到一個特殊的高度。這種本能,在集合層面上的體現,就是國民對國家主權的追求和維護,而如果通過個體的訴求進行表達,則體現為自然人對于私人生活的追求。這種追求可以體現為高墻大院的居所,也可以體現為封口封印的書信,這些無生命的事物,寄托著主體對于私生活安寧的期望。這種期望促使人們通過法律的形式將每個人的個人生活空間進行固化,在這個空間之內,是主人的家園,需要由隱私權保護其中的安寧和秘密,空間之外,則是社會公共生活的“公地”,可以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使用。
在網絡環境下,雖然“人”的存在被虛化,但他追求個人的寧靜私生活的愿望卻并沒有任何改變。現實生活的個人空間此時也移植到了網絡環境之中,在隱私權的保護之下,他可以享受精神的安全與放松,并紓解現實的壓力。而當他人侵犯他的隱私時,他個人的私生活必然受到嚴重影響。因此,網絡環境下的隱私與現實環境一樣,都是權利主體私人性的體現。
其次,不論在現實生活還是網絡環境中,隱私都是非公開的。隱私幫助主體建立了安全而安寧的私生活環境。因此,隱私的非公開性,實際是將隱私權主體和其他個體相互區隔,使得他個人生活及信息不為人知。相反如果隱私主體希望將他的生活和信息公之于眾,那么這種經過公開明示的生活和信息就當然脫離了隱私的范圍,不再是隱私。
隱私的這一特性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的較為明顯,為了保護我們的隱私,我們為我們的住所設置了各種安全措施,使得他人不能直接觀察我們的生活過程。而在網絡中,對應每一個ID的,必然是專屬于他個人的密碼。對應每一件私人信息的,必然是為他而設定的加密措施。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不論是在現實還是網絡環境中,隱私都必然是秘密的。
但在“人肉搜素”案件中,一個問題出現了。網民們進行搜索的對象信息,大多是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在網絡上公開的信息。例如,受害人將自己的個人信息貼在了自己的校友錄中,卻因校友錄未上密碼而為他人所知。此時,受害人這種提供自己信息的行為是否屬于公開?又例如,受害者原先為完成完成交易而在論壇上留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之后第三人搜索到這條信息,并將之公之于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網絡看成一個公開的環境,那么該案的受害者似乎是自己將自己的個人信息置于公開的狀態之下,第三人對此一公開信息的搜集和發布,似乎并非針對隱私,是否就因此不屬于侵害隱私權了呢?對這類爭議,筆者認為,其中的關鍵在于兩點:
第一,隱私權主體是否公開了自身的隱私。所謂公開,是指將原本不公開的信息置于公開的狀態之下。因此,是否公開,必須要從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進行判斷。就主觀層面而言,隱私權人的公開行為應在明知或應知的主觀心態下做出;就客觀層面而言,他的行為應當符合社會對公開行為的一般性認識。就上文所舉例1而言,受害人將個人信息發在校友錄中,其目的必然是希望特定的主體(同學)知曉其相關信息。由于該信息的散播范圍是確定的,受眾是特定,所以,受害人并不期望公開該信息。而在一般情況下,校友錄一般都具有區隔同學與非同學的功能,因此,當校友錄成員在內部發布信息時,一般人均有理由相信這種信息不應為外人所知。所以,受害人的這種行為從客觀角度觀察,同樣不屬于對自身隱私的公開。
第二,隱私權主體為何公布自身的隱私。如果隱私權人果真公布了自身的隱私,那么我們勢必需要了解,這種公布行為是否就等同于公開。隱私既使我們擁有寧靜的生活,也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與他人的聯系。因此,這就意味著,為了與他人建立或者加深某種關系,我們必須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對象公布一些隱私而這種公布行為有時在客觀上會使個人信息出于公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了解這種公布與公開的聯系,我們必須將公布行為與權利人的主觀意圖聯系起來。
隱私權人公布自己的隱私,必然為達到一定的目的,或者純為吸引他人注意,或者是為了促成一筆交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隱私權人公布行為的意圖,決定了他公布信息的范圍與程度。比如,如果受害人僅僅在自身QQ空間里貼入了自己的照片(設定好友可見),那么就可以推知,這一公布行為僅僅局限于他的QQ好友,僅僅達到使他的好友知悉的程度。而如果受害人為了完成一項交易而在一個公開的論壇里發布了自己的個人信息,那么該公布行為雖然沒有特定范圍的對象,但從公布的目的出發,該行為對隱私的公布僅達到可使知曉者使用該信息與隱私權人進行交易的程度,并不允許將該隱私用于與交易無關的領域。所以,隱私權人的這一公布行為,僅對特定領域產生公開的效力。因此,若第三人為“人肉搜素”而將該交易信息公之于眾,很明顯是將非公開的信息轉變為公開狀態,是對隱私秘密性的破壞。
網絡隱私的這一特點與現實隱私完全相同。現實中曾有案例,A女與B男相戀,為取得B男信任,向B公開了自己的過往性史。后二人分手,在分手后,B男在于C女交往中,將A女的性史信息予以告知,導致該信息迅速傳播,給A女造成極大困擾。在這一案例中,A向B告知自己的信息,僅僅希望該信息為B所知,并不愿意將之公諸于眾。[4](P698)所以,B將A之相關信息泄露給無關第三人,顯然是將非公開的信息公開化,是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因此,隱私所特有的秘密性,并不因存在環境的不同而變化。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發現,網絡環境下隱私的內涵,與現實環境并無不同。
三、網絡言論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
網絡是網民自由發言的平臺,在虛擬管制環境下,網民們的發言幾乎沒有任何不利后果,這也使得網絡成為言論最為自由,最少約束的場所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不法行為人侵害他人隱私權的成本大大降低,加重了隱私權的受害程度。因此,在網絡環境下,網民的言論自由往往容易與隱私權發生沖突。
網絡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之間的矛盾沖突主要源于它們各自實現方式的不同。隱私權的目的在于維護自然人的私密生活和信息,排除別人妨害害,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保守性;而網絡言論自由的目的則在于維護公眾“知曉和訴說”的權利,滿足人們輿論監督和知情權的需要,具有開放性的特征。在自由的虛擬網絡世界中,自然人一方面希望知道或評論更多別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為他人所知,于是網絡言論自由和隱私權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矛盾。
在“死亡博客”案中,網民們的主要訴求有二:首先,基于公共利益,原告因自身的不道德行為,原屬其隱私的信息而應轉化為公開信息。在現實社會中,確實會有特定主體因公共利益的存在而必須公開自己的信息,如官員應公開自己的個人財產。但在“死亡博客”案中,原告雖德行有虧,但其行為之影響畢竟僅限于家庭范圍內,與廣大的不特定多數的人民群眾并無關系,其行為的非道德性顯然與公共利益無關。很顯然,此案中原告的個人信息,不能因公共利益而成為公知信息。其次,基于社會良知,原告人的不道德行為應當被譴責。從網民的角度看,他們的行為本身是合理的,也是發揮了網絡輿論監督的作用。但當這種批評的聲音從網絡文字轉化為現實中的言語暴力時,一些網民的行為就明顯過火了。他們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言論自由的界限,構成了對他人權利的侵犯。即使從社會道德的角度看,由于道德之施行關鍵在于人的內心遵守,若以某種強力落實道德要求,無異于以德入法,破壞法定秩序。
通過對“死亡博客”案中網民主要訴求梳理,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網絡言論自由和網絡隱私權來說,其只不過是在信息時代下,傳統隱私權和言論自由權的延伸。因此,傳統的解決言論自由和隱私權及矛盾的基本理論,同樣適用與網絡環境中的言論自由和隱私權的沖突。
具體而言,我們應通過以下兩個渠道調和這種矛盾沖突:
第一,加快針對隱私權保護的立法工作。目前,但隱私權的立法工作一直較為滯后。《侵權責任法》頒行前,司法部門一直以保護名譽權為由對隱私權進行曲線保護。這種保護的范圍有限,效率也較低。而在《侵權責任法》中,法律雖在將隱私權納入了保護對象,但并未對隱私權的界限做出明確規定。這種模糊性從一個方面造成了網絡言論自由與隱私權的沖突。而作為一種重要人格權,隱私權應該受到足夠的重視,對其進行細致的規定,將有利于沖突的減少。
第二,加快針對網絡秩序的立法規制。目前,我國的互聯網行業仍然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由于新事物涌現的速度過快,導致既有管理體制無法有效落實,這就使我國目前的互聯網絡社群交往仍處于自行發展狀態。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在未來應進一步落實論壇版主負責人和發言備份制度,并在部分地區嘗試網絡實名制度。同時,應重視社會組織在調整網絡秩序方面的作用,重視行業自律,由行業組織對大型論壇、網站的管理人和所有者進行培訓和引導,并嘗試對部分論壇進行認證,真正建立良好的行業管理秩序。
四、結語
網絡環境下的隱私權保護一直是一個重要的難題。網絡中的隱私權是現實中的普通隱私權在特殊的網絡環境下的體現,它具有與普通隱私權相同的客體,并且同網絡中的言論自由存在巨大沖突。這一沖突在可見的未來,都必然會是我們對互聯網規制問題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從整體角度出發,我們應當從加強隱私權保護立法,以及加快針對網絡秩序立法規制兩角度入手,調和網絡言論自由同隱私權的沖突。
[1]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美〕Richard Posner.The economics of Justice[M].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3]韓明友.人性的起源[M].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5]楊立新.人身權法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李瑞(1981-),男,法學碩士,長春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法學教研室講師,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計楠(1992-),男,長春工業大學人文學院2009級本科生,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