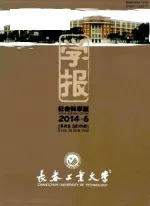辛亥革命的成敗與中國現代民主政治
問 昕
(福建師范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辛亥革命的成敗與中國現代民主政治
問 昕
(福建師范大學 社會歷史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新型的革命,其實質是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的碰撞。辛亥革命實現了民主、共和和憲政,順應了世界潮流,堪稱中國民主政治的里程碑。辛亥革命的根本意義,在于推翻了君主專制,國家原有的主奴關系被打破,奴才變成了公民,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辛亥革命縱然有許多不足,但以其光輝的政治實踐,證明了民主政治的普適性。
辛亥革命;民主政治;普適性
一、辛亥革命順應了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
中國歷來是一個君主專制的國家,君主的權力不斷加強,到明清時期達到頂峰。在專制制度下,國家成為專制者的私有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自命天子,自稱“君權神授”,裝神弄鬼,愚弄人民,使人民服從其統治和指揮。這種情況持續數千年而無疑議,一旦有人提出質疑,其結果要么是被鎮壓下去,要么是在反對者掌握政權后,重新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如此循環往復,數千年未變。所以梁啟超曰:“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1]
近代以降,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的民主革命摧毀了束縛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專制制度,開始了近代的文明政治,張揚政治民主、社會公平和自由、人權等觀念,并成為一個世界潮流。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的專制統治者繼續陶醉在夜郎自大的迷夢中,他們以犧牲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為代價,竭力維護其統治寶座的“穩定”,這是由其貪婪的本性決定的。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勢力,在鎮壓了維新派后,繼續玩弄“新政”的騙局,夢想延續其茍延殘喘的統治。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終究難免被拋入歷史的垃圾堆。
與專制者的愚昧自私相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有識之士,他們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發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吶喊,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思想,要求改古變法,引進新制;他們提出并踐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從不同的角度批判舊觀念和舊體制,觸及到政治學說、政治體制的一些方面,無論是在膽識還是見解上,都難能可貴;他們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提出君主立憲的政治改革設想,開始了維新變法運動……孫中山指出君主專制的弊端,“創新機器,發明新學,人民以懼死刑,不敢從事。所以中國人民,無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2](P50-51)堅決主張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并最終成為現實。
循著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正在逐步適應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這些底層的人民才是中國的脊梁。“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其說是革命者推翻了君主專制,不如說是他們順應了世界的潮流。
近來,學術界不乏這樣的論點,認為清末“新政”的實施,勢必要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甚至把“新政”說成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開端,這種觀點是荒謬的。第一,論者在滿清專制統治已被推翻的情況下,虛構了“如果新政進行下去,將如何如何”這樣的一段歷史,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推論,顯然不是唯物主義的做法,也缺乏最起碼的學術常識。第二,“新政”是在鎮壓維新派不久后出臺的,它不是一個順應潮流的自覺行為,而是因形勢所迫而采取的一種應急策略。如果指望專制者開放民主,放棄獨裁,無異于癡人說夢。第三,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新政”主導者并不理解“民主”為何物,他們不想放棄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想繼續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新政”絕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結果。第四,論者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為專制者應該承擔的甲午戰爭的失敗責任來掩飾,為屠殺維新志士的罪責來開脫,為鎮壓革命者的行為來張目,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否定辛亥革命的目的。然而,辛亥革命順應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推翻了君主專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其歷史功績終究是無法否定的。
這種論斷產生的根源,是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奴化思想在作祟,他們總是認為:君主總是好的,君主受了身邊“小人”的蒙蔽,等等,這是典型的奴才心理在作怪,是給主子打掩護。他們把“新政”抬的很高,目的是企圖否定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是“多此一舉”的結論。由于他們奴化思想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不能認識到專制者的本來面目,愿意生活在專制制度之下為奴為仆。由于奴化思想而缺乏自信,便要千方百計來造神以膜拜,同時還要低估他人的智慧和創造力,不相信人民在擺脫專制統治后,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的更好。這種情況,正是專制遺毒造成的惡果,也是專制者樂于看到的結果,證明專制者實施奴化教育的成功。
二、民主·共和·憲法: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里程碑
革命者從一開始,就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即“創立合眾政府”,并且有明確的政治理論做指導,即“三民主義”。什么是三民主義?孫中山做了精辟的解釋:“簡單地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地說,便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3](P572)三民主義的政治理念中浸透著民主精神,民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君主專制“是惡劣政治的根本”,“必須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4]三民主義所具有的民主精神,成為革命者相互號召以推翻君主專制的旗幟。
民主共和制度是實現民主政治的載體,沒有共和制度,民主就成了空中樓閣。孫中山對民國與帝國的區別有過精彩的論述:“民國和帝國是不同的:帝國是由皇帝一個人專制,民國是由全國的人民做主;帝國是家天下,民國是公天下”,[5](P58)民國的政府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5](P355)孫中山設計中的共和制度,源自美國的三權分立,但比美國三權分立更完美,“在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還有考選權和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2](P359)
民國成立后,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僅存在了三個月,但是大總統負責制、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各行政部門都建立起來了。行政院設置9個部,各部設總長1人,為國務員,協助大總統處理行政,并總理本部事務;各部次長1人,輔佐總長,整理部務,監督本部司、局,以及司局以下之處、科。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宣誓“以忠于國,為眾服務”,第一次樹立了政府“服務于民”、“天下為公”民主政治的現代形象。“君政時代則大權獨攬于一人,今則主權屬于國民之全體,是四萬萬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國中之百官,上而總統,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6](P211)
實現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目標還遠遠不夠,國家機構的運作還需要規范化,這就需要制訂憲法以實施憲政。孫中山對憲法下了這樣的定義:“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從中國數千年來君主專制的歷史來看,專制者都是金口玉言,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所謂的“法律”,不是為了保障人權,而是為了限制人權。孫中山指明了憲法的精神在于“法治”,這是對“人治”的否定和超越,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武昌起義后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是一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文件,被認為是民國憲政的開端。稍后制訂實施的《臨時約法》,是民主共和制度正式確立的標志。有學者認為,《臨時約法》規定了主權在民的原則,提供了與人治、綱常禮教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是一部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憲法性文件。[7](P14)它不但是民主政治的保障,還是共同遵守的社會契約,即使高高在上的總統,“不過國民公仆,當守憲法,從輿論。”[8](P110)“國會議員,不過國民之公仆,并非有何神圣,茍其瀆職,即須受法律之制裁。”[9](P645)政府的運作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唯一的依據,帝王、人主、天子、君父已被時代所拋棄,成為人民的公敵。
可見,辛亥革命從一開始就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有著成熟的政治理論做指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的重大積極成果。雖然這個道路步履艱難,但它畢竟是保存下來了。民國成立后,革命者頒布了憲法,推行了憲政,規定了公民行使民主的范圍,并約定憲法要相互遵守,民主共和政治從而得以實踐。民主、共和、憲政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說明辛亥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里程碑。
三、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民主政治的直接結果
辛亥革命承載著數千年的歷史包袱,寄托了沉重的歷史使命,而能夠在中國實現了以民主、共和、憲政為內容的民主共和制度,說明了民主政治的普適性。民主共和政治的實踐,打破了神秘化的君權專制,否定了“圣靈社會”的宿命論,開辟了一條中國政治的現代化之路,使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第一,民主政治創造生動活潑的政治氛圍。在民主共和的環境下,政黨社團如雨后春筍蓬勃興起,僅1912年間,各種政治性的團體就出現了300多個,其中在民政部備案的有22個。[10]這是政治權力下移的反映,是公民參政意識增強的表現。專制體制下的政治是科舉而仕,共和體制下則是政黨而仕。專制政體打擊和排斥政黨,共和政體則需要政黨。民國時期的競選活動,多采用公開演說的方式,茶館、酒肆、廣場等公共場所,都可以見到競選者或演說者的身影。“你方唱罷我登場”,表面的“混亂”體現的是君權的崩潰、個人崇拜的破滅,體現的是社會的公平。1912年的全國大選中,登記的選民占全國總人口的10%,[11]雖然這個數字還微不足道,但與1908年清朝資政院和咨議局選舉時0.4%的比例相較,無疑是一個大的飛躍。
第二,民主政治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和諧的條件。有資料顯示,從1912—1918年,短短7年時間,中國新建工礦企業470多家,投資將近1億元,加上對原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的資金投入,合計新增資本在1.3億元以上,相當于辛亥革命前50年投資的總和。在輕工業發展的同時,重工業也得到較大的發展,如1914年建立了湖北大冶鐵廠等6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了龍關鐵礦公司,1917年建立了上海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建立了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等。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迅速出現“棉紗大王”、“面粉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鋼鐵大王”,民國初年成為民族工業發展最輝煌的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實施和政府頒布的一系列鼓勵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和法令。
第三,民主政治意味著打破奴化思想的束縛,對各種文化和思想流派采取寬容的態度。民國初年,集會、游行、示威、結社、選舉等活動成為公民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政黨和社團紛紛成立。民眾還通過創辦報紙和雜志,組建通訊社等形式,積極參政議政,許多報紙以評說政府官員、議論時政得失、監督政府工作為己任。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更是打起了“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向專制和愚昧宣戰。
第四,民主政治為全新的社會生活方式開路。民國政府廢除了跪拜、作揖、請安、拱手等舊式禮節,廢除了“大人”、“老爺”之類的稱呼,代以官職或“先生”的稱呼,反映了上下尊卑的觀念已被平等的觀念所否定,使人們從愚昧的等級觀念中解脫出來。“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以卑賤、頹廢、放蕩行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滅了……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換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12](P99)
這些社會變化證明民主政治不但生根發芽,而且開花結果了。有人認為,“歷史證明,西方的競爭性政黨政治制度與模式在中國是行不通的。”[13](P127)但是,上述事實恰恰證明他們錯了。他們片面強調中國的“國情”,任何悖理的東西都以“國情”堂而皇之來搪塞,如此一切都無需再解釋便都成了合情合理的東西。他們認為,議會制度和民主制度在中國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條件”。他們這樣說的目的,令人實在不解其中的真義,莫非是要中國回到君主專制的老路上去?
四、民主文化的普及和深入: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歷史使命
有論者認為,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職位移交給袁世凱,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因此辛亥革命是“失敗”了。這種觀點至少存在幾種錯誤:第一,判斷一次革命的成功或失敗,首先應該確定一個衡量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應該是誰在掌握政權,而應該以革命者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否實現為標準。事實上,辛亥革命“創立合眾政府”的目標是實現了的。第二,袁世凱逼清帝退位立下了功勞,他繼任臨時大總統,是南北雙方公認的,是合理合法的,不是“竊取”革命果實。第三,不是只有革命者才有資格掌握政權,其他人就沒有資格掌握政權。打天下并不一定要坐天下,如果以坐天下為目的而打天下,就會造成權力壟斷,從而剝奪他人的參政權。第四,任何一次革命總要有一個結束,其期限不能太過拉長,辛亥革命也不例外。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職位移交袁世凱,是南北雙方談判的結果,說明辛亥革命已經成功,至于后來袁世凱稱帝,與辛亥革命的成敗已經是兩回事。
袁世凱之“竊國”說,是基于列寧“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的錯誤認識。在他看來,革命成功與否,要看誰在掌握國家政權,政權要掌握在革命者手中才算是成功。因此,受封建正統觀念、英雄史觀的影響,人們對政治權威的崇拜,使政治觀點成為學術結論。
還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務,因而是“失敗”了。這種觀點最早起源于劉少奇在1954年《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當時的革命派是有缺點的……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毛澤東在1956年《紀念孫中山》一文中也說:“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兩位政治領導人都說辛亥革命“失敗”了,其強調的重點是顯而易見的。[14]筆者認為,孫中山等革命者的奮斗目標只是“創立合眾政府”,而不是什么“反帝反封”,“反帝反封”是后人強加給他們的政治任務。退一步講,辛亥革命沒有完成“反帝反封”,那么這個任務今天是否完成了?這恐怕也是個疑問。
辛亥革命實現了“創立合眾政府”的奮斗目標,實現了民主政治,但沒有完成普及民主文化和“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的任務,又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可以舉一個典型事例來說明。
民國初年,戴季陶有一次身穿日本服裝出行,與一老農攀談。老農問其國籍,戴氏自稱“中華民國人也”。不料老農很驚異,“似絕不解中華民國為何物者”。當戴氏告訴他也是中華民國人時,老農竟茫然地說“我非革命黨,我非中華民國人”。事后,戴季陶大為感慨:“中華民國成立已三年矣,而人民智識尚有若是者,則袁世凱之舉動,真無足怪矣。”因此,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迅速敗亡的原因,與其說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倒不如說是接受民主共和觀念的部分政治精英的奮起抗爭。正如當時有同盟會員所言,“革命告成之后,全國靈覺為之震蕩,然大都屬于上流人士,而氓之蚩依然渾噩相安。中國由專制政治驟躍為共和政治,自表面觀之,雖若神速可喜;而自里面觀之,前后陟斷,習慣、根據悉受變動,人情未定,黨見難齊,調和統一,待時尚多。”[15](P479)數千年來,占人口90%以上的普通老百姓被社會邊緣化,他們關心的是柴米油鹽,交租納賦,生兒育女,生活水平始終在低層次上循環,精神方面也由于知識的缺失而沒有更高的追求,至于統治者是皇帝還是總統,他們并無多大興趣。只有當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法保障時,才會考慮奮起而反抗的問題,而這種反抗并無半點民主意識的支配,充其量就是一種本能的行為。
辛亥革命沒有完成普及民主文化的任務,如果要求人們對民主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就更無從談起了。例如,在專制制度下,君主既是家族的首長,又是國家的元首和最高的實際統治者,“家”“國”不分,國家為其一人一家所有。除了君主之外,其他人并無國家可言,連他們本人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君主在理論上擁有絕對的權威,可以對任何人生殺予奪,予取予求。但現實中君主并不是總能做到這樣,原因是君權受到了傳統勢力的制約。專制君主出于其統治寶座“穩定”的考慮,要想方設法拉攏一批人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并千方百計表現出一幅開明的姿態。因此,在君主制度下,除了皇帝之外,他人是沒有自己的“國”可言的。國既沒有,何談“愛國”?所謂的“愛國”,愛的其實是專制者的國,不是自己的國,奢談“愛國”純屬自作多情的一廂情愿。只有在共和制度下,國家才成為一個由公民來自主管理的國家,公民才有了“愛國”的權利。遺憾的是,由于對民主認知的膚淺,別說民初,許多人恐怕至今都不能認識到這一點。
民主文化的普及和民主意識的深入,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章炳麟說:“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16][P760]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專制者費盡心機壓制民智,愚弄人民,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只有通過革命手段,才能推翻君主專制,以求開啟民智。在革命成功后,普及和深入民主文化,更需要在共和制度下,依靠政府的長期宣傳和教育才能實現。可惜的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南京政府推翻北洋軍閥而統一全國后,不久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被完全打斷,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一切專制者都貪戀權力,費盡心機破壞民主,不甘心退出歷史的舞臺,但歷史的潮流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臨時約法》的民主精神鼓舞革命黨人重新整合,繼續斗爭,成為一面有相當號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幟,“使專制暴虐的軍閥感到膽寒,使他們不再敢公然倡導帝制,實行復辟。”[17](P574)相比之下,孫中山等人在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之后,有的讓位,有的功成身退,有的息影園林,有的另有追求,充分體現了革命黨人能夠以身作則,以國家和民族前途為重,能上能下,能進能退,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不以把持政權為唯一目標的寬闊胸襟。這些革命者與袁、張之流兩相比較,善惡美丑,自有公斷。要選擇君主還是民主?專制還是共和?也許是辛亥革命留給后人的嚴肅思考。
[1]梁啟超.過渡時代論[N].清議報,1901-06-26.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縣解.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并行[N].民報,第5號.
[5]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夏新華,胡傳晟.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8]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
[9]陳旭麓.孫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0]安靜波.再論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J].學習與探索,1997,(1).
[11]丁三青.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J].史學月刊,1996,(5).
[12]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A].辛亥革命親歷記[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
[13]關海庭.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史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4]徐梁伯.辛亥革命“失敗說”獻疑——兼論史學與政治主導意識同構現象[J].社會科學戰線,1996,(4).
[15]黃彥,李伯新.孫中山先生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后)[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6]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M].北京:三聯書店,1960.
[17]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問昕(1969-),男,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渤海大學政治與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