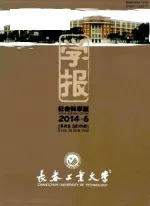開拓與啟航:蔡和森對群眾工作的貢獻
徐德莉
(1.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610061;2.湖南邵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湖南 邵陽422000)
開拓與啟航:蔡和森對群眾工作的貢獻
徐德莉1,2
(1.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四川 成都610061;2.湖南邵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湖南 邵陽422000)
我黨早期杰出的理論家和宣傳家蔡和森同志不僅傳播與宣傳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與唯物史觀,而且為黨的早期群眾工作、路線、方法等做出科學的理論指引,為黨的群眾工作做出重要貢獻。
蔡和森;群眾工作;貢獻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列寧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學的冷靜的態度去分析客觀形勢和進化的客觀進程,同時又能非常堅決地承認群眾(當然,還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階級的聯系,并實現這種聯系的個人、團體、組織、政黨)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并且把這兩方面卓越地結合起來”。[1](P59)馬克思主義觀是我們黨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礎。并通過中國革命實踐不斷中國化。我黨早期杰出的理論家和宣傳家蔡和森同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革命規律的同時,將馬克思的群眾觀傳入到中國來,并建構系統的群眾路線、群眾工作方法做出重要貢獻。
一、提出群眾工作方法——“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
(一)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是由黨的性質和根本任務決定的
蔡和森在《社會進化史》一書中充分論證了這一群眾史觀的基本原理。他根據恩格斯的兩種生產理論指出:“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因有二:一是生產,一是生殖。前者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產,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為人類自身的生產,簡言之即為傳種。人們生活于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各種社會組織,莫不為這兩種生產所規定所限制”。《社會進化史》全書貫穿這一思想,從生產的發展和生產方法的變遷論述了家族、財產和國家的起源與變遷。他指出:“人類發展的大概,經過野蠻時代和半開化時代以至文明時代的發端,每個時代的變化,有每個時代的新特征,而這些特征即直接為生產方法的變遷所引起”。而經濟的進化包括社會的變化,并非全然是自動的歷程,“是要由人們的工作與活動才能完成的”。[2](P78)這些論述證明了生產活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民群眾是生產活動也是社會歷史的主體。
蔡和森在《向導》周報上發表的大量文章中指出:“革命黨當大大宣傳民眾,大大結合民眾,轟轟烈烈地繼續做推翻封建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民主革命”。“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土耳其國民黨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立腳在被壓迫民族的群眾勢力上面”。中國國民運動的要素,“除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工農階級外”,還有“被外資壓迫而不能有多大發展的幼稚資產階級”。國民黨之所以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主要是缺乏民眾基礎,“常常縮頭縮腦不敢出面領導群眾,有時且故意躲避”,如此等等。這些論述對于喚起民眾、對于推動國民黨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蔡和森分析指出,中國歷史的發展要求中國革命要有“新的政黨、新的方法來團結組織各種各派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群眾”,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所應擔負的使命”。蔡和森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十分注重發動群眾、依靠群眾。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他批評陳獨秀“沒有看到正在醞釀著的整個革命形勢,沒有估計到廣大群眾的革命情緒”,堅持以工人階級為中堅,廣泛發動各界群眾,把斗爭引向深入。五卅運動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揭開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也證明了蔡和森群眾觀點的正確性。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夏斗寅、許克祥相繼叛變革命后,蔡和森堅決主張以暴動對付暴動,發動一切工農群眾起來作殊死戰。“堅決的號召廣大的農民群眾以自己的勢力來解決許克祥,……關于湖北……積極號召全省農民群眾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軍閥猛烈進攻……迅速準備廣大群眾勢力推翻國民黨土劣的中央機關”。[3](P45)蔡和森在這里指出肯定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發展人民群眾的重要性。
建黨之初,蔡和森就說:黨“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然則這種黨如何的準備組織呢?照舊組織革命機關,是不中用的。我以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資本家的工廠里去,跑到全國的職業機關、議會機關去。去干什么?去做工,辦事,當代表,做議員。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國各處,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組機關,即以中產階級現成的職業機關、議會機關,做革命機關。這種方法,我得之于布爾什維克”。[4](P24)“嚴格的物色確實黨員,分布各職業機關、工廠、農場、議會等處。”[4](P34)這種組織方法有利于黨打入敵人內部,在內部釀風潮,同時要求黨員也要參預群眾行動,也便于在群眾中做好宣傳發動工作,進行革命斗爭。[4](P24)這種組織方法實際也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方法,雖然他還沒有提出“密切聯系群眾”這個名稱。從蔡和森的敘述中也不難看出,他已指出重視人民群眾的意義所在和系統群眾觀點正在形成。
(二)密切聯系群眾是完成黨的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蔡和森說:“有新的政黨、新的方法來團結組織各種各派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群眾,以使中國革命運動進行到底,并領導無產階級得到解放,這即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所應擔負的使命,所應有的政治的責任。”[3](P17)在大革命時期,蔡和森就認為:“革命黨當大大宣傳民眾,大大結合民眾,轟轟烈烈繼續做推倒軍閻相同際帝國主義之壓迫的民主革命。”[4](P64)關于當時興起的統一論,蔡和森認為要相信群眾,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統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數貧苦群眾的幸福和全國被壓迫民族的對外獨立之上,才能夠真正的統一。”[4](P74)
他提出:“鏟除那種舊軍隊式的組織毛病而改造為自覺自動的群眾黨的組織,鏟除那種機械的宗法的紀律而代之以真正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同時由下而上的黨內討論盡可能的發展,由下而上的選舉制度盡可能的采用,工農同志應盡可能的參加指導機關,黨內事情應盡可能的使黨員群眾知道”,[3](P107)“凡屬一切不壓制群眾意見,不妨害黨的改造的分子,都應盡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來”。[3](P109)為了密切黨群關系,改造好黨,蔡和森還對黨、群各提出一個注意:“黨的機關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眾,不要怕討論或批評。黨員群眾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籠統的反對知識分子,不要籠統的反對一切過去的負責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識分子都是機會主義者,也不是一切舊的負責工作同志都是系統的機會主義者。”[3](P109)從而避免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隨后,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蔡和森系統回顧了黨內機會主義的發展狀況,揭示了其根源,并提出了對黨的改造意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加強民主,密切聯系群眾。因為,組織上的民主,與作風上的密切聯系群眾是統一的:加強民主必然要求密切聯系群眾,密切連聯系群眾是民主的重要反映。
二、蔡和森對脫離群眾思想的批判
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后,在北京召開了黨的第二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討論和決議中就有涉及密切聯系群眾的問題,蔡和森對此是肯定的。他說:“組織問題的議決,主要的意義則是必須把我們黨變成群眾的黨,雖然目前黨員增加到三千多人,但還不夠,而應更擴大數倍。”[3](P64)“固然我們的組織已很擴大,有許多覺悟和正在革命化的分子,團結在我們戰線上來,初時亦與國民黨發生聯合戰線關系,但到‘五卅’運動以后,黨的勢力又擴大到各階級的民眾中甚至于軍隊中,一部分軍隊參加這次革命的聯合戰線,總之在無產階級未成功以前,我們唯一正確的策略就是聯合戰線,唯一的責任就是擴大這個聯合戰線的策略。”[3](P67)“對宣傳工作的決議案,應完全站在革命的觀點上作公開的宣傳,實際上要與群眾發生密切關系,引導群眾到黨中來。”[3](P64)
國民黨叛變革命后,黨為了挽救危局,及時審查和糾正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召開了“八七”中央緊急會議。會議上,蔡和森發言,他批評脫離群眾的家長制作風:“素來黨的指導即未建筑在群眾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遍的政治團體,非階級的指導,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導簡直與國民黨一樣,并且還以小資產階級幾個上層領袖的意識為轉移”,[3](P70-71)“過去黨的家長制到現在已經不適用了,非打倒不可”。[3](P71)他還提出:“我們要相信群眾的力量”,“過去黨的錯誤未傳達到群眾中去,這次的錯誤要傳達到群眾中去,使群眾都認識此錯誤,然后黨才能建立一個新的領導權”。[3](P71)在《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中,蔡和森嚴厲批評了那些輕視群眾、脫離群眾的行為觀點:“自來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他們簡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認有群眾的勢力,所以他們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于外圍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罵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鬧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所以革命數十年,議論卅載,上不能破壞舊軍事組織,解除軍閥的武裝,而反使封建殘局滋乳延長;下不能將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國最深最廣大的群眾,喚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勢力,而坐失了許多可以擴大興奮的宣傳運動之機會,每每失敗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轍,縈情于現成的勢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幫助而不能自己,致使可以膨漲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縮;反蔑視群眾無力,或誣群眾麻木,不知真正為群眾的利益而奮斗而革命,群眾未有不感發興起的。”[4](P74-75)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接受群眾的監督,黨才能保持先進性,才能實現其先鋒隊性質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地位,才能最后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
蔡和森對脫離群眾的作風的批判。他指出:“一九二五年以后,黨即開始成為群眾的,而指導機關仍然沒有群眾化,且漸漸養成一種輕視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眾的習慣。”[3](P106)于是,脫離群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機關領導聽不到也聽不進群眾意見,因為“黨內群眾的政治討論,素來是沒有的,指導機關內工農成分也是沒有的”;[3](P105)其二是不依靠群眾力量,不任用群眾分子,如“指導機關內工農成分也是沒有的”。[3](P105)于是就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而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下級黨部及群眾對于上級機關如果發生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時,上級機關便要認為大逆不道,采取高壓。由此養成“怕群眾”的習慣,黨內事情怕群眾知道,以為如此,將發生異見,動搖指導機關的威信;因此指導機關也愈怕群眾的代表來參加。指導機關與群眾的聯系很不良,不僅隔斷,甚至背道而馳,群眾完全離開黨,黨的指導機關完全拋棄群眾,在天高皇帝遠的深宮之中,做那鐵的組織鐵的紀律的酋長時代的工作。愈做愈沒有黨,愈沒有群眾,愈沒有工作,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刑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之一切自由。”[3](P106-107)彭述之就是這種脫離群眾的作風的代表。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群眾優良作風的積極倡導者,他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為指導,認識到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以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根本任務為根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堅決與脫離群眾的右傾機會主義家長制作風、官僚習氣作斗爭。他是提出科學系統的群眾觀點與群眾工作方法的開拓者,可以說是開啟了黨的群眾工作的航向,引導中國革命時期群眾路線的科學制訂有重要理論作用,即使對于今天黨的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現實與引領意義。
[1]肖前,李秀林,汪永祥.歷史唯物主義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蔡和森.社會進化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3]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蔡和森文集》(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徐德莉(1979-),女,四川大學博士,湖南省邵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講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