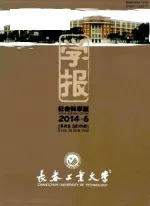規約含義再思考:兼與會話含義對比
冉志晗
(合肥學院 外語系,安徽 合肥230022)
規約含義再思考:兼與會話含義對比
冉志晗
(合肥學院 外語系,安徽 合肥230022)
通過與會話含義的對比,本文探討規約含義基本概念、哲學溯源、學科意義,以及規約含義的本質和一般特征,目的在于把握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的關系,以利對語言意義系統更全面科學的認識。
規約含義;會話含義;探討
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是Grice 1975年于William James系列講座里首次并舉提出的兩個關于意義類型的概念,為語言意義研究帶來了深刻變革。如今,會話含義理論在語言哲學領域獲得廣泛認同,而規約含義的命運與會話含義大相徑庭。很長時間里,規約含義在語言哲學領域遭受忽視、質疑和批判,在語用學領域更是被邊緣化[1]。只是最近幾年,國內外學者才開始關注并探討規約含義主要思想、本質特征和推導機制等。基于會話含義理論在語用學界深入人心的事實,本文結合與會話含義的對比,探討規約含義基本概念、哲學溯源與哲學意義,以及規約含義的本質和一般特征,目的在于把握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的關系,以利對語言意義系統更全面科學的認識。
一、什么是規約含義
與會話含義一樣,規約含義廣為人知始于Grice1975年發表的Logic and Conversation一文。Grice在文中把規約含義定義為與會話含義相對的一個概念。Grice從說話人意圖出發,將話語的意義定義為說話人意欲表達的思想,即“說話人意義學說”(a theory of speaker meaning)。在他看來,自然語言中一句話的意義是一個立體的集合,由所言(what is said)和含義(what is implicated)兩部分組成。所言是句子直接陳述的具有真假值的命題,而含義則是句子在實際使用中產生的不影響句子真假值的、超出或不同于所言的意義,該意義可進一步分為規約含義和會話含義兩個部分。會話含義可以運用古典格賴斯會話含義理論的“合作原則”下的四準則推導出來,但是,規約含義“并不是由像‘準則’這樣的上位語用原則得出來的推斷,而只是依從常規而附在特定的詞項或形式之上”[2](P127)。也就是說,規約含義不需依據合作原則或準則,也不依據特殊語境來解釋,而是與特殊的詞匯聯系在一起。當使用這些詞匯時,便產生言外之意。例如:
(1)a.Mary is poor and she is honest.
b.Mary is poor but she is honest.
以上2個例句的所言相同,由句子的語言形式直接呈現。所陳述的真假值相同,即Mary is poor和Mary is honest兩個事實。但(1)b中but的出現隱含being poor和being honest是兩個對立的現象,這個隱含的對立即是由but所觸發的規約含義。所言依賴的語言形式被稱為句子命題的形式表征,而規約含義依賴的語言形式被稱為規約含義觸發語(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triggers)[3]。規約含義觸發語除格賴斯提及的那些連詞(如but,therefore等)以外,還有表示命題態度的副詞(如perhaps,unfortunately等)和一些由第一人稱代詞I和一個認知動詞構成的插入語(如I think,I reckon等)[4]。
二、規約含義的哲學溯源與學科意義
規約含義哲學溯源遠遠早于會話含義。Grice在其1961年發表的The 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一文中第一次提到規約含義,其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以前Frege(1892)關于涵義色彩(coloring)的討論,這一點鮮為人知[1]。
Frege將語言意義分為所指(reference)和涵義(sense)。所指是客觀存在,涵義是所指的呈現方式(mode of presentation),具有認知內容(cognitive content)[5]。Frege認為,所指相同的兩個表達式的涵義不一定相同。著名的例子如the morning star(啟明星)和the evening star(長庚星)指的是同一天體,但兩者的涵義卻不等同;另外,有時相同涵義的句子傳遞的信息也有細微差異。涵義的色彩還體現在其它一些詞身上。比如still,but,although和yet等。雖然這些詞不影響所在句子的涵義,卻能為句子增添認知或情感等色彩。下面兩例引自馮光武(2008):
(2) a.Mary has still not come.
b.Mary has not come.
(3) a.Mary is poor and she is honest.
b.Mary is poor but she is honest.
c.Though Mary is poor,she is honest.
(2)a和(2)b的涵義相同,但前者隱含說話人對Mary到來的期待。例(3)中,and和but都是連詞,但后者隱含了說話人認為but前后兩個命題之間有某種對立。因此,雖然(2)中各句的涵義相同,但是but和though的出現使(2)b和(2)c有了(2)a所不具有的色彩。
所指(reference)和涵義(sense)之間的劃分是Frege關于語言意義的最為精彩的洞悉。可惜,他的討論到此為止了,因為在他看來,語言的意義只關乎句子的真假值,而涵義的色彩并不影響句子的真假值。半個多世紀以后,Grice不僅注意到了同樣的語言現象,還將它納入意義理論的整體框架去研究。但Grice提出規約含義的主要目的是將會話含義確立為一種“非規約含義”,并且把研究重點放在會話含義上。
Grice會話含義學說一提出就引起學界關注,影響極其深遠,促使人們對意義的哲學探討重心從語言表征轉向心理表征,從而產生語義學與語用學的分水嶺。但是,Grice本人卻很少涉及規約含義,對規約含義的本質也把握不到位,討論不夠系統、深入,后期學者對規約含義也是格賴斯意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基本事實的認識也不夠。關于規約含義的探索長期以來在國內外學者中受到冷遇。Grice甚至出現時而把這種意義叫規約含義,時而把它稱為言語行為的現象[6](P362)。比如,他分析句子smith is poor,but he is honest時指出,說話人實施的第一個言語行為是陳述Smith貧窮和Smith誠實兩個事實,與此同時,說話人還實施了一個將這兩個事實對立起來的高層言語行為(higher-level speech act)。但從他零散的討論中依然可以看出,格賴斯試圖在規約含義與所言及一般會話含義之間劃清界線。在他看來,規約含義與所言不同,因為它不影響話語的真假值;與一般會話含義也不同。因為它完全依賴某些詞語的常規意義,而不需要語境進行推導。
格賴斯認為,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都是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產生,都具有說話人取向性。也就是說,對兩種含義的推導都需要從語言使用者入手,以說話人為中心進行分析。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都與說話人的主觀意識緊密相關,動態中再現說話人意圖或認識,充分體現出語言的意義是對某一認知主體而言的基本哲學精神,符合分析語言的意義應該從語言使用者切入的基本立場。
三、規約含義的本質
規約意義體現為說話人對句子命題的評價或對命題間關系的認識,在本質上是主觀的。規約含義是語言主觀性的一種表現,語言主觀性就是語言可以表現人的自我意識,是說話人將自己看成認知主體的一種表象[3]。為認清規約含義的本質,我們可以將之與所言、會話含義進行比較。
乍一看去,規約含義和所言一樣都和語言形式直接有關,但是它們的本質卻不同。所言是客觀的,例(1)中,Mary是否貧窮,是否誠實,其真假可以通過客觀方式驗證;而規約含義是主觀的,很難通過客觀途徑驗證(平窮與誠實之間的對立純屬個人認知)。可以看出,規約含義是說話人對句子命題或對命題間關系的主觀認識或評價。
同時,規約含義的主觀性以說話人為取向。只要說話人對句子命題有某種認知,就可以使用相應的規約含義觸發語(but,well,although等)去觸發。因而,規約含義的適切條件(felicity condition)只須關照說話人,不關心聽話人是否具有同樣的認知,也不關心聽話人是否接受說話人的評價或認知。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規約含義具有主觀性,但由于具有主觀性的語言形式很多,主觀性不能成為鑒定規約含義的唯一尺度。比如,作為主句出現的由第一人稱代詞I和認知性動詞(如think,believe等)構成的主謂結構,以及主句中的認知性形容詞(如unfortunate,fantastic等)都能傳遞一個人的主觀認知,但它們承載的是句子的命題而不是句子的規約含義。馮光武(2008)曾舉以下例子說明語言形式的意義和規約含義的不同:
(4)a.I think that my wife is having an affair.
b.My wife is having an affair,I think.
上例中,(4)a的命題是一種心理狀態,“我認為我妻子有婚外情”,這一命題由位于主句中的I think直接陳述(而不是隱含)。考證這一心理狀態(我認為我太太有婚外情)是否為真,須要考證說話人的行為,比如他是否檢查或試圖檢查妻子的手機短信,或者是否監視或試圖監視她的行蹤。與(4)a不同,(4)b的命題則是“我妻子有婚外情”。驗證這一命題,須要觀察“我妻子”的行為。位于句末的I think是規約含義的觸發語,但不是命題的一部分,表明說話人對“我妻子有婚外情”這一命題的把握程度不高,但這一心理狀態很難用客觀一致的方法去驗證[4]。
規約含義的主觀性與會話含義的主觀性有所不同。會話含義雖也具主觀性,但并非是說話人對句子命題的判斷,而是聽話人“以話語的語義內容和對一般語言交往的合作本質所做的假設為基礎,經由語用推理所得到的結果”[7](P161)。規約意義由所使用的單詞、詞語本身所具有的規約意義所決定,而會話含義與說話人所使用的單詞及詞語之間的關系是間接的。雖然會話含義依然要以話語的語義內容為基礎,但說話人所要表達的內容遠比其話語的語義內容要豐富[7](P152)。請看下例:
(5)——A:What time is it?
——B:You are late.
在例(5)的對話中,表面上看,由于話語的字面意義和含蓄意義之間的差距,A,B兩人的對話似乎沒有關聯性。A要理解B話語的用意,必須做出一系列的推理。此例中,B可能知道A要去參加一個會議,當A詢問時間時,B通過告訴A要遲到了實際上給了A一個大概的時間。這種推理是基于A,B都愿意把對話進行下去,且以兩人共知的背景和意圖為基礎而做出的。
四、規約含義的一般特征
基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規約含義具有可推導性(calculability)、說話人取向性(speaker-orientation)、不可撤銷性(noncancellability)、非真值條件性(non-truth-conditionality)[4]等一般性特征。其中,前三個特征點與會話含義相同。但是,規約含義不可以撤銷,而會話含義可以因與蘊含(entailment)、背景知識、語境因素等沖突而可以撤銷或分離;同時,規約含義具有真值條件性,而會話含義與命題的真假值無關。
規約含義與會話含義都具有可推導性,但兩種意義的推導過程不同。規約意義產生于句中具體的詞或詞組,不需要考慮語境的因素。而會話含義的推導需要以合作原則為前提,依賴于語境線索。以下重點分析規約含義的說話人取向性,非真值條件性和不可撤銷性。
(一)說話人取向性
規約含義以說話人為取向,體現的是說話人對句子命題的評價或對命題間關系的主觀認識,這一認知來源于說話人,而非聽話人。規約含義的適切條件只須關照說話人。只要說話人對句子命題有某種認知,就可以使用規約含義的觸發語去觸發,而不考慮聽話人是否具有和說話人同樣的認知心理,也不用考慮聽話人是否和說話人持有一樣的關于句子命題的評價、態度或判斷。換句話說,即使說話人知道聽話人有不同的信念、評價、態度或判斷,只要自己有這樣的信念和評價、態度或判斷,就可以說出具有規約含義的句子。聽話人自然就可能挑戰說話人或拋棄說話人的信念和認知心理。請看下例:
(6)Mary is a female,therefore,she is fired.
上句中的therefore觸發了這樣的認知:Mary被解雇和她是女性之間有某種關聯。這一認知源于誰?當然是說話人。
規約含義的說話人取向性在對話中更為一目了然[4]。試對比:
(7)a.Jack has been fired.But he worked so hard.
b.——A:Jack has been fired.
——B:But he worked so hard.
(7)a與(7)b的規約含義相同:Jack被解雇了和Jack工作很努力之間有某種對立。但(7)a是同一個說話人,“被解雇”和“工作很努力”之間的對立性是說話人自己的認識。但(7)b是兩個人的對話,“被解雇”和“工作很努力”之間具有對立性這一主觀認知屬于使用but的說話人B,而A可能有也可能根本沒有相同的認知。
馮光武對自然意義的研究中還提到了規約含義的說話人取向不具有投射性(projective)這一特征[4]。也就是說,當含有規約含義的句子嵌入另一個句子時,規約含義的取向可能發生改變,不一定還是說話人。例如
(8)Mary thought that she is a female,therefore,she is fired.
這句話中,“是女性”和”被解雇”之間的關聯是Mary的認知,但不是說話人的認知。
規約含義的說話人取向性決定了規約含義的認知性。規約含義不是與生俱來的普遍語法,而是隨人的認知能力的提高而培養起來的[4]。關于這一點,Paltiel-Gedalyovich也曾在他的實驗中發現成年人幾乎都能認識到下句中的邏輯問題,孩子們則不能[8]。
(8)Elmo is swimming,but he is wet.
顯然,(8)的問題在于but所觸發的兩個命題之間的對立關系。成年人很容易認識到Elmo在游泳和Elmo身體濕了之間很難形成對立,孩子們卻不能。只有當人的認知能力達到一定水準時才不難認識到but的不恰當性。
與規約含義相同,會話含義也具有說話人取向性。事實上,Grice意義理論本質在于從語言使用者入手去分析語言意義的說話人意義學說。
(二)不可取消性
與會話含義不同,規約含義一旦產生,便不能在同一話語中抹去。格賴斯(1975)認識到規約含義這一特征,但未究其原因[9]。事實上,規約含義的不可取消性是由它的主觀性本質尤其是說話人取向性決定的,因為說話人若要在同一話語中取消自己對某一命題的評價或判斷會使整個話語前后矛盾[4]。但是,Grice只注意到規約含義的不可取消性,卻忽視了這一特征的相對性,因為規約含義可以被聽話人取消,也可以被說話人自己取消[6]。例如:
(9)……A:Fortunately,I did not pass the final exam.
……B:Fortunately?What do you mean?
(10)Mary is a female,therefore,she is talented in language learning.That was an odd idea.Being a femal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being talented in language learning.
(三)非真值條件性
規約含義的非真值條件性是指規約含義對所在句子命題的真假沒有影響的特性[4]。例如:
在例(7)a.“Jack has been fired.But he worked so hard.”中,命題有兩個,Jack被解雇了,Jack工作很努力。規約含義是說話人認為Jack被解雇了和Jack工作很努力之間具有對立性,這是說話人對兩個命題之間關系的認識,即使說話人不認為兩個命題對立,也不能判定兩個命題為假。
據此,含有規約含義觸發語的句子的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定義為:ΣE為真,當切僅當ΣE的命題P為真[6]。依照這一定義,可將(7)a的真值條件具體化為:(7)a為真,當且僅當Jack被解雇了和Jack工作很努力兩個命題均為真。
五、結語
目前,相比對會話含義的研究,國內外語言學者對規約含義的探討還處于較低的水平。本文基于前人對會話含義與規約含義的研究,總結比較兩種含義,歸納規約含義的本質與特點。實際上,繼Grice之后,Bach(1999)、Potts(2005)等一批學者進一步探討了規約含義[10][11],并對Grice的部分理論提出質疑與批駁。但是,如果把規約含義置于格賴斯關于語言意義的哲學思想大背景下去解讀,便不難發現規約含義不僅有其存在的理據,而且有其不同于所言及會話含義的區別性特征。規約含義、會話含義同所言一起,構成Grice語言意義的整體。
[1]馮光武.規約含義的哲學溯源與爭鳴[J].現代外語(季刊),2008,(2)
[2]Levinson,S.C.Pragmatics [M].Cambridge:CUP,1983.
[3]Feng,G.A Theory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and Pragmatic Markers in Chinese[D].Reading: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2006.
[4]馮光武.自然語言的規約含義探索[J].外語學刊,2008,(3).
[5]Frege,G.On sense and reference[A].In P.Geach & M.Black.(eds.).(1960)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2nd edition)[C].Oxford:Blackwell,1892.
[6]Grice,H.P.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7]何兆熊.新編語用學概要[M].上海: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8]Faltiel-Gedalyovich,L.Children’s Knowledge of Non-truth-conditional Conventional Meaning:Evidence from the Contrastive Element of Aval(‘but’)[J].ATL,Hebrew University,2001,(17).
[9]Grice,H.P.Logic and Conversation [A].In Cole,P.& Morgan,J.(eds.).Syntax & Semantics:SpeechActs(vol.3)[C].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1989.
[10]Bach,K.The Myth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J].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1999,(22).
[11]Potts,Christopher.The Logic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M].Oxford:Oxford Wiversiey Press,2005.
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及物性視角下英語新聞語篇批評性分析研究”(編號:2010SK283)。
冉志晗(1970-),女,碩士,合肥學院外語系講師,主要從事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篇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