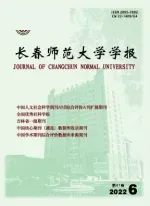和諧社會視野下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轉變分析
周 耕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廣東珠海 519041)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出現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趨勢及其對社會穩定形成嚴重威脅,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具體到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經濟效率不斷提高,傳統的分配機制被打破,社會成員在收入分配方面差距迅速擴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加劇,制約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推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國政府正在調整分配政策,努力實現從“效率優先”到“更加注重公平”轉變。
一、從“效率優先”到“更加注重公平”轉變的理論依據
效率與公平關系是理論界和現實社會生活長期關注與爭論的問題,論爭的焦點主要是二者的優先次序。對此理論界有“效率優先論”、“公平優先論”、“兼顧效率與公平論”、“效率與公平制約論”。
“效率優先論”來自于西方自由競爭的各個學派,他們認為自由競爭是最平等的,反對政府通過行政干預收入的再分配,認為這樣會阻礙經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哈耶克主張公平、經濟增長都可以在市場運行中自發地形成和實現,而旨在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試圖人為地進行收入的再分配,無疑是在破壞公平。
“公平優先論”認為應將公平作為優先考慮的政策目標,市場競爭產生的收入差距過大或兩極分化是最不公平的,效率不是來自于公平而是來自于不公平,最終當不公平的現象普遍發生時,效率的降低也就不可避免了。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寫道: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即公平是第一位的。
“兼顧效率與公平論”認為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利用,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要以生產者達到的產量使消費者得到的滿足程度來衡量。如果生產要素的組合所達到的產量能給消費者帶來一定的滿足,那么,經濟就具有一定的效率。當任何重新組合將使消費者的滿足程度減少時,這就表明經濟處于最有效狀態,這種狀態稱為“帕累托最優狀態”[1]。
“效率與公平制約論”認為二者實際上都不可偏廢,它們之間應當保持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如果平等與效率雙方都有價值,而且其中一方對另一方沒有絕對優先權,那么在它們沖突的方面,就應達成妥協。這時,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并且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無論哪種犧牲都是公正的。”[2]
從歷史的角度看,對公平與效率的現實要求總是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相聯系的,并會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主義者把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作為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理論基礎。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實際上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生產力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影響和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生產力的水平主要表現為效率;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社會關系,其中的分配關系主要表現為產品分配的公平程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依次更替,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也隨之得到相應的變革。不同的效率觀和公平觀,對于其所處的具體歷史時代來說,都具有合理性,但這種合理性不是永恒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總會打破這種合理性。所以,效率與公平并不存在絕對的、永恒的、一成不變的“誰優誰先”的次序問題,兩者主次關系的變化始終根據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正因如此,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了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不斷提高效率的同時實施社會公平發展戰略,中共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中共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二、從“效率優先”到“更加注重公平”轉變的現實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效率與公平分配原則上的政策性選擇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形成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生活資料的分配原則是平均主義,工農業產品在全國范圍內統購統派統配。在當時實行相對平均分配,極大激發了廣大群眾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的種種弊端束縛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制約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自1978年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沿襲了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方式和原則。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改革目標,計劃和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社會主義最終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貧窮和落后,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率。
與此相適應,分配領域的改革必須進行調整。1993年,中央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一原則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當時,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剛剛開始,市場經濟因素只是初見端倪,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原則恰恰順應了這一歷史發展的趨勢,在這樣一種情形下具有無可爭辯的歷史合理性,并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有助于人們沖破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確立經濟領域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形成市場經濟;
第二,有助于沖破平均主義式的、絕對的平等觀,充分地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多勞多得,將分配狀況同每個人對經濟效率的實際貢獻直接聯系起來;
第三,在客觀上印證了發達的經濟基礎對于實現真正公平的社會的極端重要性。
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一個社會才能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為社會公平的充分實現提供必須的方式和途徑。[3]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大幅提升,經濟保持平穩快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在經濟增長的背后,貧富差距的拉大也越來越突出,已經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國家統計局信息顯示,2005年我國基尼系數突破0145,2006年達到0147,超過了所有的歐洲國家。而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129,因此解決貧富差距拉大問題勢在必行。基于貧富差距拉大的實際,中共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隨后,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特別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胡錦濤作報告時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黨代會報告將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提上日程,意味著廣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將會提速,有利于縮小令人不安的貧富差距。由此可見,現在已經到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淡出的時候,“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則更符合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首先,如果繼續按照“兼顧公平”的原則去做,那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難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是“共同富裕”。“惠及十幾億人口”、“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是黨和政府對中國人民所作出的鄭重承諾。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從現在起著手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否則,這句承諾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中國民眾實際生活水準的普遍提升將成為泡影。如果只把公平放到一個“兼顧”的位置,那么這就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可以不遵循公平的規則、機會均等的規則和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的規則來謀求經濟效率。于是,種種非法的“致富”方式便會流行于社會中。其后果是妨礙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并且經濟效率將會因陷入一種無序的狀態而缺乏可持續性。[3]其次,如果繼續按照“兼顧公平”的原則去做,其結果必然有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因為就一般情況而言,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問題就越多,社會就越不穩定。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狀況,就會發現凡是基尼系數過高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都存在著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的情況。
由此可見,“更加注重公平”的提出并不是因為公平天生就是第一位的,而是基于對我國經濟社會現實的審慎考量,是實事求是的結果。從以上對效率與公平的政策性調整看,在不同的時期,效率和公平地位在不斷發生變化,而每一次調整都最終取決于經濟實踐的客觀要求,而不是直接依據各種所謂絕對的“優先論”。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提到貧富差距問題時,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4]顯然,現在已經到了認真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問題的時候了。圍繞著這一問題,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去做,其中一項重要的事情便是不失時機地改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把“更加注重公平”作為今后開展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三、從“效率優先”到“更加注重公平”轉變的現實意義
公平、公正對于整個社會乃至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隨著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進程的推進,公平、公正的作用越來越凸顯。為了社會成員和諧地生存和更好地發展,為了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為了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我們必須有“更加注重公平”的共同準則。只有把“更加注重公平”視為整個社會的制度設計和安排的基本依據,才有利于把我國建成一個人人共享、發達、公正的和諧社會。
我們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的發展應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以人為本的發展應具體表現為社會成員對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是基于社會公平與分配合理來講的。不是基于平均主義來講的。事實上,共享發展成果是在允許有差別的條件下,能夠使所有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這里的共享不等于平均分配,而是根據不同人的貢獻和需要來合理、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5]也就是實現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會發展。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的公平觀、公正觀是不同的。而且隨著歷史進程的推進,公平的含義也在逐漸豐富,并且越來越關注“人”自身的發展要求,越來越具有人文關懷。因此,就涉及到一個極為簡單的但卻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常識性道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是實現真正的公正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只有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一個社會才能具備相應的社會經濟資源,才能為社會公平的實現提供必須的方式和途徑。發達的物質基礎是真正的公正社會的支撐構架。馬克思、恩格斯在談論公正社會時,總是把高度發達的物質條件作為最重要的前提條件。“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鄧小平也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視為現實公平的根本前提。經驗證明,在生產力落后的條件下,也就是社會經濟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不可能出現一個真正的公平社會。如果要刻意地制造一個公平社會的話,那只能制造出一個貌似“平等”的平均主義社會。就本質而言,平均主義也是一種剝削,是貢獻小者、能力弱者對于貢獻大者、能力較強者的一種剝削。在這方面,中國曾有過慘痛的教訓。因此,我國若想建成一個真正的公平社會并避免重蹈平均主義的覆轍,就必須重視社會公平得以確立的前提性條件——大力發展生產力。可見,我們需要這樣一個發達的公正社會。
公平是人類社會永恒的追求,但公平的實現永遠都只是歷史的、具體的。追求效率的結果將使人類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地位上都逐漸趨于公平與和諧。社會公平程度的改善也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和保證,這樣才能激發每個勞動者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積極性。因此,只有基于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狀況的審慎考量,運用發展的眼光靈活地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才能把我國建成一個人人共享、發達、公正的和諧社會。
[1]陳鍇.效率與公平關系新論[J].延安大學學報,2006(5).
[2]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抉擇[M].王奔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2,80.
[3]吳忠民.社會公正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390,391,401.
[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鄭功成.科學發展與共享和諧——民生視角下的和諧社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