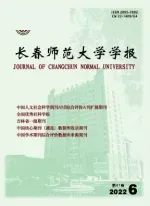拋棄理念的幻覺: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涵義
安麗霞
(長春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吉林長春 130032)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曾因其經典語句“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1]序56而備受爭議。很多觀點認為黑格爾的哲學充滿了極權主義,黑格爾本人也因此成為保守主義形象的代表。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沒有簡單地為黑格爾的哲學下結論,而是用犀利的語言揭示法哲學與宗教在“虛構”方面某種驚人的一致性。馬克思指出,不僅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就連整個德意志社會的政治與意識,也是不顧及現實的人本身的。
一、黑格爾的“理念”世界:國家與理性的一體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宗教與理念世界進行了某種區分,在他看來,“如果虔敬是真正的虔敬的話,那么,當它離開內心生活而進入理念所展開和理念所揭示的華富那樣一種光明之境,并且本著對上帝的禮拜對自在自為地存在的、凌駕于感情主觀形式之上的真理和規律表示崇敬的時候,它馬上會放棄這一感情領域中的形式。”[1]序58
這種崇敬或許來自于黑格爾在對理性不斷追問中產生的某種信仰。黑格爾把理念的研究看成是哲學的任務,他認為“哲學所研究的是理念,從而它不是研究通常所稱的單純的概念。相反地,哲學應該指出概念的片面性和非真理性,同時指出,只有概念 (不是平常聽到那種稱做概念的、其實只是抽象理智規定的東西)才具有現實性,并從而使自己現實化。”[1]1
如果說哲學是現實的學問,那么在黑格爾看來,現實只有在概念中實現自身,只有在概念中才有現實。至于概念怎么就可以設定現實性,黑格爾用了否定的說法:“除了概念本身所設定的這種現實性以外,其他一切東西都是暫時的定在、外在的偶然性、私見、缺乏本質的現象、謬妄、欺騙等等不一。”[1]1
這樣看來,現實一定就是具有永恒性、必然性的東西。這樣的存在在黑格爾看來就是理性,或者說理性就是現實性。“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1]序58
在黑格爾那里,理念也好,概念也罷,都只是手段,目的是為了揭示蘊含于存在事物中的理性。哲學家是理性的記錄者,在理性之外,哲學不能設想,也無法預見,“如果它的理論確實超越時代,而建設一個如其所應然的世界,那么這種世界誠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見中,私見是一種不結實的要素,在其中人們可以隨意想象任何東西。”[1]序58
依照這個觀念,黑格爾提出,他的《法哲學》所研究的國家學,“就是把國家作為其自身是一種理性的東西來理解和敘述的嘗試,除此以外,它什么也不是。作為哲學著作,它必須絕對避免把國家依其所應然來構成它。”[1]序57-58
這里存在著兩種理性:“作為自我意識著的精神的理性和作為現存的現實世界的理性”[1]序58。黑格爾相信“作為自我意識著的精神的理性”的任務就是要認識和把握“作為現存的現實世界的理性”。“自我意識著的精神的理性”知道要想實現它自身就要與現實世界的理性本身相統一,“兩者自覺的同一就是哲學理念。”[1]序59
兩種理性的同一就是讓現實世界“合理化”,理性和現實既是同一的,它就不會與現實世界起沖突,在它眼中的現實都是可以接受的,“理性也不意冷心灰,因為灰心就會認為現世中的確萬事皆非……”[1]59這樣與現實結合的理性,不偏不倚,規規矩矩,它不能盼望,也不作期待,理性不能超出現實的界限。“正因為在現世中不能盼望有更美滿的景況,所以只好遷就現實,以求茍安。認識所提供的是與現實保持更為溫暖的和平。”[1]59
二、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
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思辨的法哲學”的詭計是顯而易見的:“思辨的法哲學”只在“現存的現實世界的理性”中成為它自身,在黑格爾那里理性本身就是現實性,這就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置疑現實,除非置疑理性本身。在“理性”的幻覺中,人們無論如何都要對現在的事物表示出認同,而哲學在這里的確與它的時代保持了黑格爾的“同一性”。在馬克思看來,一味地讓哲學符合現實,謹慎地不讓哲學超出它的時代,看似最忠實于現實,而實際只是遵循現實之理性,而這一理性卻是無人身理性——置現實的人而不顧,因此它是“抽象而不切實際的思維。”[2]10-11
置現實的人于不顧的不僅是黑格爾的法哲學,這也是馬克思為我們描繪的德意志。或者說黑格爾的法哲學只是表征了這樣的現實,因為德國的政治意識和法意識“最主要、最普遍、上升為科學的表現正是思辨的法哲學本身。”[2]10
所以問題不在于黑格爾用理念抽象化了現實,而是現實早已“抽象化”了。
在馬克思看來,“如果思辨的法哲學,這種關于現代國家——它的現實仍然是彼岸世界,雖然這個彼岸世界也只在萊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實際的思維,只是在德國才有可能產生,那么反過來說,德國人那種置現實的人于不顧的關于現代國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產生,也只是因為現代國家本身置現實的人于不顧,或者只憑虛構的方式滿足整個的人。”[2]10-11
在這里,與其說馬克思批判的是黑格爾的法哲學,不如說是對“只憑虛構的方式滿足整個的人”的現實進行批判,因此“對這種哲學的批判既是對現代國家以及同它相聯系的現實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對迄今為止的德國政治意識和法意識的整個形式的堅決否定……”[2]10
馬克思用極富激情的語言宣布“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這種制度雖然低于歷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對象,正像一個低于做人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劊子手的對象一樣。在同這種制度進行的斗爭中,批判不是頭腦的激情,激情的頭腦。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黑格爾用理念解剖了現實后,又細心地用理念縫合了現實,不過這不是馬克思的風格。馬克思的手術刀是批判,解剖之后也不會縫合,而是一定要把解剖后的現實展現給大家看,如果“這種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視的對象,而是既應當受到鄙視同時又已經受到鄙視的存在狀態。對于這一對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為它對這一對象已經清清楚楚。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2]6
揭露的目的是讓人們不再麻木不仁,不再把他們所處的現實看成是理所當然,“應當公開恥辱,從而使恥辱更加恥辱。應當把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作為德國社會的羞恥部分 (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2]6總之,批判的目的在于必須在“柔軟而又溫暖的天鵝絨中”[3]12尋求種種冷酷的東西,不是要取消人們的慰藉,而是要人們看到慰藉的不可靠。
三、從天國到塵世:馬克思《法哲學》批判的涵義
在致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寫到:“如果說神先前是超脫塵世的,那么現在它們已經成為塵世的中心。”[4]15通過宗教批判,我們可以去除虛無飄渺的神,但對于神的觀念卻不會輕易消失,它重新把我們帶入了神的世界。“的確,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上套了鎖鏈。”[2]12神的這個世界不在別處,就在塵世之中。看來人類通向真正的自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馬克思看來,目前的任務就是找到那個在塵世中心的“神”。馬克思為我們找到的就是黑格爾的“理念”。黑格爾的“理念”同樣給人以現實的慰藉,然而這一慰藉卻往往只能導向對周圍環境虛幻的滿足。不僅僅是馬克思,就連歌德也對黑格爾把哲學和神學結合起來的行為表示不滿。洛維特也認為“黑格爾哲學那貫穿一切的、雙重含義的本質就是:它是一種建立在基督教的邏各斯立場之上的精神哲學;它從根本上是一種哲理神學。”[5]21
然而這種哲學神學在某種意義上同樣是一種真實,它真實地存在于人們的頭腦里。理念的真實在于,當我們認識到它的虛幻之后并不會在我們想要拋棄它的時候就會輕易地消失,人仍然距離自由如此遙遠。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2]4
在這個意義上,剝除理念的幻覺,或許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更加清醒地面對自身以及周圍的世界,“要求拋棄關于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2]4想要讓幻想不再統治自己,只能通過消除對幻想的依賴感。消除對幻想的依賴不在于解釋幻想是怎樣出現的,因為哲學的任務不在于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改造不是盲動,“在馬克思那里,改變世界的意愿不僅僅意味著直接的行動,而是同時意味著對迄今為止的世界解釋的批判,意味著對存在和意識的改變。”[5]127所以法哲學批判的意義在于當人們認識到了理念的虛幻就會不抱有不必要的幻想,就“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2]4就“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2]4
[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美]懷特.分析的時代:二十世紀的哲學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德]卡爾·洛維特.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思維中的革命性斷裂[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