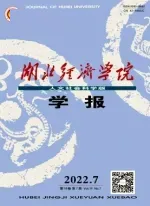愛默生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自然觀
趙謙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安徽 蕪湖 241003)
愛默生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自然觀
趙謙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外語系,安徽 蕪湖 241003)
作為一個文學家和思想家,愛默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雖然他的哲學不成體系,但他仍是按照一定的方法來發展自己的哲學的。從愛默生《論自然》等主要作品中,我們可以總結愛默生對于自然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看法,從而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解讀他的自然觀。
愛默生;作品;哲學;自然觀
一、愛默生與美國超驗主義概述
美國散文作家、詩人和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美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19世紀上半葉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這場文學運動在美國文壇上形成一股進步的潮流,大大地影響了后來的一大批美國文學家,如麥爾維爾、霍桑、惠特曼、狄金森等。愛默生的許多見解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舊沒有失去時效,這一點使人頗感驚奇。他的作品不僅在美國本土廣為流傳,成為美國自由傳統的一部分,而且在世界上也被認為極有價值的一筆文化遺產。愛默生的自然觀對于我們認識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文將從《論自然》等愛默生的主要作品入手,總結愛默生對于自然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看法,從而近一步解讀他的自然觀。
二、從愛默生主要作品看他的自然觀
(一)愛默生《論自然》中所體現出來的自然觀
愛默生于1836年發表的《論自然》,被認為是超驗主義信條的概括。超驗主義在美國思想文化史上意義重大。超驗主義者是反傳統、反權威、反物質主義的浪漫主義者,也是關心政治平等與社會公益的人道主義者。在書中他提出,自然是規律,是最后判決的話,是最高法院,自然是也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方式。
《論自然》的開篇段落標志著愛默生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同時也是美國文學的轉折點。它記錄了他從傳記、歷史和評論轉向自然作為他的起點的時刻。在閱讀《論自然》的開篇語時,很多讀者都經歷了相似的激動,愛默生引導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們不該同樣地保持一種與宇宙的原始聯系呢?為什么我們不能擁有一種非傳統的,而是有關洞察力的詩歌與哲學,擁有并非他們的歷史,而是對我們富有啟示的宗教呢?”[1]P6接著自己提出的問題,愛默生開始陳述我們可以從自然中得到的益處。在第二章《商品》中,他考慮了自然是如何為我們建造的、種植的以及吃的一切事物提供原材料和能量。任何人都會對這些陳述印象深刻:“我們在這個負載著人類飛越宇宙的綠色地球上盡情地開采穩定而豐富的資源。”[1]P12當他贊賞潮汐動力的磨坊時,愛默生想到的是大自然的有用性,他認為,將機器放在海岸上,利用潮汐的沖力轉動輪子碾碎谷物,所以這其中有了月球的幫助,像一個雇傭的幫手來碾磨、搖動、抽水、鋸開樹木或劈開石頭。而且他典型的思維跳躍就是從這一活動遷移到他經常重復的訓諭:“將你的馬車拴到星星上。”但是自然作為物品只是最明顯和有形的益處,很快愛默生轉移到自然的非物質方面的特性。在第三章《美》中,他概述了以自然為根據的一套美學理論。“這便是所有事物的構成之法,或者說是人類眼睛所具有的塑造力量——它使得天空、山巒、樹木、動物這些基本形態,都以其自在自足的方式令人賞心悅目。”他認為自然為我們提供了美的第一和最可靠的標準。“大自然是一片貯存著形式的大海,”他說,而且“美的標準在于自然形式的全部輪回”。這是一個基本命題,一個假設的,一個“首要的結果”。“至于心靈為何要追尋美——在此問題上沒有理性的提問或回答,”[1]P14-20愛默生說。這不可解釋,但其本身卻是其他事物的解釋。
正如自然提供給我們美的標準,《語言》篇給了我們關于語言及語言用途的解釋。愛默生更進一步提出,自然就是語言。“自然是思想的承載體”是他的觀點。一開始,愛默生解釋了為什么“詞語是自然事物的象征”。從最簡單的看,“蘋果”這個詞代表了蘋果這種事物;但其實大多數的抽象概念,如果追溯其來源的話,都會發現是來源于可見的、具體的、有形的事物。“Sierra”意思是鋸子,“supercilious”(目空一切的)來自拉丁文super cilia,意思是揚起的眉頭;“experience”要追溯到拉丁詞periculum,是指從危險中贏得或奪取的東西。所以愛默生在他后來的散文《詩人》中說,語言是化石的詩歌。愛默生下一步的論述是最局限于哲學方面的,也是最難的部分;然而對于作家們來說,這是最激動人心的部分。他指出,一位作家知道,“并非僅僅只有詞語是象征性的;具有象征性的是自然界中的事物。”他還舉例論證,“當一個人在寂靜之中凝視滔滔河水時,他怎能不聯想到世上萬物的變動和流逝呢?往溪水中仍一塊石頭,那不斷增加的波圈就是世事變幻的生動證明。”作家們理解“語言直接依賴自然的這種屬性”,他們所做的是“把外部現象轉化為人類生活中某一部分”[1]P21-26。愛默生所理解的,以及他之后的美國作家能從他那里得到的,是作者與自然之間直接聯系的重要性。愛默生極力推介這種聯系,“在每個有著悠久文明的國度里,都可以找出幾百位作家文豪,他們曾一度深信,并促使別人也相信,說他們見到了,也說出了真理。這些人并非親自用自然的語言來裝飾某種思想;相反,他們是下意識地依靠本國古代作家創造的語言來養活自己,而那些古代作家才是直接依賴自然寫作的。”[1]P24那么語言的本質就是意象,因為這個原因,“優美的文字和雄辯的演說都是些永恒的寓言。”我們喜歡意象并對它積極回應并不僅僅因為語言是一個巨大的意象庫,而且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個語言的取之不竭的上游水庫和源泉。“世界充滿了象征,”愛默生說,“人類所用的語言就是象征,這是因為整個自然正是人的心靈的象征。”[1]P48每個心靈都可以從大自然中尋求素材。
愛默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過程、意圖或觀念先于且決定結果。他的自然觀的最大膽的方面,是他提出自然教會了他看到自然之外的東西。或者更為謹慎的提法是,他認為物質的、外部的自然的美及其相互關聯性會引導他去思考,并研究外部世界的內在規律。“在檢驗自己感覺的真實性方面,我是極其缺乏能力的。在此情況下,我怎么才能知道,自我感覺是否能同外界事物吻合,其間差別何在,獵戶星座是否真的在天上,抑或是上帝在我心靈的天幕上畫出了某個星座的形象呢?”愛默生承認現象是足夠真實的,不管它們是客觀存在的還是只存在于人類意識中,所以他繼續推進自己的觀點,“這是文化的統一效應影響了人類心靈,它在具體的自然現象方面,比如熱、水、氮的存在,并不會動搖我們的基本信念。但是,它卻引導我們把自然看作是一種現象,而不是一種實在,并且誘使我們把必要的生存歸結于精神的力量,而把大自然視為一種偶然事件或效果。”[1]P58
(二)愛默生其它作品中的自然觀
愛默生區別自然內在、不可見的法則與其外在、可見的形式的做法并非首創。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們,尤其是柯勒律治也提出了相似的區分法。愛默生最大的貢獻可能是他關于自然的這兩方面如何相互聯系的陳述。他的畢生精力都是在解釋自然的法則與進程是如何成為人類思想的一部分的,并且在說明人類思想與外在自然的關系。可以說,愛默生是精神方面而非物質方面的自然主義者。大約從1848年起,他都在斷斷續續地研究他稱為“智力的自然史”的課題。像所有徹底的浪漫主義者一樣,也像達爾文等新思想科學家一樣,愛默生理解自然是處于永久的變化或波動中的。“自然界沒有固定的狀態,”他在《論圓》中寫道,“宇宙是流動的,易變的。永久只不過是一個表示程度的字眼。”他把自然理解為一個過程而非一個事物,“這樣,就沒有睡眠,沒有停頓,沒有保存,只有萬物的更新、萌芽和生長。”他把自然看成動態的觀點可以解釋他為什么偏好自然而非歷史。“在自然界,每時每刻都是新的,過去總是被吞沒,被忘卻;只有來者是神圣的。除了生命、變遷、奮發的精神,再沒有可靠的東西。 ”[1]P444-455
所以愛默生堅持認為一切都是流動的——他稱之為 “變質”——他相信多元的,多樣的和具體的,認為內在法則在決定外部現象;而且雖然不是以明顯的方式,自然界中的事物都是統一的、整體的。“大自然的每一件事物都包含了自然的所有能量,”他在《論補償》中認為,“一切都是由一種神秘的材料做成,就像自然主義者在每一種變形中都能看出一種類型。”[2]P125
愛默生自然觀的中心是時刻存在、包羅萬象的人類意識——和有著無限多樣性的外部自然之間的關系。他讀過肯特和史蓋林的著作,當他在《論超靈》中談到“自然的源泉在于人腦”時,他是在回應肯特。他也知道史蓋林的著名觀點:“自然是外化的意識,大腦是內在化的自然。”在《美國學者》中愛默生指出,“自然是靈魂的對立物,其部分與部分都是對應的;一個是印章,一個是印跡。自然的美是一個人心靈上的美,自然的規律就是他自己心靈的規律。所以一個人對自然越是無知,那他對自己的心靈也就越無知。”[1]P66在《論補償》中他寫道:“每一個新形式不僅重復了這個類型的主要特征,而且在每一個相對應的地方重復了其他類型的所有細節,所有的目標、推動力、障礙、能力,以及整個體系。每一種職業、行業、藝術、事務,都是一個世界概要,與其他事物相互關聯;每一事物都是人類生活的完整象征,是人世的善與惡、磨難以及過程與目標的完整象征。 ”[2]P126
愛默生提出的自然與意識之間廣泛的聯系是其著作中不可動搖的中心點,是其基本條件,這也解釋了他為什么選擇自然作為自己的起點。自然是愛默生新宗教神學思想的起點。在《在神學院的演說》中,他對于有組織的基督教信仰的拒絕可以被看成是代表宗教的一種聲明。他提出每個人都具有的“道德情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實質”。對于宗教信仰,愛默生指的是具體的、個人的宗教感受或經驗。“道德情感的直覺是一種對靈魂規律之完美性的洞察。”直覺,對于他來說,就像宗教信仰一樣,是一種實際的、現存的個人體驗。“人不可能憑別的方式領承這種神諭。準確地說,我要是能從另一個人那里得到它,那也不是因為我受到了引導,而是由于受到了激發。對于他說出的話,我必須在心中找到它的真確性,或者拒絕它;如果我把他的話原原本本地接受,我就成為了第二個他,那我就得不到任何東西。”不管他是耶穌或摩西、保羅、奧古斯丁,“我都不能接受。”因此,所謂神諭必須是對我或對你的神諭。“人們逐漸把神諭說成很久前出現的,似乎上帝已經死了一樣。”但是如果真有上帝,愛默生相信,他就應該活在當前。所以他不對間接的神諭、轉述的福音感興趣,因此他從不把《圣經》當作權威,他認為“沒有世俗的歷史……所有歷史都是神圣的”[3]78-89。自然是愛默生通往合乎道德規范生活的實際指引,也是關于事物本質的理論——它是對生活的指導,是哲學、藝術、語言、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基礎。
三、結語
但是盡管愛默生著作繁多,他并沒有什么具體的行動計劃或思想體系。他是一個詩人哲學家,他相信的是靈感,而不是理性,他的演講和文章因此缺乏一種系統性,這一點他也意識到了,而且對此非常痛苦。他不會爭辯,他也盡可能回避對當前的重大事件發表意見,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啟蒙普遍的人性。但在精神和思想層面,他是完全自由的,從個性來說,他也是樂觀的。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他點亮了世界上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心靈之火。他關注的是單個的人,涉及的卻是普遍的主題、宇宙的主題,所以,他的作品至今還仍是清新的,還保持著最初的魅力,并將永遠閃耀在人類精神的天空。
[1]吉歐·波爾泰.愛默生集:論文與講演錄(上)[M].北京:三聯書店, 1993.6-455.
[2]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丁放鳴,譯.愛默生散文選[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125-126.
[3]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孫宜學,譯.美國的文明[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7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