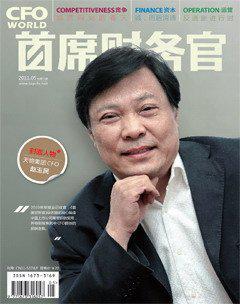從財政挫折中吸取教訓
Ann Wyma
在大宗商品價格高漲的背景下,解決社會需求固然重要,但這必須與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任務相平衡。
過去新興市場從財政緊縮中學到的教訓仍具意義,特別是對發達國家而言。
過去的10年中,我們看到許多新興市場執行了充滿挑戰的財政緊縮政策,即使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仍對應享權益支出采取嚴厲的結構性改革措施,運用反周期性政策并大幅削減公共部門負債。因此,目前最大的20個新興市場的負債率不到發達經濟體的一半。事實上評級機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所以許多新興市場的長期國債評級高于發達國家,特別是高于歐洲非主流國家。
很多國家的財政改善進程是經過多年的努力完成的,期間更是利用了經濟高增長、低利率、充足的資本流和(某些情況下)較高的商品價格等非常有利的經濟狀況。但不需要過深挖掘新興市場的歷史就可以找到被迫采取和實行財政緊縮計劃的例子,因為那些財政政策不可持續、通常采取順周期性政策并最終破壞財政穩定(有時會導致債務違約和重組)的國家已經受到了市場的懲罰。正是這些痛苦的經歷(例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及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為新興市場在近期的財政緊縮提供了一些啟示。
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和歐洲的財政發展提醒我們新興市場的經驗在如今仍有意義。財政挫折最重要的教訓之一仍然是即使已在努力削減短期赤字,但仍需要認識到調整更長期債務的必要性(特別是解決養老和醫療改革以及相關的表外負債問題)。這是從10多年前土耳其的危機所中學到的經驗,如今特別適用于美國。事實上,標普將美國AAA債務的前景降至負面(暗示未來兩年降級的概率為1/3)是因為對政府無法解決中長期預算挑戰的擔憂日益增加。
新興市場歷史上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市場情緒可能突然轉向,并且有時是不可預測的,
特別是在更長期可持續性問題仍沒有明確解決方案的情況下,阿根廷就是個例子。面對希臘債務重組的擔憂加劇以及葡萄牙在芬蘭大選后要接受官方融資援助的命運,市場在今年4月下旬對歐洲非主流國家息差(擴大至歷史高位)的負面反應顯示了類似的動態變化。正是這種惡性循環會最終把各國推向重組道路。
最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有些是以殘酷的方式)已經學到在市場壓力下采取財政鞏固計劃通常更加痛苦,因為政治反對會更加激烈,經濟萎縮會持續更久,并且與采取先發制人的調整相比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走上債務可持續的道路。盡管如此,同意并實施前瞻性的、全面的財政政策通常是說易行難,因為這常常涉及到政治。即使是將財政政策與政策風險隔離的嘗試(如《歐洲穩定和增長公約》)都表明單靠法規并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證。但根據財政鞏固情況來管理政治進程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雖然之前兩周的焦點是工業化經濟體的財政狀況,但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也是時候重溫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因為可以說許多國家的財政政策都過于寬松。解決社會需求固然重要(特別是在大宗商品價格高漲的背景下),但這必須與長期財政可持續性的任務相平衡。目前歐洲非主流國家和美國由于預算狀況緊張而面臨金融市場挑戰,這應該會提醒新興市場決策者們創造財政空間以應對未來潛在經濟沖擊的重要性。如果發達經濟體無法成功應對自身的財政挑戰,這種“未雨綢繆”的儲蓄事實上可能會特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