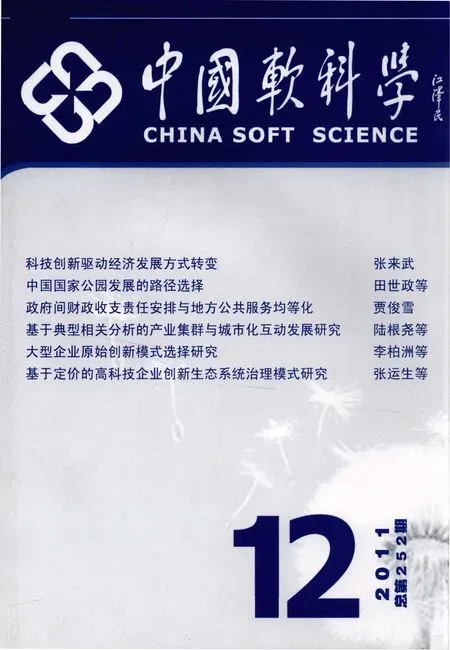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喬小勇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喬小勇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目前,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貿易摩擦已經由企業的微觀層面向政府政策的宏觀層面發展,反補貼已經成為我國貿易摩擦的新熱點,并且國外70%以上反補貼政策實施目標為中國。本研究在構建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的基礎上,運用2004-2009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印度對我國發起的38起反補貼案件及其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相關數據,對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得出相應結論。同時,選取中美2006年銅版紙案件對研究結論進行進一步的論證與說明。
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
一、引言
反補貼是國際間的政府行為、國際間法律訴訟行為、貿易救濟政策之一,它主要針對一國政府的出口補貼政策和生產補貼政策。反補貼的目的是保護進口國同類產品生產商的利益,維護正常的國內市場秩序和國家貿易秩序。與反傾銷相比,反補貼已由企業的微觀層面上升到了政府政策的宏觀層面,反補貼調查的對象涉及一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企業是反補貼調查的直接承受著,并且反補貼政策的實施也容易對被調查國的整體產業、整個區域造成“全面殺傷”。因此,一國政府的反補貼調查機關在對國外出口產品進行反補貼決策時,往往首先考慮本國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貿易等環境,即決策環境。
國內外學者多從法學分析、經濟學分析角度概括提出政治、經濟是反補貼政策實施的主要宏觀決策影響因素。胡麥秀、薛求知(2008)[1]運用兩國貿易模型和福利函數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美國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動機和原因,研究結果表明,國際貿易中的非均衡收益格局是美國對華出口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的經濟動因,而謀求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政治動因。Erna Van Duren和Larry Martin(1989)[2]通過研究指出一些涉及農產品的反補貼案件導致了國際社會的激烈爭辯,并且案件涉及到了相關的法律和政治因素。Kathy Baylis(2007)[3]分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使用對出口國與進口國關系的影響,并指出政治壓力是進行反補貼立案調查的一個主要因素。Anne O.Krueger(1996)[4]通過考察具有民主制度國家貿易政策的決定因素,表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通過一個政治過程實現的,這個政治過程允許最優化的代理人在經濟活動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何海燕、喬小勇(2010)[5]研究了國外對華反補貼指控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指出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貿易順差較大等政治、經貿因素是國外對華反補貼最主要的原因。Jai S.Mah(2003)[6]對在反補貼調查過程中美國ITC的角色和決策特點進行了分析,并運用建立在時間序列數據上的經驗證據表明,進口反補貼決策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有一個長期的均衡關系,這些宏觀經濟變量包括經濟增長率和進口滲透率。此外,部分學者也從市場經濟國家的角度研究其對實施反補貼政策的決策影響,如Loren Yager(2006)[7]作為美國總審計署的發言人,從“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兩個角度分析選擇何種方案對中國征收反補貼稅,并預測了方案實施后可能產生的結果。GilbertB.Kaplan和ChristopherT.Cloutier(2007)[8]針對美國對中國銅版紙發起反補貼立案調查做出了評論,指出這是美國對像中國這樣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發起的第一起反補貼立案調查,對兩國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張斌(2009)[9]通過研究指出,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在對華反補貼價格比較基準問題上也存在一個共同點,即是否適用外部基準取決于各自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或在同一產品反傾銷調查中對市場導向產業認定。
實際上,反補貼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管理、經濟、政治、法律等多個層面,并且反補貼政策的實施也受多個方面的宏觀因素影響。由國內外研究現狀可知,針對本部分的內容在三個方面還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一是,研究方法問題,根據反補貼政策實施的自身特性,可以從系統科學、管理決策、公共政策分析角度,運用管理科學和管理決策方法,深入挖掘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二是,研究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指標具體包括哪些內容;三是,研究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具體指標對一國政府反補貼決策的影響程度如何。目前,中國不僅是全球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也是全球反補貼調查的最大目標國,全球70%以上的反補貼調查是針對中國,因此,本研究在構建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的基礎上,運用2004-2009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印度對我國發起的38起反補貼案件及其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相關數據,對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同時,選取中美2006年銅版紙案件對研究結論進行進一步的論證與說明。
二、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構建
1.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構建的基本思想
線性回歸模型的一個局限性是要求被解釋變量是定量變量而不能是定性變量。但是在許多實際問題中,經常出現被解釋變量是定性變量的情況。Binary Choice Mode是被解釋變量可以為定性變量且被解釋變量只有兩種選擇的模型,即被解釋變量只取兩個值,表示一種決策或一種結果的兩種可能性。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Model應用于被解釋變量為非負整數值的情況,此時被解釋變量通常表示事件發生的次數。Lagged Variable Model考慮了時間因素的作用,使靜態分析的問題成為動態分析的問題,進而提高研究結果的動態性和科學性。
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構建和運用的基本思想為:(1)對于調查的反補貼案件,反補貼調查機關的決策有兩種結果,要么實施、要么不實施,其滿足Binary Choice Mode中對被解釋變量的要求。(2)利用反補貼政策實施的案件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研究反補貼政策實施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反補貼政策實施的案件數量屬于非負的離散變量,其滿足 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Model對被解釋變量表示事件發生次數的要求。使用此模型時,值得注意的是,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研究時間長度應符合模型的要求,不應太小。(3)如果獲取的案件樣本數據對于兩個模型的要求都符合,那么就可以利用以上兩個模型共同驗證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這樣可以提高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4)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廣泛存在著滯后效應問題,某些經濟變量不僅受當期各種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過去某些時期甚至自身值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研究時考慮了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滯后變量,從而從動態分析角度來進行分析與研究。
2.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樣本及變量的選取
本研究采用2004-2009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印度對我國發起的38起反補貼案件為研究對象,從而更好地為我國反補貼調查機關提供借鑒。從中華人們共和國商務部貿易救濟網獲取的資料可知,這38起案件已有32起做出肯定性終裁。在分析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時,將每一起案件是否已經做出肯定性終裁(Fi,i=1、2、…、38,表示第i個案件)作為案件的被解釋變量,對其賦值為1和0。對于已經做出反補貼肯定性終裁的案件賦值為1,而將除此之外的情況賦值為0。表1為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終裁情況表。

表1 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終裁情況表
反補貼調查涉及政府的宏觀層面。由反補貼自身特點以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反補貼實踐的特征和趨勢可知,宏觀影響因素對于反補貼決策結果起到了重要影響作用。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國際反補貼立法與實踐,本研究的關鍵宏觀影響因素包括政治、經濟、貿易等影響因素,其中經濟、貿易等影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轉化為政治影響因素,如是否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經濟增長緩慢、貿易順差持續增長、匯率問題、失業問題等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層面。根據以上分析,本研究選取的關鍵宏觀影響因素指標共六個,其分別為:是否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DMit,此變量為虛擬變量,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匯率同比變動率(ERCit)、貿易差額變化率(TCit)、反補貼政策實施國GDP變化率(GDPCit)、進口滲透率同比變動率(IPRCit)和反補貼政策實施國失業率同比變動率(URCit),其中i表示第i個案件,t表示第t年。
加入WTO之前,許多國家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認為反補貼不適用于中國。但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貿易工作的積極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一旦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得到普遍認可,國外對華反補貼調查將會不斷增多。特別是美國、歐盟、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地區在不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修改國內反補貼法律并適用于我國,這勢必極大影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但是,從目前國外發起的反補貼調查案件來看,在不承認一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對該國使用反補貼政策的主要對象為中國。以上分析表明兩種情況,一是一國被視為“市場經濟國家”,則容易被別國提起反補貼訴訟或實施反補貼實施;二是雖然一國不被視為“市場經濟國家”,但隨著該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等其他原因,也容易被別國提起反補貼訴訟或實施反補貼實施(如中國)。因此,作為解釋變量(虛擬變量)之一的“是否承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DMit)”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顯著性并不確定。
從理論上來講,一國國內的宏觀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產業競爭力下降,將使得任何進口競爭都可能對該國國內產業生產、銷售經營情況產生較大的壓力。在此條件下,國內生產商、行業協會等將通過游說或對政府施壓以保護本國國內產業,結果會導致反補貼立案調查案件數量上升,最終做出肯定性的終裁的概率上升。本研究選擇反補貼案件發起國GDP變化率(GDPCit)和案件發起國失業率(URCit)來反映。前者表示案件發起國總產出變動對反補貼政策實施的影響,后者代表案件發起國內部市場需求變動對反補貼政策實施的影響。
從匯率的角度來看,它不單單是經濟層面的問題,在某些方面會涉及到一國的政治層面。比如,美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等。事實上,匯率問題并非是導致中美貿易問題的主要原因,但美國奧巴馬政府并沒有停止進一步要求人民幣升值。并且,在中美貿易關系日趨緊張之際,美國還可能考慮征收人民幣匯率反補貼稅,從而使得人民幣匯率同出口補貼聯系起來。從理論上來講,當進口國貨幣升值時,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下降,這將一定程度上降低進口國相同行業生產商的利潤,進而增加對他們實質性損害的可能性;反之,若進口國貨幣貶值將減少實質性損害的可能性。因此,匯率升高將增加進口國提起反補貼訴訟的可能性。本研究選擇匯率同比變動率(ERCit)來反映。
我國正處于經貿快速發展時期,逐漸崛起為世界貿易大國,隨著我國經貿的快速發展,我國對許多國家處于巨額貿易順差地位,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美歐等發達國家面對這種不利的貿易形勢和迫于國內貿易保護注意的壓力,就會利用反傾銷、反補貼等各種貿易保護手段來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并且,貿易逆差和進口滲透率的上升意味著國內廠商面臨國外的競爭更加激烈。進口滲透率升高,表明進口國產業市場份額的減少、生產規模的縮減和利潤的下降等,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產業對貿易保護的需求將會增加,對政府的壓力也將加大,因而容易增加進口國發起反補貼調查和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可能性。

表2 各變量對實施反補貼政策影響的預測期方向表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以上各變量對實施進口反補貼政策影響的預期方向做出預期,具體如表2所示。
3.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BN-L”組合模型構建
根據“BN-L”組合模型構建的基本思想、樣本及變量的選取,反補貼政策實施宏觀決策影響因素的“BN-L”組合模型如下:
①當被解釋變量為定性變量時,模型為(二項Logistic回歸和滯后變量組合模型):



p由θ來表示,可以得出:

p表示事件的發生概率。
公式(1)中的解釋變量(虛擬變量除外)均為變化率。并且,解釋變量的數據來源主要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OECD,中國海關統計,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商務部貿易救濟網等官方數據庫。此外,模型中回歸系數的意義為,第j個解釋變量增加一單位將導致發生比Ω變為原來的eβj倍。但在該模型中,各解釋變量都是相對指標,在實際中沒有增加一單位的可能性,所以,通過轉化即可發現,當第j個解釋變量增加0.01單位時,將導致發生比Ω變為原來的e0.01βj倍。
②當被解釋變量表示事件發生次數時,模型為(負二項分布和滯后變量組合模型):理論上,泊松模型是概率論中一種常用的離散型概率分布,其分布的參數λ為衡量單位時間內隨機事件的平均發生率。以CVit表示i國在t年對中國發起的反補貼數量,CVit去非負整數值,是一種典型的離散型計數模型。本研究使用泊松分布計數模型擴展到負二項回歸計數模型來進行分析與研究。


由于泊松分布的特點,被解釋變量的期望值和方差是:

于是,可由對數似然函數最大化得到參數β的估計。根據公式(5)和(6)并去自然對數可得到:

公式(7)與計數模型具有一致的形式。泊松分布的假設對模型施加了一些限制,它們在實證應用中經常得不到滿足。如,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均值等于方差,即公式(6)滿足的條件。據此,當離散程度較大時,對泊松模型建議選擇普遍的負二項分布模型,通過引入為觀察到的影響因素vt進入條件均值μt,可將泊松模型擴展得到:

由此可以得出負二項回歸計數模型為:

其中εt為特定誤差或截面單元異方差,且εt=lnvt,exp(εt)服從 γ 分布。由此,i國對中國反補貼的關鍵宏觀決策因素的負二項分布多變量計數模型為:

由上文可知,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廣泛存在著滯后效應問題,某些經濟變量不僅受當期各種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過去某些時期甚至自身值的影響。公式(10)引入最優滯后期m,可以通過計量經濟學中的LR、FPE、AIC、SC、HQ等準則來確定最優滯后期。引入m以后,公式(10)變為:

根據計算結果,給定解釋變量變動1個單位,則i國對中國反補貼的期望值的比例變化為[exp(βk)-1]。通過負二項回歸可計算出參數的估計值 βk,將[exp(βk) -1]乘以100 后變為百分數,可得出各解釋變量對于被解釋變量是否顯著性影響以及影響程度。
三、基于“BN-L”組合模型的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由于國外對華發動第一起反補貼案件調查的時間為2004年,至目前2010年共七年時間,因此當被解釋變量表示某國某年反補貼政策實施的案件數量時,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研究時間長度為7,相對較小且不符合負二項分布計數模型的要求。本研究采用被解釋變量為定性變量時的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研究模型。
1.最優滯后期的選擇與確定
本研究采用被解釋變量為定性變量時的進口反補貼政策實施宏觀決策影響因素研究模型。由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es計算可知,公式(1)中的變量TCit、GDPCit最優滯后期m取值為1。
2.國外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的確定
為了分析結果的有效性和分析過程的簡化性,根據計算的最優滯后值,本研究構建的確定進口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模型為:

根據國外對華發起反補貼調查的38起案件的具體情況,對選取的各項指標數據進行分類匯總,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3.0對各指標進行整體的二項Logistic回歸計算。以下將對回歸的結果進行具體分析。對數似然比檢驗與Hosmer-Lemeshow檢驗是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整體檢驗常用的兩種方法。由表3可知,當模型中含有虛擬變量DM時,模型的似然比卡方統計量為15.941,自由度為6,對應p值為0.014,小于選取的顯著性水平0.05,所以認定該模型是整體顯著的。但表4顯示,Hosmer-Lemeshow卡方統計量為1.947,對應的p值為0.866,大于選取的顯著性水平0.05,即認定模型不是整體顯著的,與表3所示結果相矛盾。由表 5可知,變量ERC、TC-1、GDPC-1、IPRC、URC、DM、CONSTANT的Wald統計量對應的p值均大于顯著性水平0.05,即以上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均無顯著性影響,這與實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吻合,說明模型中某些變量的加入影響了整體的回歸效果。

表3 模型整體顯著性的對數似然比檢驗結果表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

表4 模型整體顯著性的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表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表5 回歸系數估計值及其顯著性檢驗結果表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表6 模型整體顯著性的對數似然比檢驗結果表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

表7 模型整體顯著性的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表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由前面分析內容可知,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的“是否承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DMit)”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顯著性并不確定。因此,本研究剔除變量DMit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由表6和表7可知,在剔除變量DMit后,模型的似然比卡方統計量對應p值與Hosmer-Lemeshow卡方統計量對應的p值均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即認定模型是整體顯著的。
對于二項Logsitic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評價,通常選取統計量 Cox-Snell R2統計量和Nagelkerke R2統計量。Cox-Snell R2統計量類似于一般線性模型中的R2統計量,統計量的值越大表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越高。而Nagelkerke R2統計量是Cox-Snell R2統計量的修正,使得其取值范圍限定為0~1,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模型擬合優度越高,而越接近于0,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越低。表8列出了本次模型回歸的Cox-Snell R2統計量和Nagelkerke R2統計量的值分別等于0.42和0.60,也就是說模型解釋了被解釋變量62%以上的變動,說明該模型擬合優度相對較好。

表8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結果表Model Summary

表9 錯判矩陣表Classification Tablea
根據得到的錯判矩陣表9可知,在6起未做出肯定性終裁的反補貼案件中,有2起案件被正確預測,4起被錯判,正確率為33.3%;在32起做出肯定性終裁的反補貼案件中,有31起案件被正確預測,1起案件被錯判,正確率達到96.9%;模型總體的預測正確率為86.8%,說明模型的預測效果較為理想。
根據表10中Wald統計量及其對應的p值可知,除常數項和變量URC外,變量ERC、TC-1、GDPC-1、IPRC的Wald統計量對應的p值分別為0.032、0.029、0.048、0.030,均小于選取的顯著性水平0.05,說明這四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即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性影響。綜上分析,該模型的回歸方程為:

公式(12)通過以e為底的冪函數變換可得:

由上文可知,模型中回歸系數意義為,當第j個解釋變量增加0.01單位時,將導致事件發生比Ω變為原來的e0.01βj倍。表10中回歸系數估計值及符號的具體分析如下: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變量ERC對反補貼政策的最終實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正效應,影響系數為89.436,表示變量ERC每變化1個百分點時,補貼產品進口國最終實施反補貼政策的概率將變為原來的2.44倍,即補貼產品進口國匯率上升將導致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可能性增大;變量TC-1對反補貼政策的最終實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正效應,影響系數為24.283,表示變量TC-1每變化1個百分點時,補貼產品進口國最終實施反補貼政策的概率將變為原來的1.27倍,即補貼產品進口國與國外存在較大貿易逆差額時將導致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可能性增大;

表10 回歸系數估計值及其顯著性檢驗結果表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變量GDPC-1對反補貼政策的最終實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負效應,影響系數為-55.175,表示變量GDPC-1每變化1個百分點時,補貼產品進口國最終實施反補貼政策的概率將變為原來的0.57倍,即補貼產品進口國國內宏觀經濟形勢較好將導致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可能性減小;
變量IPRC對反補貼政策的最終實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正效應,影響系數為11.896,表示變量IPRC每變化1個百分點時,補貼產品進口國最終實施反補貼政策的概率將變為原來的1.13倍,即補貼產品進口國進口滲透率的升高將導致實施反補貼政策的可能性增加。
綜上所述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1)在補貼產品進口國國內貨幣升值壓力較大、宏觀經濟形勢較為低迷、對外貿易環境較為嚴峻等情況下,其做出反補貼政策的概率將會上升,這充分驗證了之前的猜想,即與表2的預期方向相一致;(2)解釋變量“是否承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反補貼政策最終實施的影響顯著性并不確定,其作為反補貼調查機關的一種自由裁量行為,很容易導致反補貼政策的濫用;(3)進口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為GDP的變動情況、匯率的變動情況、貿易差額的變動情況、進口滲透率的變動情況以及是否承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覆蓋了政治、經濟、貿易等層面。
四、案例分析:中美2006年銅版紙案件中美國對華實施反補貼政策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依據第三部分的研究結論,本部分選取2003-2006年美國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相關數據作為實證分析依據。
1.2003-2006年美國國內的 GDP和 Real GDP總體狀況分析
總體來看,2003-2006年世界經濟發展相對較好且較為穩定。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世界經濟增長率可知,2003-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分別是4.0%、5.3%、4.9%、5.5%。由表11可知,2002-2006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都呈持續增長態勢。實際上,根據2004-2007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的數據可知,2004年美國宏觀經濟總體上運行相對較好,與前幾年相比,可以說實現了從低速增長轉向了穩定增長。2005年,美國經濟仍處于擴張階段,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05年,美國私人消費支出增長3.6%,帶動經濟增長2.49個百分點,仍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勞動力市場狀況繼續改善,通貨膨脹整體溫和,消費價格指數上漲3.4%,與上年基本持平等。2006年上半年,美國經濟走勢穩健,消費暢旺,出口形勢良好,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但是,從2006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經濟開始走入了一個敏感區域,能源價格的上升、短期貸款利率的上漲、房地產市場的衰退使得美國2006年下半年經濟顯著放緩。

表11 2002-2006年美國GDP與Real GDP基本情況表單位:億美元
2.2003-2006年美國國內失業率總體狀況分析
由2007-2008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可知,受國內整體經濟趨好的影響,2003-2006年美國失業率分別為5.8%、6.0%、5.5%、5.1%、4.6%。總體來看,2003-2006年美國失業率呈下降趨勢,且波動較小。圖1反映了2003年1月-2006年12月美國失業率月度變化趨勢,由圖示可知,該期間失業率整體呈下降趨勢,沒有明顯的劇烈變動,且保持較低水平(2008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數據顯示,1960-2007年,美國失業率最高值為1982年的9.7%,最低值為1969年3.5%)。

圖1 2003年1月-2006年12月美國失業率趨勢圖 單位:%
3.2003-2006年中美貿易差額總體狀況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隨著中國經貿的快速發展,中國對美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地位,這也直接導致了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以及美國國內將“中美貿易順差”政治化,從而為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打下了基礎。中美貿易摩擦已經由企業的微觀層面上升到了政府間的宏觀層面。由表12可知,2003-2006年,中美貿易順差額逐年增加,2006年相比2003年增長了 146.25%,年均增長35.04%。
為更好地說明中美貿易順差是美國對華實施進口反補貼措施的關鍵宏觀要素之一,本文研究了2001-2008年中美貿易順差額TS與同期美國對華反補貼次數UCN間的相關關系,由表13可知,雙側顯著性概率為0.003,小于顯著性水平0.01,說明2001-2008年TS與UCN在顯著性水平0.01上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0.888。

表12 2003-2006中美貿易順差額情況表單位:10億美元

表13 2001-2008年中美貿易順差額與美國對華反補貼次數間的相關分析結果表
4.2003-2006年中美匯率總體狀況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近年來,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明顯。從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使得中國出口企業獲得了潛在的價格支持,從而使中國出口商品在中美貿易中獲得了不正當的價格優勢”,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上,每當美國經濟惡化,就會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從而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尋找借口。因此,一方面,僅以貿易順差為由來判斷人民幣匯率是缺乏經濟學基礎的;二是,簡單的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同進口反補貼措施聯系起來是不科學的、不合理的。

圖2 2003年1月-2006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趨勢圖
由圖2可知,2003年1月-2006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呈上升趨勢,尤其是2005年8月以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快速增長,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突出。
5.美國反補貼法對像中國這樣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適用問題分析
在美國國內法中,NME即“非市場經濟”一詞來自“國家控制經濟”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1930年關稅法》有關反傾銷的法律規定中。從最深層次原因來說,NME(Nonmarket Economy,NME)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尋求的一個工具,它的出現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結合。
2005年7月14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議員菲爾·英格利希提出一個內容廣泛的綜合性方案,即《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要求擴大反補貼法的適用范圍,使之可以應用到中國等“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2007年3月,美眾議院通過了旨在針對中國產品征收反補貼稅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該法案要求經美國現行反補貼法的適用范圍擴大至中國等“非市場經濟國家”。顯然,美國在反補貼問題上對中國發難可謂蓄謀已久。
總的來說,在加入WTO之前,許多國家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認為反補貼不適用于中國。但隨著我國加入WTO和對外貿易工作的積極開展,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2004年為36個,2005年為41個,2006年為66個,截至目前已有超過75個國家(地區)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一旦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得到普遍認可,國外對華反補貼調查與指控將會不斷增多。
6.2003-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和GDP的比重分析
通過分析與研究2003-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和GDP的比重,可以從宏觀上把握銅版紙案件調查期內中國出口對美國宏觀經濟的滲透程度。
由表14和圖3可知,2003-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分別為924.7、1249.47、1628.97和2034.72億美元,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比重和GDP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但2006年相比2005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和GDP的比重同增速有所下降。

表14 2003-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和GDP的比重表

圖3 2003-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占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和GDP的比重趨勢圖
通過對中美2006年銅版紙案件反補貼政策實施的關鍵宏觀決策影響因素分析可知:①2003-2006年世界宏觀經濟和美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相對較好且較為穩定;2004年美國宏觀經濟總體上運行相對較好,實現了從低速增長轉向了穩定增長;2005年美國經濟總體處于擴張階段。同時,中美經貿相互依賴關系日漸增強。②受國內整體經濟趨好的影響,2003-2006年美國失業率雖然呈整體下降趨勢,但波動不大,且處于較低水平。③中美貿易摩擦已經由企業的微觀層面上升到了政府間的宏觀層面,中美貿易順差額TS與同期美國對華反補貼次數UCN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④匯率是影響國際收支的重要因素,從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2003年-2006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呈上升趨勢,尤其是2005年8月以后,人民幣升值壓力較為突出。⑤美國將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以及將其簡單的同反補貼貿易摩擦聯系起來是極其不合理的,政治動因是美國對華實施反補貼措施的本質原因。⑥美國將進口反補貼措施適用于像中國這樣的非市場經濟體,拉開了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的序幕,違反1984年喬治城鋼鐵案的判例所確定的原則,具有很強的政策影響效應和示范效應。
[1]胡麥秀,薛求知.美國對華實施反補貼的經濟與政治動因分析[J].南京師大學報,2008,(2):63-67.
[2]Erna Van Duren,Larry Martin.The Role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Countervailing Duty Disputes:Cases Involving Agriculture [J].Canadian Public Policy Analyse de Politiques,1989,(15):162 -174.
[3]Kathy Baylis.Countervailing Dutie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M].British,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7.
[4]Anne O 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5]何海燕,喬小勇.應對國外反補貼指控的舉措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0,(5):20 -29.
[6]Jai S Mah.Countervailing Duties in the USA [R].Economics Working Papers,2003(45).
[7]Loren Yager.U.S.-China Trade Challenges and Choices to Apply Countervailing Duties to China[R].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06.
[8]Gilbert B Kaplan,Christopher T Cloutier.The First Affirmative Countervailing Duty Case against China[N].The Metropolitan Corporate Counsel,2007 -05 -01.
[9]張 斌.對華反補貼價格比較基準:基于美國和加拿大案例的比較研究[J].國際商務研究,2009,(1):10-15.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Key Macroscopical Decision-making Factors for Foreign Countries Implementing Countervailing Policy against China
QIAO Xiao-yo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t presen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trade friction of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microcosmic aspects of enterprise to the macroscopical aspects of government,and the main target of more than 70%of foreign countries implementing countervailing investigations is China.Based on constructing“BN - L”assembled model of key macroscopical decision - making factors,this research draws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by exerting the related data of United States,Canada,Australia,South Africa,India implementing 38 countervailing files from the year 2004 to 2009 and domestic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and making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key macroscopical decision - making factors of foreign countries implementing countervailing policy to China.Moreover,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above obtained are getting further argument and explanation through choosing the file of coated free sheet paper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in the year of 2006.
foreign countries to China;implement;countervailing policy;key;macroscopical decision-making factors
F752
A
1002-9753(2011)12-0024-11
2011-06-23
2011-10-20
國家自然基金項目“中國反傾銷實施效果評估體系與方法研究”(70873007)。
喬小勇(1983-),男,漢族,河南新鄭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政府管理與決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與貿易救濟。
(本文責編:辛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