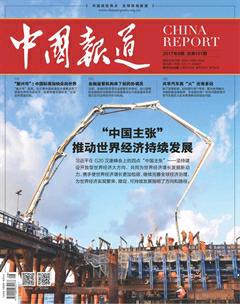“創(chuàng)新中國”攜手“德國工業(yè)4.0”
王鳳娟
中德合作絕不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戲,而是能夠把市場和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得更大,是強強聯(lián)合的明智之舉。隨著“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yè)4.0”深入對接,中德兩國企業(yè)創(chuàng)新理念攜手合作,將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發(fā)展?jié)摿Α?/p>
7月的柏林,風清氣爽,綠蔭掩映中的柏林視覺藝術(shù)中心正在舉行精彩紛呈的“感知中國·德國行”創(chuàng)新中國主題互動展。展覽通過圖文專題和現(xiàn)場科技產(chǎn)品互動,在柏林觀眾的家門口展示了中國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中德兩國在智能制造等領域的合作。
“我對量子計算機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到中國親眼去看一看,學習這項先進技術(shù)。”德國參觀者Georg Engelhardt看完展覽之后意猶未盡地向本刊記者感慨,他正在攻讀計算機專業(yè)的博士學位,對展覽中的科技創(chuàng)新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
創(chuàng)新中國展邂逅柏林
“感知中國·德國行”創(chuàng)新中國主題互動展是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推廣局、國務院國有資產(chǎn)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宣傳工作局主辦,中國外文局中國報道雜志社、《INTERNI設計時代》承辦,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中國航空工業(yè)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等協(xié)辦。
展覽中,中國自主研發(fā)的飛機和高速鐵路模型吸引了眾多觀眾的目光,VR沉浸式體驗“虛擬敦煌博物館”、無人機巡場跟拍、機器人集體舞蹈和3D打印糖果等成為展場的亮點。中國外文局副局長王剛毅在展覽開幕式上說,本次展覽為德國觀眾親身感知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中國打開了一扇窗口。
德國中小企業(yè)聯(lián)合會副會長約亨·勒恩拿德博士說,“德國工業(yè)4.0”與“中國制造2025”緊密合作,肯定會獲得更大的成功。他還呼吁德中兩國中小企業(yè)間加強合作。
“當今的中國在傳承工匠精神的基礎上不斷進步創(chuàng)新,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取得了一批科技創(chuàng)新和制造業(yè)的成果。”中國外文局副總編輯、中國報道雜志社社長陳實表示,希望通過此次展覽為中德兩國合作呈現(xiàn)更多契合點,不斷獲得創(chuàng)新合作的動力。
“這個展覽很有趣,移動互聯(lián)改變著生活,蜂窩物聯(lián)網(wǎng)、智能水泵、智能巡檢、智能交通等大數(shù)據(jù)管理和分析是未來發(fā)展的趨勢。”參觀者Thomas Rahmlow在中國移動的展板前駐足觀看。
“水陸兩棲的飛機很酷,這架飛機如果用于投水滅火是實施救援的神器!”參觀者Leonore J?rss仔細觀看AG600飛機實物模型后說,中國航空發(fā)展真快,機型這么多,期待能親身體驗實物飛機的航空展。
“看完展覽才了解中國石化在節(jié)能減排方面做出了這么多創(chuàng)新的研究,這很棒!”前來參觀的德國夫婦Ulrich Weber和Lynn Weber對中國創(chuàng)新的成就感到驚嘆。
濃縮中國創(chuàng)新成果的展覽令參觀者感慨,不少參觀者表示,這次展覽讓他們感受到了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的巨大變化,“驚喜”“期待”“自豪”“振奮”和“中國制造”“中德合作”等成為出現(xiàn)頻次最高的觀后感。
中德創(chuàng)新的黃金搭檔
2014年10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柏林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主持第三輪中德政府磋商,共同發(fā)表以“共塑創(chuàng)新”為主題的《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共塑創(chuàng)新》,這也是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德國成功進行國事訪問時與默克爾總理達成的共識。
李克強總理表示:“創(chuàng)新實際上是為中德關(guān)系裝上了新的引擎。我們還是應該以創(chuàng)新為引領來加強我們之間的合作,中德創(chuàng)新合作不止于科技,不止于基礎研究,不止于教育領域,更多的可能會表現(xiàn)在我們企業(yè)之間合作,通過市場的合作。”
目前,“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yè)4.0”深入對接,這對中德來說都是發(fā)展的關(guān)鍵時期。中國始終重視工匠精神的傳承與科技的創(chuàng)新,德國也以發(fā)達的科學技術(shù)和現(xiàn)代制造聞名于世,兩國在工業(yè)領域各有所長、各有優(yōu)勢,高度互補。德國擁有先進技術(shù),而中國具有龐大的制造業(yè)市場以及廣泛的制造業(yè)基礎,且研發(fā)人員多、研發(fā)成本相對低。
“中德合作絕不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戲,而是能夠把市場和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得更大,是強強聯(lián)合的明智之舉。”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表示,互利共贏是“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工業(yè)4.0”對接的根本目的。
創(chuàng)新力量正在崛起
近年來,從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到亞太經(jīng)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從博鰲亞洲論壇、達沃斯世界經(jīng)濟論壇年會到“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改革”“創(chuàng)新”“開放”“合作”“包容”等為關(guān)鍵詞的“中國方案”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隨著“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yè)4.0”的深入對接,中德兩國企業(yè)創(chuàng)新理念攜手合作,將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發(fā)展?jié)摿Α?/p>
在前沿技術(shù)領域,世界首臺超越早期經(jīng)典計算機的光量子計算機在我國誕生;在航天領域,天舟一號貨運飛船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順利完成自動交會對接,這是我國自主研制的貨運飛船與空間實驗室的首次交會對接;在航空領域,我國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機首飛成功,意味著我國實現(xiàn)了民機技術(shù)集群式突破,成為世界少數(shù)幾個擁有研制大型客機能力的國家。首艘國產(chǎn)航母正式下水,“華龍一號”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完成穹頂?shù)跹b,海域天然氣水合物連續(xù)試開采60天,創(chuàng)造世界紀錄。一系列重大項目、重點工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彰顯了我國科技實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不斷增強。
航空工業(yè)不斷進行技術(shù)創(chuàng)新,推動工業(yè)化、信息化“兩化融合”和智能制造技術(shù)發(fā)展;中國移動加快5G網(wǎng)絡加速布局,搶占通信技術(shù)革命先機;中國高鐵從技術(shù)引進到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成功研制出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中國石化在芳烴成套技術(shù)、頁巖氣、現(xiàn)代煤化工、生物航煤、地熱及節(jié)能減排領域開展專項行動;“數(shù)控一代”讓傳統(tǒng)制造業(yè)邁向智能制造業(yè);第四代核電高溫氣冷堆擁有獨立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這樣一個個創(chuàng)新點連起來,組成中國閃亮的創(chuàng)新名片,為中國邁向創(chuàng)新型國家行列奠定重要基礎。這些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在國際競爭中由小變大、由弱到強,不僅改寫了世界科技產(chǎn)業(yè)版圖,也成為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新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