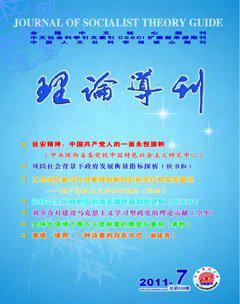全球化語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變與重構
秦勃
摘 要:隨著西方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全球化特征日顯,傳統文官制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由于外部政治環境等諸多因素的激蕩和影響,當代西方文官制度曾經引以為傲的優勢逐漸出現越來越多的弊端,其諸多基本原則面臨新的挑戰,以至于發生嬗變,變革已經成為傳統文官制度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變革的目標是構建一種科學效能的新型文官制度。
關鍵詞:全球化;西方文官制度;變革;公務員制度;科學效能
中圖分類號:D523.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1)07-0101-04
西方文官制度是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體現,是資產階級管理國家事務的有效工具;同時,作為一項管理技藝,它充分體現了節約交易費用的科學價值。盡管在其產生后的100多年間也歷經了曲折與反復,但是它自身所固有的特質使其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在西方各國行政管理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一直沿用至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一場新的科技革命,這場科技革命使西方國家工業化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也沖擊了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許多學者將這一時期冠以各種名稱,如“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全球化時代”等。人們在重視科學技術的同時,也越來越意識到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文官制度在體制機制上亦面臨著新的挑戰,這尤其體現在它的諸多基本原則上。
一、原則嬗變:傳統文官制度面臨的現實挑戰
1.走向交叉互融的兩官分途原則。在兩官分途原則確立之初,西方文官制度體系中政務官和事務官以一種近乎“涇渭分明”的狀態而存在:他們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擁有不同的性質和特征、任期不同、職能相異。然而,隨著文官制度在西方各國的推行,特別是受到新科技革命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激蕩和影響,兩官分途原則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者之間并非完全不可逾越,恰恰相反,他們逐漸呈現出一個相互交融的態勢。一方面,政務官根據自身管理政治事務的現實需要,往往接近和拉攏事務官,在任用上,政治家自主任命大量與自己政見相同的高級文官。在管理上,對失去了文官體制傳統保護的高級文官實行合同制。他們的工作績效主要由政治性的部長和主管來評估。他們為了獲得獎勵,不得不積極響應政治領導人的政策。[1]另一方面,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務官與作為“政策執行者”的事務官并未被生生割裂,相反,他們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政務官在制定政策時為了使政策不脫離實際,往往會向事務官咨詢甚至請教,而事務官也會憑借自己的專業特長、技能經驗等為政務官提供一定的幫助,也就是說,在技術層面,政務官需要得到事務官的幫助。在英國,戰后政府部門最高層次的常務次官,由高級的、高資歷的常任文官擔任,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但撒切爾夫人認為,高級文官長期在政府中擔任要職,形成一個特殊的超穩定系統和人際關系網,他們憑借自己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和實際控制各個部門專業性較強的文件資料,不僅為大臣決策提供信息、咨詢,而且積極地參與決策,甚至實際地控制著決策。為此她決心采用“摻沙子”的做法,適當地改組常務次官的人員結構,打破高級文官一統天下的格局,任命“特殊官員”。如將她的秘書惠特摩直接任命為國防部的常務次官,任命庇特·密特業為財政部首席次官(制定中期財政戰略和金融政策的參與者)。[2]46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于20世紀80年代根據各自的文官改革法案設立了SES(高級公務員系列),在文官系統中建立一個統一的執行官員群體,使得高級文官與政治領導人形成一種“新型關系”,這都體現出政務官和事務官呈現出一種交叉互融的態勢。
2.強化政治傾向的“政治中立”原則。“政治中立”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西方國家維護其根本政治制度的一個技術措施。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西方文官制度中,盡管“政治中立”原則并沒有完全被摒棄,但事實上一些國家的文官試圖打破“政治中立”的樊籬,有的甚至已經突破了這一原則的界限,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化傾向。在英國,國家試圖對文官隊伍加強政治上的控制,撒切爾夫人更是將“政治態度”作為選拔高級文官的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自20世紀80年代初到1987年,白金漢宮中的40位常任次官和135位副常任次官,大多數是由撒切爾夫人與其大臣根據他們的政治傾向而任命的,文官的政治中立原則實際上被其所摒棄。而美國國會兩院更是以政治中立使文官成為政治上的二等公民為由,兩次通過了文官政治權力法案。美國總統為了推進行政改革的進程,往往利用政治任命官員,從而加強了對文官系統的控制。在澳大利亞,政治家與官僚之間及官僚內部的權利再分配,強化了對文官的政府控制。[2]43-44在日本,絕大部分政務官是通過事務官進入政府。特別是政府首腦,大多數都有過從事事務官的職業經歷,至1972年,日本20世紀出任首相的35人中,只有5人沒有擔任事務官或軍官,因此有人認為,日本是文官收買了政黨和政府。總之,縱觀西方各國,事務官對政治越來越表現出一種濃厚的興趣,特別是他們中的高級文官試圖沖破傳統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的禁錮,改變“政策執行者”的角色,朝著“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制定參與者”的角色轉變。
3.打破終身雇傭的文官永業原則。文官職業化和職務常任制是西方文官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和重要特征,也是文官的一項身份保障權利,文官永業原則符合連續性和穩定性的要求,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穩定文官隊伍和吸引優秀人才為政府服務。然而,隨著政府所處環境以及文官制度核心價值觀的變化,傳統的文官永業原則受到挑戰,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這種文官任職的永久性會造成政府組織的功能失調,而且政府組織內部的不協調會帶來許多社會和經濟問題。不斷變動和不可預測的環境要求政府具有更強的適應性、靈活性和高效率,即能夠及時改變規模和策略以應付競爭、財政約束和滿足消費者日益多樣化的需求。于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棄了文官永業原則,簽訂短期或臨時合同的公職雇員日益增長,公共部門使用臨時性、兼職或季節性雇員的數量明顯增加。如英國在1979-1983年之間,實行合同制的政府雇員占公職部門總數的27%。澳大利亞在1989年到1991年間,聯邦政府部門的全日制工作下降了6.4%,而非全日制工作增加了104.1%。美國實行考績制的常任雇員,比例也在不斷降低,已由30年代的87.9%下降為55.5%。[3]近年來,連強調終身制的日本使用臨時工也有大幅增長。至1992年,臨時職工已占日本公務員總數的11.9%強。根據歐洲統計中心勞動力調查,德國非正規錄用的人員,從1985年至1995年10年間增長了12.6%,地方政府非常任人力是常任公務員的6倍。這樣,越來越多的終身職位被取消,使得西方國家文官的管理呈現出多樣化和非職業化的特征,這也在本質上有助于讓更多的組織和人員參與問題的解決。
4.淡化制度剛性的考試任用原則。考試任用是西方各國文官制度得以確立的最顯著、最關鍵的標志,也是西方文官制度最重要的價值體現。在實行文官制度的西方國家,都將考試任用這項原則以法律(法規、規章等)的形式確立起來。如英國于1870年7月4日頒布的關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道樞密院令就明確規定“實行文官考試任用制”;美國于1883年1月16日通過的《彭德爾頓法》明確規定“由人事委員會制定有關考試的具體規定并統一管理文官考試事務”;日本于明治十九年(1886年)制定了官吏考試任用的專門性制度——《文官考試試用及見習規則》。由此可見,西方各國強調考試任用的制度剛性,在相關配套的制度體系中將文官任職條件、考任操作程序等內容以固定的規范確定下來,錄用文官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了。然而,正如前所述,西方國家統治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階級統治往往僭越制度的規范,特別是在人事任免這個重大問題上,更是以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為價值判斷標準,于是就會削弱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剛性,典型的做法就是不經過考試任用的程序直接任免文官;另一方面,出于技術方面的考量,西方國家越來越傾向于將行政職位的一部分特別是高級職位向社會開放,不拘一格招攬優秀人才,這也往往淡化了考試任用的制度剛性。例如,美國的大多數政府機構越來越傾向于到各個大學招聘優秀學生,允許學生在學習期間在政府機構做些有償的工作,畢業后有些人(不經過考試)就可以成為該機構的正式雇員。[5]48當然,所謂淡化考試任用的制度剛性并不意味著摒棄這一基本原則,考試任用原則不管是過去、現在,抑或將來都是西方文官制度中一項重要的基本原則,如果放棄了這一原則,西方文官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二、科學效能:當代西方文官制度重構的趨勢和選擇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西方掀起了一場旨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政府改革運動,它起始于英國和美國,并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擴展和深化,繼而在全球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這股浪潮中,作為官僚體制支柱的文官制度,首當其沖成為改革的焦點。盡管西方各國文官制度的變革在基本形式、具體內容、操作方法等方面不盡相同,但是由于所面臨的問題大致相同,變革還是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通過變革傳統文官制度的痼疾,重構一種科學效能的文官制度,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視系統結構的改革,實現“職品”(職位分類和品位分類)互補。職位分類(Position Classification)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許多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人事分類制度,它實行職位定性分類以及報酬分等與職位掛鉤,強調文官職權與責任,主要特點是“以事為中心”;品位分類(Rank Classification)是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采用的另一種人事分類制度,它以文官的個人條件,如學歷、資歷等來劃分官階、評定職稱與報酬,主要特點是“以人為中心”。職位分類和品位分類都有各自的特點和長處,相應的,也各有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對文官系統結構進行改革時,西方國家一般既保持科學分類的傳統,又根據新的情況予以適當變革,實現科學與效率相統一。如美國1978年通過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打破職位分類的限制,實行“級隨人走”,1986年通過了文官制度簡化法案,在職位分類上,本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把性質相近的職位進行合并。加拿大國庫委員會與文官委員會從1996年開始,通過深入調查后建立了文官通用分類標準(UCS),將未改革前的聯邦政府公務系統72個職組改為29個。涉及管理的職位共5個;專業技術職位共有19個;經濟與社會科學職位有1個;不由工會代表的職位共有4個。[5]針對職位分類過分追求精密性和細致性的特點,漸漸簡化了職位分類的結構體系,重視人對職位的影響,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針對品位分類過分注重建立等級秩序而忽視工作職位對文官的要求等特點,建構更加開放的系統結構,按照專業和工作需要調整文官職組。總之,當代西方各國的文官制度分類呈現出職位分類與品位分類相互補充、交叉融合的新趨勢。
2.完善競爭機制,強調能力主義。在傳統的文官管理中,實行的是常任文官職業制。盡管這樣能使文官隊伍保持長久的穩定和連續,但是它缺乏靈活性,容易造成惰性、僵化的管理體制,于是這種文官終身任用制的優勢已經逐漸變成了劣勢。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斷完善競爭機制,放棄文官“終身制”,打破“鐵飯碗”實行臨時合同制或短期雇傭制。如,新西蘭從1988年開始對文官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內容包括:文官由終身制改為任期制,并根據《雇用合同法》簽訂雇用合同。日本在2001年制定的《文官制度改革大綱》中也明確規定,在某些職位的任用上實行公開競聘,鼓勵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進行人才交流。英國通過擴大招考范圍增加文官錄用的競爭程度,面向社會公開選拔高級文官職位,即便是從內部選拔,也不再進行簡單的晉升,而是引入競爭機制,讓符合條件的人參加競爭,擇優任用。[4]48當然,強調競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吸引和選拔優秀人才以及在在職文官中產生“鯰魚效應”。因此,政府無論是在文官錄用還是在對已被錄用的文官績效評估時都強調文官的素質和能力,能力主義成為改革的價值取向。為了開發文官潛能,推進文官隊伍能力建設,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對文官的培訓。英國圍繞能力標準強化能力培訓,高級文官培訓5年為一個周期,分長期培訓(4周)和短期培訓(3周)兩種形式,培訓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主要采用案例教學、實地調研等方式。瑞士政府將文官在培訓方面所具有的優勢作為穩定文官隊伍、吸引優秀人才的一個重要條件。日本建立了一種文官自我完善的培訓制度,主要是在職培訓(邊干邊學)和脫產培訓。法國所有部級部門都有繼續教育計劃,采取措施對所有文官進行各種培訓,相當于行政機構總薪水水平的6%的資金用于進一步的培訓。[4]49
3.精簡機構,放松規制。文官制度的改革必然會關涉政府職能和規模的調適甚至重構,因此,壓縮政府規模、縮減文官隊伍以及使政府職能達到合理、適度的狀態就成為當前各國文官制度改革的一項共同內容。英國于1981年將文官部縮編改組為官吏及人事局,并恢復財政部人事業務單位,負責經費支援。1977年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在他執政之初,成立了一個由文官委員會的朱爾·休格曼(Jule Sugarman)和聯邦管理預算局的霍華德·梅斯納(Howand Messer)共同領導的“工作組”。提出設立一個全新的“行政職位”,即在利用行政人力資源上給予行政機構領導一定的靈活性與確保對文官的正當保護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6]次年,美國頒布生效《文官制度改革法》,決定裁撤文官委員會,改設人事管理局及功績制保護委員會。隨著機構的裁減,文官隊伍也相應地進行了精簡。1993年克林頓政府發起行政改革運動時,宣布未來五年裁減聯邦政府雇員25.2萬人,節約開支1080億美元,五年來實現裁員35.1萬人,削減財政支出1370億美元,使美國國家財政在連續30年出現赤字之后,第一次有了結余。[7]撒切爾夫人上臺后對英國文官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其中英國文官隊伍總數從1979年的73.2萬人削減到了1990年的56.2萬人,整整減少了17萬人。澳大利亞從1990年至1997年,公務員減少25.7萬人。荷蘭1982年至1989年把總數為16萬人的公務員隊伍減掉2.6萬人。[8]日本政府局級機構1967年為131個,自1980年開始則一直保持在128個左右,中央政府文官1967年為89.9萬人,到1991年只有86.4萬人。[9]
當然,文官制度改革并不僅僅就是簡單的撤并機構、精簡人員。西方國家在縮減政府規模的同時也逐漸放松了規制,下放了權力。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越來越重視成本——效益分析,許多國家甚至師法企業的做法,著力打造“企業型政府”,其核心價值取向就是政府對效率的追求。蓋·彼得斯認為,政府無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對管理層進行預先控制的內部機制和規則的數量太多,它們包括人事規則、僵化的付酬制度、預算規則、具有約束性的采購法規以及許多別的規則。因此有必要清除這些清規戒律,使政府富有靈活性和效率。詹姆斯·威爾遜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美國官僚政治》中指出,放松規制意味著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在該框架下以取得的結果而不是以投入要素作為判斷行為主體的標準。因此,美國的做法是刪除繁文縟節,廢除過多過濫的法律法規,簡化預算和人事審批程序,建立“以結果為本”的新模式。1993年9月戈爾領導下的國家績效評估(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簡稱NPR)發表了名為《從繁文縟節到結果為本——創造一個工作更好花錢更少的政府》的報告。報告認為,政府的繁文縟節窒息了文官的創造力,使他們的工作職能照本宣科。報告指出,一個有效的企業家政府將拋棄繁文縟節,簡化預算和人事審批程序,變循規蹈矩的體制為追求產出的體制。為此,美國政府甚至使用起重車傾倒上百萬和上千萬磅由聯邦人事管理總署所頒發的脫離實際的管理法律與法規,廢除了1萬頁的《聯邦人事手冊》;簡化分類體制和辭退體制;授權給雇員,使其對結果負責;廢除其他規制。而歐洲大多數國家則采用內部市場一類的辦法來代替原先的層級控制。總之,放松規制這一措施已經成為各國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趨勢。
4.重視文官職業倫理,著力建構“道德政府”。西方國家重視文官職業倫理的這個視角突破了過去的只注重從組織結構和立法監督方面進行強化的局限性,而把職業倫理看做是公職人員從事倫理行為、維護公共威信的內在的義務和責任,看做是伴隨文官制度而來的一種內生的必然要求。因此,在西方文官制度變革中,各國把文官的職業倫理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把強調文官的職業道德作為治理腐敗的一條有效路徑,把建構“道德政府”作為文官變革一個主要的手段和目的。為此,西方各國普遍運用組織制度和倫理準則,持久開展公務員倫理道德訓練,完善道德凈化機制。首先,建立和完善關于文官職業倫理方面的法律法規。1993年,美國頒布了《美國行政部門雇員道德行為準則》;加拿大于1994年頒布了《加拿大公務員利益沖突與離職后行為法》;墨西哥又緊隨其后制定了《公務員職責法》。日本于2000年4月實施了《國家公共事業道德法》,在國家人事院建立了“國家公共事業道德委員會”,負責有關涉及公職人員道德的事務。其次,在文官隊伍中灌輸職業倫理觀。由于政府官員每天的工作都代表國家及國家的形象,所以美國自建國之日起,無論是普通民眾、政治家還是法官,都對政府官員在職業道德上寄予很高的期望,特別是在20世紀70—80年代,更是把建構“道德政府”作為聯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在文官隊伍中強調“道德”、“忠誠”、“責任”等。英國頒布的《文官準則》明確規定:文官須“公正、誠實、忠誠、負責、保密、廉潔”;新加坡長期形成了這樣的價值觀念:一個廉潔的政府非常重要,對腐敗的任何寬容都會侵蝕價值體系、背叛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并削弱投資商的信心。再次,把職業倫理作為評價文官素質的一個基本要件。如,加拿大在對文官進行素質測評時就明確規定:“要在測評中體現公共服務組織的道德標準與價值觀內容”。澳大利亞1999年頒布的《公務員法》也強調文官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并且具體細化為14個方面的價值觀念和13條行為準則,以此作為考核文官素質的具體標準。
三、結語
西方傳統文官制度的重構是因應全球化對西方各國公共管理帶來的沖擊的應然選擇,是對舊有的人事管理體制機制、基本原則等諸多問題的糾錯,它科學效能的價值取向為去除傳統文官制度的種種痼疾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路徑選擇。因此,文官制度改革也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再造理論、公共服務理論、企業家精神理論等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無疑對我國正在進行的公務員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價值。
參考文獻:
[1][美]帕特里夏·英格拉姆.西方國家行政改革述[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5.
[2]陳振明.國家公務員制度[M].廈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6.
[3]段余應.各國文官制度及行政體制改革新態勢[J].中國行政管理,1997,(1).
[4]傅興國.當代國外公務員制度改革的趨勢[J].中國人才,2005,(11).
[5]仁宣.加拿大公務員制度創新概況[J].中國公務員,2002,(4).
[6]Mark.W.Huddleston﹠William W.Boyer.The Higher Civi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Quest for Reform[M].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6:98.
[7]田兆陽.美國行政改革走勢.[J].中國公務員,1999,(3).
[8][荷蘭]瓦爾特·基克特.西方國家行政改革述評[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181.
[9]蔣立峰.日本政治概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257.
[責任編輯: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