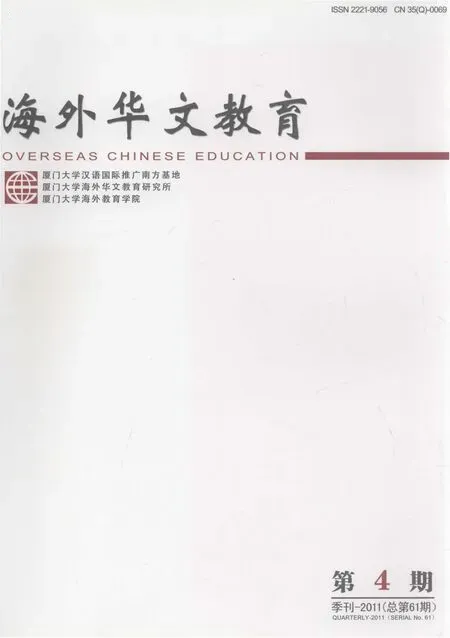建構主義與中高級漢語詞語教學
胡清國
(東華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中國上海200051)
一、詞語教學的難點及研究現狀
對外漢語教學的中高級階段,基礎語法教學已經結束,盡管還或多或少地會遇到語法問題和語法項目,但成系統、大規模的語法教學已經很少。主要的教學任務已經轉移到短文教學和詞語教學上來,甚至可以說,詞語教學是更中心的教學。因為詞語是構建文章、話語的基本材料。離開詞語,文章的教學就成了無源之水。“沒有語法人們可以表達的事物寥寥無幾,而沒有詞匯,人們則無法表達任何事物。”①
張志公先生曾說過“語匯重要語匯難”。詞語教學的困難在于,第一,中高階段的詞語,語義更加抽象,義項更加復雜,同義近義現象大增,學生一用就錯,容易陷入畏難情緒中;第二,詞語數量異常龐大,HSK甲乙丙丁共有8000多個詞語,必須一個一個地學,無法進行類推,學習者無法獲得自主認知結構參與其中的成就感;第三,語體分布的差異明顯,如書面語和口語、通用語和行業語之間的差異,大量保留有古語詞或古代用法的遺留,使用頻率低,增加了學生的記憶負擔。
詞語教學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關于詞語教學的模式探討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眾多方家的關注。主要有胡鴻、諸佩如(1999)探討了集合式的詞語教學模式,呂文華(2000)闡明了語素教學法,馬玉汴(2004)討論了放射狀詞語教學法。他們的名稱不同,內容也有一定差異,但主要的共同之處是利用作為語素的漢字具有較強構詞能力的特點,引出一串相關的詞語,構成一個相關的詞語網絡,建立一個意義相關的詞語組,從而方便學生的理解與記憶,加快他們的學習進程。如“光”這個語素,可以引出“光明、光線、光學、光榮”等詞語,由于有一個共同的語素,這些詞語的意義都與“光”相關,學生可以以“光”為線索,進行理解與記憶。
這些教學模式有理論的支撐,在實際運用中也收到很大效果,但也存在無法克服的問題與困難。無論是放射式還是集中式詞語教學,在教學中勢必為引申而引申,大大超出課文所給單詞的數量與范圍,無形中加重了學生的記憶負擔。況且其中的詞語由于不能在短文中復現,失去了具體語境,學生很快遺忘。看來如何吸取上述教學模式的長處,繼續探索詞語教學的方法和模式的創新仍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課題。
二、建構主義的教與學
建構主義是在對上世紀80年代強調刺激—反應,把知識灌輸給教學對象的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反思與批評中誕生。其最早提出者可以追溯到瑞士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他認為兒童是在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逐步建構其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從而使自身認知結構得到發展。②隨著對人類學習過程認知規律的深入認識,加上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興起與普及產生的與建構主義理論的互適性,建構主義理論在西方逐漸流行開來。并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對中國的教育產生極大的影響。
建構主義強調知識的獲取主要是學習者個體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的認知思維活動主動參與并進行建構。知識僅依靠教師的傳授是無法習得的,必須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于其他人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包括文字、音像、多媒體課件等),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才能獲得知識。所謂意義建構,指的是通過教與學,幫助學生主動地、有效地、深刻地理解與把握學習內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質、規律以及該事物與其他事物的內在聯系,并在學習者的大腦中長期儲存成為知識“圖式”。
總之,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內涵可以概括為“以學生為中心,強調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探索、主動發現和對所學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而傳統教育理論是以教師為中心,強調的是“教”。由于建構主義的教育思想得到了現代信息技術的有力支持,建構主義教育思想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國內外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
建構主義理論的“教”與“學”呈現出如下特征:
1.在教育者的幫助下以學習者為中心,在學習過程中發揮學習者的主體性,自己主動地去進行積極的學習。
2.強調“情境”對學習的重要意義。學習總是發生在一定的背景中,認知與環境有一種必然聯系。特定的環境可以調動學習者已有的學習經驗和認知結構,從而加速學習者對知識的“同化”與“順化”。
3.合作性學習成為范式。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建立學習共同體,通過合作互動獲得自身的認識與情感的發展。
4.調動各種信息資源支持“教”與“學”。為了幫助學習者進行主動探索并完成意義建構,教學者在學習過程中有必要為學習者提供各種學習資源(各類教學資料與教學媒體),但這類信息資源并非主要用于教育者的講解和演示,而是用于支持學習者的自主學習和合作探討。③
三、建構主義理論指導下的詞語教學實踐
建構主義理論尊重學習者的主體地位,強調自我的意義建構在知識獲得過程中的作用,創設有力的環境進行合作學習,對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也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一)教師指導下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詞語教學
語言教學的根本目的是讓學生通過有限的課堂教學,盡可能快地習得漢語,具備聽說讀寫的言語交際能力。這四項技能的教學與學習都離不開詞語,詞語是基礎。
第一,介紹適度,關注數量和容量的問題。中高級階段,每篇課文的生詞量動輒七八十個,甚至上百。數量如此之大,而教學時數相當有限,況且很多詞語的義項如此復雜牽絆,這些都決定了詞語教學應該是有選擇、保重點的教學。這就需要教師根據文章的長度和教學的進度,合理分配,將詞語教學分解到幾堂課中。一般說來,每次20—30左右為宜,④保證經常性的新信息的刺激,這是數量問題。即使對這二三十個詞語,也不能平均用力,也應有所選擇。在我們看來,選擇的標準是詞語的使用范圍、頻率、語體的差異等指標。對于那些使用頻率高,語體運用面廣的詞語應重點把握,反之,則可簡略。例如《現代漢語高級教程》第二課的“倏忽”,就具較強的書面語特點,使用頻率不高,因此就不應該強迫學生能記能寫,一般的識讀即可。
容量是指學習者的大腦器官對信息(指有一定用度的知識)④的處理和記憶可容納的數量。新詞語即是新信息。學習者如果要理解并記憶,就需要在大腦中進行加工,而大腦在一定時間內對信息的處理加工是有一定的數量制約的,當信息量超出能處理的容量時,大腦器官會產生關閉或拒載,表現為學習者注意力難以集中,昏昏欲睡,這些信息就無法借助于短時記憶進入到長時記憶,并最終為學習者的意義建構。
第二,提倡學習者對知識的主動建構。建構主義強調,學習不是由教師簡單地傳遞知識給學生,而應是由學習者自己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這既包括學習者對新信息的意義建構,也包括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對外漢語教學,學習者都已經掌握了第一語言,也已經對外部世界有了相當的理性認識,因此,教師僅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應是知識的提倡者和灌輸者,教師需要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習者調動原有的知識框架去參與新的意義建構。
詞語教學中意義教學可說是中心部分,教學中教師不應該直接告訴學習者這個詞的意義是什么,而應該是為學習者的主動的意義建構提供線索或路徑。如《現代漢語高級教程》第三課生詞“閱歷”,老師提問,“閱”在哪一個詞語中經常能見到,回答是“閱讀”,再問有時老師批改作業會在本子上寫一個“閱”,那“閱”是什么意思,學生會回答“看過”或“讀過”,那“歷”又是什么意思?學生會回答“經歷”,學生在教師的啟發下能得出“閱歷”就是“看過經歷過(做過)”的意思。教師繼續啟發:在下述句子中的“閱歷”是什么意思?
(1)他閱歷太少,還不能當公司的領導。
(2)年輕人應該多到外邊走走看看,增加一點閱歷。
教師提問“看得多做得多”會怎么樣,學生很快說出“就會比別人知道得多或懂得多”,老師歸納“閱歷”還有一個意思是“看過做過之后得到的知識”。這個過程學習者不是簡單地被動地接受新信息,而是主動地利用原有知識參與意義建構。
第三,堅持精講多練。對外漢語教師都聽說過這樣一句話“語言不是教會的而是練會的”。詞語的掌握也不可能教會,只能是練會。學習者必須通過大量的誦讀、反復地操練,通過反射性練習與規定性練習,才能實現自由運用的這一終極目標。有人做過研究,一個新詞語,必須通過7次以上的反復學習才能最終掌握。
因此,我們提倡歸納式的詞語教學,在同義近義的辨析中,通過典型例句,然后由學習者進行推導歸納。例如“所有”與“一切”的辨析:
(3)所有問題都已解決/一切問題都已解決。(所有+N/一切+N)
(4)所有的問題都已解決/*一切的問題都已解決。(所有+的+N/*一切+的+N)
(5)所有同學都必須參加/*一切同學都必須參加。(“所有”后邊的名詞可以指人,一切不可以)
通過要求同學齊讀或者指定同學讀正確的例句,強化初步印象,之后迅速轉入練習,并要求學生能陳述為什么這樣選擇,例如:
(6)世界上的( )生物都離不開空氣。(所有/一切)
(7)我覺得食堂( )的菜都很好吃。(所有/*一切)
(8)明天的晚會( )同學都必須參加。(所有/*一切)
練習完之后再要求大家跟老師讀或大家一起大聲讀,再次建立彼此的意義關聯。
(二)有效情境下的詞語教學
情境性的要求凸顯的是有意義的教學,從有意義的情境獲得知識,比較容易成為不可遷移的知識。緣此,建構主義十分重視情境對學習者意義建構的重要性。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想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即達到對該知識所反映事物的性質、規律以及與其他事物之間聯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辦法是讓學習者到現實世界的真實情境中去感受。詞語學習的真實情境如何呈現?我們認為,必須將詞語置于真實的話語(句子)中,且這些句子是在真實生活中可再現、能使用的。
第一,在句子中學習詞語。詞語的語音和形式可以脫離開話語,但詞語的意義單獨地教授是學習者無法識解并記憶的,更不用說一個詞語有時意義是如此繁多甚至彼此關聯不足。顯然只有在真實的句子中,學習者才能運用原有的知識經驗對新詞語進行同化。趙元任指出:“學詞匯的時候,你得在句子里頭學詞的用法,記的時候,要是光記一個詞等于你本國語的一個意義,那樣子一定學得不對。你得記短語,記句,這樣子意義才靠得住。”⑤例如,學習《現代漢語高級教程》第五課“贏得”這個詞語:
(9)他最終贏得了領導的信任。
(10)經過激烈的拼搶,我們隊贏得了最后的勝利。
(11)小伙子的救人行為贏得了大家的稱贊(贊揚)。
根據句子老師提問“贏得”是什么意思,學生都能回答出“獲得、得到”這樣的正確答案來。進一步啟發,請學生們注意它后面的詞語都是“信任、勝利、贊揚、掌聲、歡呼”之類,一般不能說“贏得了失敗、贏得了批評”,學生很快能判斷:“贏得”后邊所帶的詞語應該是好的意思,說話人希望得到的。
第二,在句子中完成詞語練習。每當學完一些重要詞語,學習者大致理解并掌握了詞語的意義后,應該馬上轉入練習,以鞏固當前的認知。但我們反對沒有任何語境提示的造句練習,提倡做完句練習,多通過提問、場景演示來完成詞語的操練。我們的基本做法是,生詞講練完成(如完句練習)之后,教師布置一個綜合的詞語填空練習,老師不給出詞語,同學們可以翻看生詞表完成檢測。例如:
(12)這件事你必須( )老板的意見,然后再決定怎么做。
(13)一個人如果總是( )別人,那么自己永遠也長不大。
括號里的詞語應該是“征求、依賴”,如果學生用了別的詞語,對了只給一半的分。過一段時間后再進行這樣的檢測,并且要求學生不能查閱書本詞典等任何資料,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解與記憶來完成。學習課文的時候,我們也經常把其中的一些重要詞語挖去,然后讓學生填空。實踐下來,收到良好效果。
第三,倡導互動合作的學習。建構主義主張在教學過程組建學習共同體,通過師生間、生生間的互動合作獲得認知、情感的發展。在建構主義看來,互動合作學習也是一種社會情境,學習者對知識理解的質量與深度只有在社會情境中才能被確定。杜布斯認為,集體的對話的環境可以使個體通過對問題理解的對話,超越和拓展自己的理解和建構。學生可以在對話和交往中調節他們的學習,并且使學習得以持續進行。②
漢語詞語教學如何開展互動合作學習?我們可以組建學習合作小組,不同國家、不同學習水平和能力的學生高低搭配,一個班組建3至4個學習小組,新課開始前的詞語聽寫,由各小組批改,并交由老師最后審閱。詞語的完句練習,各小組內部可以互相討論協商,然后確定一個代表大家意見的答案,小組之間可以互相提問,開展活動。比如我們經常開展的一個小組活動就是一個小組說詞義,一個小組說出該詞語的比賽活動。再如,老師有時通過語素或詞綴進行詞語擴展練習,例如,我們學到了“耳熟”,哪還有什么“×熟”,同學們會搶著回答“眼熟、面熟、臉熟”,學習了“耳饞”,請同學們說還可以說“×饞”,學生會說“眼饞、嘴饞”,老師再稍作解釋。當然,有時學生會有過度泛化或類推的錯誤。有時學到一個詞語中的語素,要同學們課后再查詞典,但上課時不允許再查,然后各小組搶答,小組成員可以補充,如我們學了“消費品”,那老師會問“還有什么‘品’的詞語”,通過小組比賽的刺激,學生可以說很多。
(三)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在詞語教學中的綜合運用
建構主義誕生之后并未能很快產生大的影響,只是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逐漸普及,表現出現代教育技術和建構主義的高度相適性,建構主義理論方流布四方,開始在教育學、心理學等方面產生廣泛的影響。之所以如此,我們認為,建構主義強調基于真實情境的探究性學習,強調學生學習的關鍵是發生在有意義的情景之中,而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正可以通過聲音、圖形、圖像等手段為教育者和學習者營造一個模擬的真實情境,同時,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還能調動學習者的多種感知覺器官(感覺器官和知覺器官的合稱,如眼睛、耳朵為感覺器官,大腦為知覺器官)共同作用,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單一感知覺器官單獨作用的效果遠遠不如多感知覺器官的綜合運用的效果。
第一,聲音、圖像結合創設真實的情境。教師應充分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通過聲音、圖形、圖像等多技術手段,能夠為學習者更有效地創設符合教學內容要求的真實情境,或者為學習者進行意義建構準備必要的搜尋路徑或提示,這就可以更強烈地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加快學習者自身對知識的意義建構。例如《橋梁》(下)第24課中的詞語“嗚咽”,通過視頻技術,可以展示“嗚咽”的圖像,通過視頻,學習者很快地理解“嗚咽”是“低聲哭”。“嗚咽”還可以說成:
(14)林聲嗚咽——笛聲嗚咽——琴聲嗚咽——風聲嗚咽
學習者不容易理解,難道“風也會哭嗎?/琴也會哭嗎?”,此時我們通過進一步的視頻,借助于聲音和圖像的結合,學習者經過對原有知識的提取,理解了此處的“嗚咽”是“帶有悲傷意味的樂器聲或風聲”,但是這種用法不能隨便使用,必須與說話人的主觀情緒和作品的整體氛圍結合起來。
第二,通過圖片進行詞語的講解或效果檢測。詞語教學中,我們常用圖片來幫助學習者理解詞義并進行效果檢測。一幅圖片已經賦予了詞語意義予一定的外在形式,當然這種外在形式只是形似或神似,只是學習者進行意義建構的線索,并不能直接詮釋該詞語,這就需要學習者基于自身的經驗和原有知識框架對新知識進行同化,去主動分析并驗證。每個學習者的知識積累和思考能力并不一致,圖片所提供的詞語的意義線索,就有了較大的張力,學習者可以說出與圖片蘊含相關的許多詞語,正是這不盡相同的意義建構,可以讓學習者共享每一位學習者的思維成果,這不僅有利于建構意義的形成,還有利于建構意義的保持。例如《現代漢語高級教程》(上)的“安慰”和“陶醉”,教師為學習者提供了以下兩幅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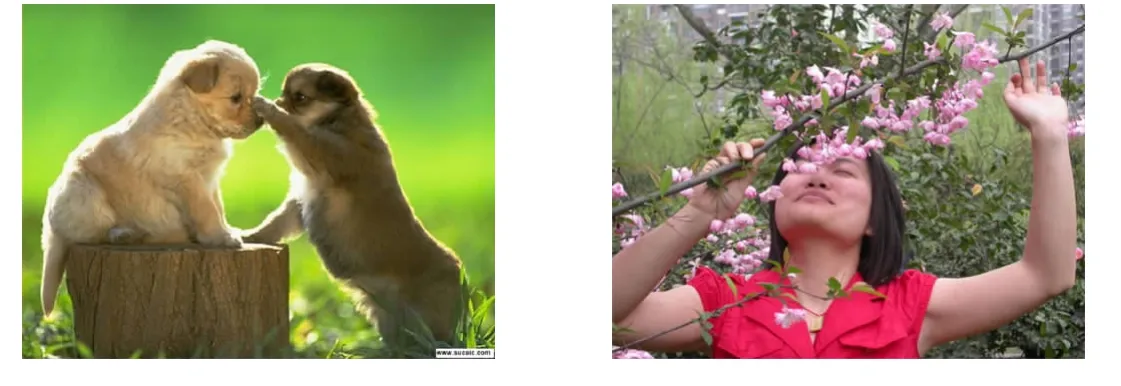
我們選擇圖片的標準是畫面生動,對意義有較明確的提示或指引作用。這兩幅畫大部分同學一見基本都能確定畫面指示的詞語意義,并大致能說出詞語的意義。
注釋:
①王又民:《漢語常用詞分析及詞匯教學》,崔永華主編《詞匯文字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308頁。
②徐輝、辛治洋:現代外國教育思潮研究,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325頁。
③何克抗,建構主義——革新 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http://www.etc.edu.cn……/jiangouzhuyi-gexinjchu.htm,2010年10月20日查。
④徐子亮,漢語作為外語教學的認知理論研究,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265、260頁。
⑤趙元任,外國語教學的方式,轉引自趙金銘《對外漢語教學法回視與再認識》,《世界漢語教學》2010年第2期,249頁。
陳灼:《橋梁》(下),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0年。
胡鴻、諸佩如:集合式詞匯教學探討,《世界漢語教學》1999年第4期。
呂文華:建立語素教學的構想,《第六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馬樹德:《現代漢語高級教程》(上),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年。
馬玉汴:《放射狀詞匯教學法與留學生中文心理詞典的建構》,《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版)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