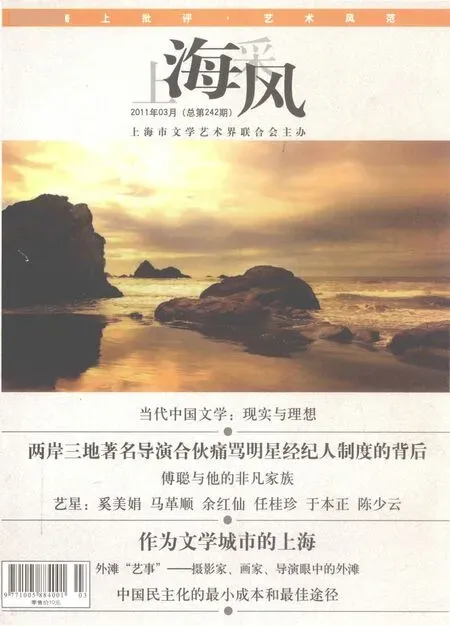一個文學流派的消逝
文/金 星
一個文學流派的消逝
文/金 星

“山藥蛋派”主將胡正
從報上得知,作為“山藥蛋派”的最后一位主將,作家胡正已于2011年1月17日在太原去世,享年87歲。“山藥蛋派”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形成于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領銜人物是趙樹理,緊隨其后的是人稱“西李馬胡孫”的西戎、李束為、馬烽、胡正和孫謙。他們都是山西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都有深厚的農村生活基礎和共同的藝術志趣及追求,一時佳作迭出,頗受廣大農民讀者的喜愛。胡正的代表性小說有《奇婚記》《汾水長流》《幾度元宵》等。但隨著他的離世,已在文壇上淡出許久的“山藥蛋派”恐怕是真的要畫上句號了。倘若由此及彼,消逝的又豈止是一個文學流派。
西風落葉之嘆,看似無奈,但更多的應是一種懷戀。“山藥蛋派”這一稱謂,確是有著明顯的地域特征,但集結在這一派下的作家都有著難能可貴的樸素而真誠的農民情結,這就超乎了一時一地,即使時至今日,也值得贊嘆與推崇。他們沒有發表過什么明確的創作宣言,但在寫農民看得懂的書(不識字的也能聽得懂)和出農民買得起的書上,卻是有著驚人的一致。趙樹理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文學只在極少數人中間轉來轉去,根本打不進農民中去。我父親是農村知識分子,但他對這種寶貝一點也不感興趣……我不想上文壇,只想把自己的作品擠進廟會上擺滿《封神榜》《施公案》《三俠五義》《笑林廣記》之類和兩三個銅板一本的小唱本的小攤里去,一步一步去奪取那些封建小說、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如此清醒而自覺,這就使他們堅持民族化、大眾化、通俗化的創作風格,深切關注農民命運和農村發展,在體驗生活時從不走馬觀花或蜻蜓點水,而是努力成為“生活的主人”。而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尤其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時,都以農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斷為基礎,從而使作品中的人物與思想始終來自所處生活的底層。當然,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山藥蛋派”的諸位作家在語言的運用上雖各具個性,但都有著流暢明快、幽默風趣的特點,“說書一般”,使廣大農村讀者如對兄弟、如對知心的好友,整個身心都被他們的作品吸引住了。孫謙在談到趙樹理的語言時曾說:“他沒有用過臟的、下流話和罵人話,但卻把那些剝削者、壓迫者和舊道德的維護者描繪得惟妙惟肖,刻畫得入骨三分。趙樹理的語言極易上口,人人皆懂,詼諧成趣,準確生動。這種語言是純金,是鉆石,閃閃發光,鏗鏘作響……”所以,像《小二黑結婚》《呂梁英雄傳》《三里灣》這類既深刻反映時代又影響深遠的作品,顯然都是創作者忠于生活而又對家鄉父老的最真誠奉獻。
自然,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任何的文學流派也總有窮途末路的時候。應該說,上世紀四十年代是“山藥蛋派”的輝煌時期,但解放后,一些作家的農民立場或民間意識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作品的影響力漸趨減小。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中,出自山西的一些青年作家在起初也大都以農村題材見長,如成一、韓石山、張石山等,一度被稱為“小山藥蛋派”。但也許是世易時移,他們的創作雖很見功力,可作品的影響或感召已明顯不如前輩作家,于是,悄然改變或貌合神離也就成為大勢所趨。久而久之,興趣的轉移,熱忱的消歇,加之越來越多原本出身農民的作家不斷地“洗腳上岸”,“山藥蛋派”文學風光不再乃至日趨沉寂也就不難想見。與此類似的,就有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新時期以來四川在農村題材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自從領軍人物周克芹英年早逝后,也是鮮有這一方面的大作。艾青有一句很有名的詩,那就是“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是因為我對這一片土地愛得深沉”,可像他那樣對腳下的土地俯首向心的詩人或作家已經不多見了。單就“要出讓農民買得起的書”這一點,如今的作家就已與當年的趙樹理諸人大為不同。出身農民并以農村題材起家的賈平凹曾多次寫到自己年少時喜愛看書,有時為了向人借書而不得不忍辱負重。但據報道,他于去年11月出版的總數21卷本的第三套文集,竟是創下了2980元的天價。正走在致富路上的農民兄弟估計是很難消受得起的。凡此種種,不斷地兩相背離,終究可哀的就想必不只是一個方面。
胡正人雖已去,但言猶在耳,他曾諄諄告誡道:“寫農村題材小說,自然要熟悉農村生活,熟悉農民,熟悉農村干部。同時還需了解農村政策,了解現行政策,過去的政策,并且還應當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些,想到以后的發展。因為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和干部,不能不受政策的影響,人物的命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與政策有關聯。寫農村題材小說也就必然要考慮農村政策問題。”如此金玉良言,倘銘記在心并勉力而行,或可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