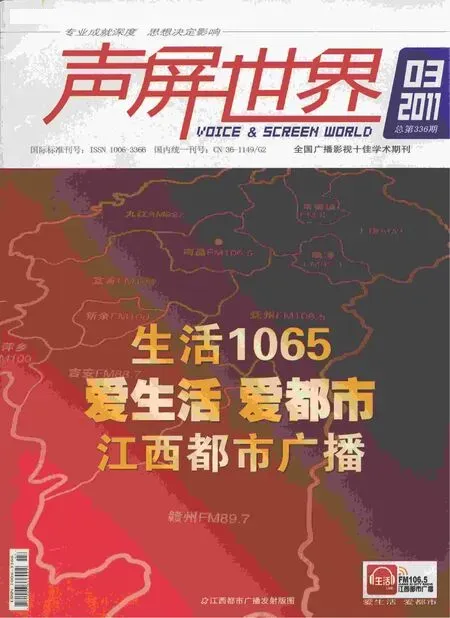轉型期媒體與環保NGO關系研究
□馮 敏
一直以來,我國實行的是政府主導型的環境保護政策,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深化,政府主導型環境保護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于是,我國政府在繼續改進并充分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開始尋找推進環境保護的新的力量之源,環保NGO(非政府組織)開始進入公眾視線。
媒體與環保NGO關系的生成:簡單宣傳報道為主
我國環保NGO起步晚,發育慢。1973年8月,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以后,新中國的環保事業揭開了序幕,環保NGO也在政府的引導下真正投入到對環境本身的宣傳和實踐活動上。1978年5月,最早由政府部門發起的第一家環保NGO——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成立。1994年,梁從誡在民政部正式注冊“自然之友”,這是中國第一家民間的環保NGO,其創始人梁從誡是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子。在此期間,我國由民間自發組成的環保NGO相繼成立。
可以說,媒體見證了環保NGO的誕生和興起。最早的是1993年6月《光明日報》記者梁若冰在“文化與生活”版面上頭條發表了《世界只有一個地球——記一次環境問題懇談會》,并配發了大幅照片。北京廣播電臺康雪也對此次“玲瓏園會議”進行了報道。1994年4月,作為環境保護類的專業媒體《中國環境報》對“自然之友”的成立進行了報道。梁若冰后來回憶到,“當時對民間組織沒有具體的概念,對這個組織在中國未來歷史上的重要意義也沒有預料”。那一時期媒體的新聞報道對環保NGO(特別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環保組織)也主要是宣傳,對草根環保NGO,包括環保NGO的具體運作細節缺乏一定的關注。這一方面和民間環保NGO的數量有限、影響力比較弱有關,社會包括媒體工作人員對民間環保NGO并沒有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對NGO的有關內容的報道恐怕還要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大背景聯系起來。中國最早提到NGO用的是“民間組織”而非“非政府組織”這一概念,可見,對“非政府組織”這一概念的理解在中國多少還存在一定的誤解。在中文里面“非”有“反”的意思,這些組織由于身份問題或未經過正式的程序登記注冊,它們的活動為政府所敏感和疑慮。為了規避風險,大部分媒體選擇回避或者少報道這類敏感的新聞,或者直接使其消失于新聞場域內部。而對NGO本身而言,其自身做事也非常低調謹慎,害怕因為太敏感而碰到“雷區”,“自然之友”的總干事就曾經感慨“94年參加民間組織的時候,民間組織做事都覺得自己必須夾著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樣”,①可見,在當時的背景下,環保NGO各方面都處于摸索階段,“夾著尾巴做人”的極低社會能見度也促使其將目光投注在如何完善組織等方面,而對擴大知名度、影響力等內容的重視和開發并沒有提上他們的工作日程。
環保NGO與媒體合作關系的發展:隨機、偶然的合作
“自然之友”成立后,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簡稱北京地球村)也在同年建立。此后,純民間性質的環保NGO開始在全國大量出現,組織數量和成員數量都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如1996年建立的“環境與發展研究所”,1997年建立的“媽媽環保志愿者協會”等等。在1995年之前,中國媒體對環保NGO,特別是自下而上的環保NGO報道較少,而1995年之后,媒體對環保NGO的報道頻率急劇增加,特別是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媒體頻頻報道NGO及其開展的活動,《人民日報》甚至在頭版頭條對環保NGO的活動進行了報道。一方面,環保NGO開始主動聯系媒體,借助媒體不斷擴大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媒體也開始越來越關注環保NGO,注重保持和加強與環保NGO的關系,他們展開了一系列的合作。
從媒體的角度分析,此時媒體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新聞的社會守望功能大大提升,而當時的環境問題已經表現出特殊的嚴重性,受到了公民的廣泛關注。對和公民息息相關的環境問題的關注和報道成為媒體進行社會監督、實現社會效益的重要途徑和載體,而此時的環境問題正在由“政府主導”慢慢向“社會制衡”轉變,環保NGO作為有組織的、具有公益性和獨立性的團體自然成為媒體的關注對象;另一方面,對包括環保NGO在內的不同群體的利益表達也可以幫助媒體達到一種報道上的“平衡”,從而保證媒體的公正性、報道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且他們較強的專業背景知識、更加全面客觀的信息資源也為媒體記者深入進行調查報道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方法。
而對環保NGO來說,主動出擊、積極聯系媒體也成為他們開展工作的主要方式。一項調查顯示,在與媒體和公眾的關系方面,借助媒體擴大影響力進而得到社會公眾的支持已成為我國環保NGO的共識。他們通過和體制內的、具有行政級別的媒體合作,使得組織的合法性得到體制內的認可,通過媒體使公眾意識到加強環境保護、提高環保意識的重要性。同時對一些比較嚴重的環境問題,可以利用媒體的“放大器”和“傳聲筒”功能,將話語表達積聚成輿論合力,提高問題的關注度以及進入決策層成為行政一部分的可能。
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與環保NGO互相倚重,通過開展記者沙龍、聯合采訪報道、環保NGO媒體工作培訓、共同策劃環保活動、聯手門戶網站搭建公益頻道等方式展開了一系列的合作。1996年的保護滇金絲猴議題、1997年“自然之友”保護藏羚羊議題、1998年保護四川大熊貓的議題等都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使我們看到了通過與媒體的聯手,社會力量和民意對政府決策產生能動影響的可能,依稀向我們描繪了一種通過媒介力量推動公民參與公民社會建構的途徑。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一階段所涉及的議題大多集中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該議題本身的不敏感性容易使其在媒體中得到呈現。
但是,在這一階段,媒體與環保NGO的合作不成熟,也不穩定,還缺乏一定的經驗,具有間歇性、偶然性的特征。類似于保護藏羚羊的公共事件依靠領導個人魅力的成分比較大,僅就單個問題試圖與政府合作,雖然通過媒體掀起了一陣報道浪潮,引發社會的關注,但是沒有形成一種持續性的力量。
媒體與環保NGO合作關系的深入:媒體新聞實踐的積極拓展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公民權利意識與參與意識的不斷增強、公民社會的不斷成長,媒體與環保NGO清楚地認識到,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化趨勢以及轉型期環保NGO與媒體的訴求都給彼此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在此前提下,環保NGO和媒體的合作也逐步深入,不再僅限于間歇、偶然的合作,而是進入一種常態的、更深層次的合作。這種合作,是對轉型期媒體訴求的一種回應,是新聞實踐的拓展延伸。也正是在媒體的積極干預和推動下,環保NGO通過將公平和諧的發展理念和環境正義融進自己的項目與活動,其公民立場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公民關注、認可,公民參與得到倡導。
環境問題關系著每一個人的生存和未來的福祉。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環境問題的產生是一部分獲利的人以損害其他人的生存為基礎的,這必然牽涉到政策的制定、社會的分工以及群體利益的分化等各個方面。公民需要知曉和環境有關的信息包括環境決策,因為這些信息和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對環境問題的重視,就必然引發媒體對包括環保NGO在內的相關的利益主體的重視。同時,通過對環保NGO和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的報道,逐步勾勒出一個不斷發展的公民社會的雛形和輪廓,而這種對公民社會、公共品質的關注和追求,實際上也是一個媒體獨立思想、獨立價值觀念的形成與表達過程,這是媒體成長的一個態勢。
從2003年開始,在反對怒江建壩、圓明園防滲工程事件、北京動物園搬遷、廈門PX項目、“5·12”汶川地震、廣州番禹垃圾焚燒、應對氣候變化、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青海玉樹地震等一系列環保實踐中,媒體與環保NGO展開了更深層次的合作。一方面,環保NGO開始把媒體作為他們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群體,利用媒體擴大自己的知名度,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所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媒體開始在眾多公共事件中潛移默化地起作用。在一些公共事件的背后,媒體不僅僅是支持者、同盟軍,還是直接的參與者。媒體針對環保NGO的議題取向也更加側重從本質上介入深層次的利益格局,同時更加注重公眾動員,以及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政策宣導等,不斷將環保理念、公民參與等政治態度傳遞給公民。
媒體與環保NGO從20世紀90年代的彼此疏忽到進行偶然、間歇的合作到如今的深入、積極的合作,這不斷探索的過程也是一同成長的過程。環保NGO通過媒體使相當一部分的議題成為公共議題,得到了社會、決策層的關注;媒體對這些公共事件的關注以及報道,本身就是追求公共品質,積極構建公共領域的一種體現。盡管環保NGO與媒體在合作中還存在著許多的問題,也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阻礙,但是隨著我國法制制度的不斷健全,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環保NGO的生存環境不斷改變、完善,發展速度不斷加快,新聞媒體的新聞改革不斷深化,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一個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健康和諧的局面出現。
注釋:①徐 楠:《環保NGO的中國生命史》,2009年 9月30日,http://www.infz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