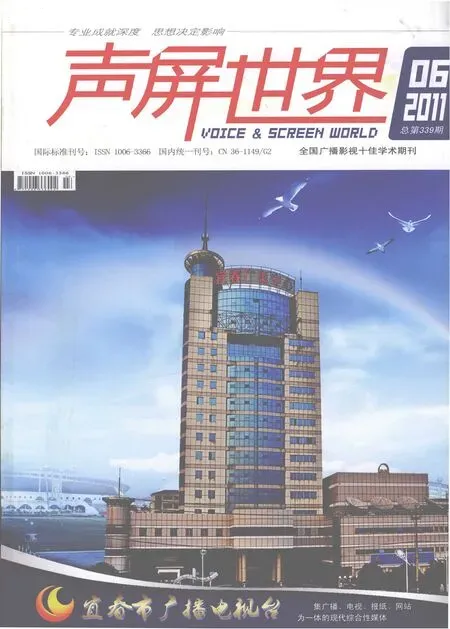春晚突破的思路
□楊 臻
從期待、歡樂、失望到如今的圍觀,春晚不減熱情,觀眾卻漸漸無情。在這一過程中,春晚也慢慢從一場茶座式的“聯歡晚會”變成了一臺程式嚴格、試圖皆大歡喜的盛典。如何留住觀眾,春晚需要轉變思路,邁開步伐,學會競爭,學會用電視的語言說話。
指導思想要轉變
春晚不必面面俱到。春晚就好比文藝界的《新聞聯播》,安全播出最重要,要不出錯,讓所有人都說不出什么,最好還要13億人民都喜歡。春晚的一位導演說,“春晚審查的標準就是全國人民都能接受,不能有爭議,要滿足各個年齡層、各種階層的需要。春晚奉行的是中庸之道,并不體現導演個人的愛好,無論是誰導演,結果都是一樣。性格特征太明確,就可能出麻煩。”①春晚越來越像一個燙手的山芋,讓承辦者喘不過氣來,身上肩負著那么多的使命,綁著那么多的顧忌,承辦者不敢變化,不敢創新,不敢有個性,不敢有特色,越中規中矩越安全。
一臺晚會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去迎合所有人的口味,最后只能是所有人都不滿意。作為國家級電視臺,央視擁有很多資源可供調度,這是它的優勢,但央視的春晚大可不必“大而全”,不必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不必承載那么多功能。導演在選擇節目時,誰的節目好用誰的,不夠精彩的大可不用,沒有必要一首歌曲非要讓陸軍、海軍、空軍各出一名代表來演唱,就像沒有必要把所有的戲曲形式都過一遍,或是讓五十六個民族都來表演一番一樣。
這里還是存在一個思路轉變的問題。春晚創作的事實邏輯是:其一是創作者猜測導演的意圖,導演猜測領導的反應,領導猜測可能會有的意見。②節目的創作者和導演有時給自己劃定一些條條框框,認為“我不這樣面面俱到,領導肯定會不滿意”,殊不知領導也是在看觀眾的反應,觀眾喜歡領導也高興,春晚年年遭到觀眾的詬病,領導也不見得就滿意,觀眾的高興與領導的高興本身并不沖突。其二是猜測觀眾的期望與滿意度,似乎春晚安排了一個少兒節目,小朋友們就一定會喜歡,就好比認為老年人一定會喜歡戲曲聯唱。其實有可能有的老年人會認為那短短幾分鐘的戲曲還沒仔細聽就結束了,與其蜻蜓點水,每樣都來一點,倒不如讓戲曲頻道專門辦一臺戲曲晚會給老年觀眾。再問問年輕觀眾,有多少人喜歡每年在春晚上都看到周杰倫、陳奕迅、容祖兒、賈玲和白凱南?這其實就是創作者和導演以自己所在年齡層和階層的心態,去猜測其他年齡層和階層觀眾的喜好。怎么解決?其實可以在春晚籌備時就與觀眾進行互動,請觀眾去投票選擇喜歡的節目樣式和表演者。
審查少一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春晚曾涌現了一批受歡迎的小品,如《吃面條》《警察與小偷》《主角與配角》《宇宙牌香煙》等等,2011年春晚小品類節目總統籌王寶社說,這種小品高峰期的存在與當時寬松的環境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審查只需央視文藝部主任和臺長過目。而隨著春晚越來越受重視,審查的次數和人數越來越多。王寶社說:“現在的審查過程是對演員心理承受力的極大考驗,對面是各級領導,坐成一排,輕易不笑,領導面前是一張紙和一支筆,會從思想、結構、包袱、演員合不合適這幾項來給意見。這些意見我們都得吸收一點,在修改后的節目中有所表現。”可是,觀眾面對這些捆綁了各種要求和意見、束手束腳的小品時,卻越來越笑不出來。
2011年第8期的《三聯生活周刊》在《別鬧了,春晚》的封面故事中談到:“央視春晚的重要性,使它變成了耗時半年、程序嚴明、層層審查的獨家制作,早已超越了導演們的把控能力。它的首要目的是爭取讓所有觀眾都樂,卻用最不娛樂的精神,將笑點一一閹割。觀眾能否樂得起來,原本是件最不能勉強的事。”眾口難調,在審查這一環節上,春晚能不能減少一點審查頻次、減少一點審查人數呢?
引入競爭
春晚一直以來都是央視獨家壟斷的,13億人看一臺晚會,觀眾會出現審美疲勞,央視也會不思進取,主辦者在遴選節目、挑選演員上也會越來越沒有新意,越來越官僚。市場經濟需要競爭,允許競爭的存在,才能為消費者換來更多更好的產品或服務。具體到春晚,如果要讓觀眾滿意,同樣需要競爭。“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提高質量的重要手段,今年已經有省級衛視臺放棄轉播央視春晚了,如東方衛視在除夕夜推出了“一個人的春晚”,讓周立波一個人給大家講清口,收視率沒有下滑,穩居全國第二。③打破央視壟斷,實現“開門辦晚會”,讓其他電視臺參與競爭,給觀眾更多的選擇權,也會促進央視春晚越辦越好。
除了鼓勵地方臺辦春晚之外,央視的春晚在節目選擇和演員任用上也需引入競爭機制。在必須要出的“指標性節目”中,同樣也可以“競爭上臺”。例如反應少數民族面貌的節目,不需要每年都讓五個自治區的少數民族來出,即使沒有精彩的節目也要挖空心思地創造,完全可以五十六個民族進行節目的競爭,誰的節目精彩就用誰的,一方面公平,另一方面也給人數少一點的民族以展示的機會,同時還可以給觀眾帶來新鮮感,了解一些平時不太關注的民族的風俗習慣。
在演員的選擇上,目前對于“熟人老臉”的批評已層出不窮。《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8期 《春晚的譜系》中有這樣一段話:“沿著時間線往前推,你會發現馮鞏已經26年登上春晚的舞臺,黃宏、宋祖英22次出現。忽然發現我們近10億的觀眾很寬容,把一個一年一次代表國家最高水準的盛大舞臺,讓給這些演藝明星慢慢變老。他們的表演曾經主導我們父母輩的記憶,今天已經很難吸引年輕人成為話題,但或許接下來的幾十年,還將主導孫子輩對娛樂藝術的認知。”長期缺乏新人的競爭,春晚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老化和失去活力。一個演員和創作團隊今年的節目好,并不代表明年的還受歡迎,何必要把著那么幾個人,直至其創作才華被完全榨干,引得觀眾一片罵聲才罷休呢?就像今年春晚上趙本山對自己的調侃一般,沒有本山大叔,地球就真的不轉了嗎?
學會運用電視語言
舞臺小一點,觀眾少一點。春晚演出的舞臺是中央電視臺1800平方米的一號廳,如此的演出空間讓演員和觀眾很難建立互動。為了讓觀眾看清聽清,馮鞏說單憑口說已經無法控制場面,必須要加入劇烈肢體運動的小品動作;趙本山說他的表演基本上要“吼”……這樣的演出基本上還是以舞臺為主導,而非以電視為主導。經過電視的傳播,電視機前的觀眾們看到的不管是主持人還是演員都一個個像打了雞血般地聲嘶力竭。既然春晚是想讓全國電視觀眾收看,那么就必須懂得電視的傳播特點,而不能按劇場思路來運作。春晚可以在一個小一點的演播廳、小一點的舞臺上舉行,觀眾少一點,距離近一點,要有交流聯歡的氣氛,互動起來也方便,主持人和演員說起話來也更切合自然狀態,電視觀眾聽起來也更舒服。
利用時空延展性,設立分會場。春晚的節目形式多樣,但并不是所有節目都適合在那么大的舞臺上表演,小品就適合在小空間中呈現。二十多年來一直為馮鞏創作的曲藝家崔硯君說:“八九十年代的小品相聲,演員的表演很流暢。但是在近2000平方米的一號廳里,大型歌舞的燈光、音像都是大場面的,伴舞都是上百人,等大歌舞一演完,再上去一兩個演員的語言類節目,根本壓不住場。”電視是具有多時空的傳播優勢,包括空間的拓展和時間的延伸,作為電視春晚來說,可以設立分舞臺或分會場,將大場面的歌舞和需要小空間的語言類節目分開,通過電視畫面的切換連接整場節目,對于電視觀眾來說,并沒有打破其收視的連貫性。其他節目也可以通過外景和小片的方式來加大信息量、增強美感和真實性。
動靜結合,打造視覺沖擊力。空政文工團團長楊月林說,春晚的大場面淘汰了很多“比較安靜”的節目形式,比如曾給觀眾留下很深印象的啞劇《吃雞》,而楊麗萍的獨舞則“太意念、太唯美、不熱鬧”。電視講求畫面的視覺沖擊力,但并不是說只有“排場很大”的節目才有沖擊力,安靜唯美的節目同樣也是視覺沖擊力的一種表現。《雀之靈》《千手觀音》《傳奇》等節目都比較安靜,但由舞美與演員營造出來的視覺美感絲毫不遜于任何一個團體操式的大型歌舞,也都獲得了觀眾的好評。
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既贏得了贊譽,也承受了來自方方面面的質疑和不滿。在不能給觀眾帶來絲毫懸念和期待的情況下,春晚要想讓觀眾真正樂起來,只有轉變模式化的思維方式,進行有益的嘗試和創新,才能不斷前進。
欄目責編:曾 鳴
注釋:①吳 淇,丘 濂:《春晚的譜系》,《三聯生活周刊》,2011(8)。
②李鴻谷:《譜系權力榜 別鬧了,春晚》,《三聯生活周刊》,2011(8)。
③《如果不再壟斷》,《三聯生活周刊》,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