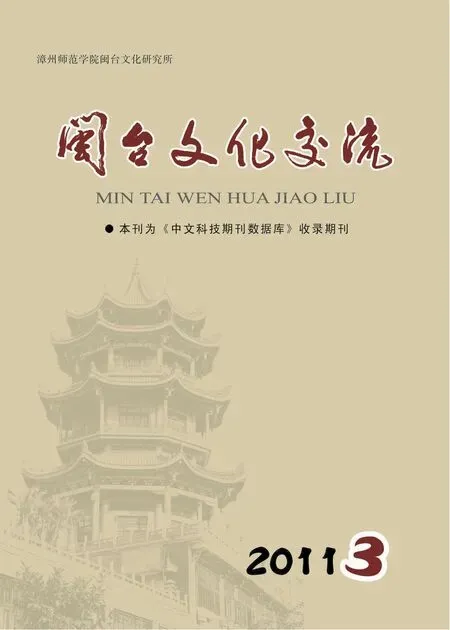政和縣楊源鄉四平戲的歷史淵源與生存現狀
鄒自振
政和縣楊源鄉四平戲的歷史淵源與生存現狀
鄒自振
中國戲曲史告訴我們,早在明清傳奇成為劇壇霸主之前,宋元南戲已崛起于民間。據史載,南戲在浙江溫州形成后,就以它濃郁的鄉土氣息,貼近生活的現實精神,以及比元雜劇更靈活、自由的演出體制,贏得廣大觀眾的喜愛,在很短時間內,就流傳到浙、閩、贛、皖、蘇等地。在傳播過程中,原來以溫州地方的語言、曲調、鄉音演唱的南戲,和當地的語言、音樂唱調相結合,形成了各種不同風格的地方聲腔,至少在南宋末年就產生了海鹽、余姚、弋陽三大聲腔。至元末,又產生了杭州腔與后來居上的昆山腔。
明人傳奇不僅指昆腔,由海鹽、余姚、弋陽三大腔在民間演變而成的宜黃腔、樂平腔、徽州腔、青陽腔、四平腔等的劇作,也都屬傳奇之列。其實,就古老的南戲而言,它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一直到現在,福建的屏南縣還有一種四平戲的古老劇種,在音樂唱腔和演出形式上,仍保留了不少溫州南戲的原始面貌。
從上所述,四平腔曾于明代中晚期在江蘇、安徽一帶盛行,之后,它便漸漸消失。清中葉以降,四平腔被戲劇研究家們以為早已滅絕了。1982年,傳來一個震憾人心的消息,在閩東北的大山一帶,發現四平戲還存在著。其中尤其以屏南縣龍潭村四平戲保護得最好,唱腔至今還保留著官話的形式,其主樂器為大鼓、鑼、鈸,沒有管弦樂器,唱時有后臺幫腔,唱腔特點仍為李漁所說的“字多音少,一泄而盡”。這就為我們探討四平腔在閩北山區的遺存帶來了喜悅與慰籍,增強了進一步研究這個被稱為“中國戲曲活化石”的古老聲腔與劇種的信心與決心。
除屏南外,位于閩、浙邊界崇山峻嶺之間的福建省政和縣楊源鄉(與屏南北部交界),至今亦有明末清初由江西傳入(一說傳自屏南龍潭)的四平戲的演出,其語言唱腔是弋陽腔的遺存,屬于高腔系統。伴奏亦僅有鼓、鈸、鑼、板鼓等四種打擊樂器,古樸粗獷,清新悅耳,句末用幫腔拖音演唱,道白皆用一種介于普通話與當地方言之間的“土官話”。楊源四平戲并有“正字戲”的稱謂,意思是所用語言為官話而非鄉談。《蟠桃會》、《轅門斬子》、《蘇秦》等三個道光至緒年間四平戲的古老劇本和數件珍藏三百多年的古戲裝在楊源鄉還保留至今。這種弋陽腔系統的古老劇種是一種“活文物”,具有相當高的研究價值。
一、楊源四平戲的歷史脈絡
楊源地處偏僻,村莊貧窮,文娛缺乏。四平戲一旦傳入,村民即如獲至寶,代代相傳,并以之作為謀生的重要手段。最早的四平戲于明末清初由江西傳入,在楊源一帶有“詠霓軒”四平戲班活動,與當地“英節廟”一年兩度的廟會密切相聯。
葉明生先生指出,政和縣楊源村的四平戲,是流傳于福建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劇種中的一個,它的存在與社區廟會及宗族社會活動有密切關系。首先是楊源村張姓族人,為紀念唐末與黃巢戰斗而殉節的祖神張謹,而于每年春、秋英節廟祭祀的演戲酬神之需要,使四平戲與廟會結下不解之緣;其次是張姓宗族為了使廟會的戲劇演出制度化,于宗族內部組織四平戲演出會社——梨園會,以確保廟會的延續;再次,由于四平戲在廟會的存在被宗族化,同時也產生了藝人在宗族中特殊的權利與義務;此外,四平戲的劇目及演出固然是以戲劇娛樂為主體,但它必須從內容到形式都融于廟會活動及其儀式之中,成為宗族活動及廟會儀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1]
康熙、雍正年間(1662—1735),楊源四平戲演出活動一度興旺。英節廟建于康熙元年(1622),內有戲臺一座,村民每年要為祖公張謹夫婦生日(一為二月初九,一為八月初五)演戲三天,風俗至今,由此推測四平戲至遲于康熙年間已在楊源扎根。戲班是半職業性或業余的,腳色行當在雍正時期較齊全,分生、旦、凈、末、丑、占(貼)、外、夫(老旦)、禮等九門。雍正中期,戲班經常被請到鄰縣周寧、壽寧等地演出,每到一地演出均達半個月以上。早期演出的劇目有《白兔記》、《劉文錫沉香破洞》、《八卦圖》、《青銅棍》、《蘇秦》、《蘆林會》等。雍正末年,當地酷愛四平戲的老藝人張子英變賣家產,重新購置戲裝道具,組建四平戲班,使四平戲在楊源得以延續。
道光年間(1821—1850)開始,楊源村的四平戲受到亂彈、皮黃聲腔的影響,吸收了部分京劇劇目,如《大補缸》、《小補缸》、《玉美人》、《楊戩打金刀》、《擋馬》、《游龍戲鳳》等。據道光手抄本《游龍戲鳳》中,鳳姐唱的“梅龍店內排酒筵,安排酒筵待客人”曲詞下注有“唱下江調亂彈”。在《擋馬》一出中,焦光普唱段注有“唱皮簧倒板”。咸豐年間(1851—1861),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四平戲失去社會依托,再次中落。清末同(治)、光(緒)年間,楊源村的四平戲班在壽寧縣平溪村演出時,不慎因戲神香火引起一場大火災,燒毀戲班行頭、道具,僅存一個小板鼓(今尚存),從此四平戲的演出活動從興盛走向沉寂。
光緒年間(1875—1908),楊源武庠生張香國再次組建規模較大的四平戲班,自任總管授戲傳科,四平戲再現振興勢頭,不僅活動區域恢復到雍正初期之范圍,而且在劇目、表演藝術上均有所開拓。除繼承明末四平戲那些以曲牌聯綴體為主的傳統劇目外,還移植兄弟劇種的一些板腔體劇目,從當地民間藝術中吸收營養,出現了一些用江南小調演唱的《嘆五更》、《玉美人》等劇目。腳色行當亦趨完善,生行漸分為正生、小生,共有十二個行當。表演上生角強調文雅,旦角要求細膩,凈角注重粗獷,丑角講究滑稽,形成政和四平戲獨特的表演風格。鄉人為了紀念張香國,在戲神的香火神位上,除主祀田公師傅外,還附祀“張香國神位”。光緒七年(1881),有江西贛州四平戲藝人到政和,將楊源鄉禾洋村李延文、李德文等人在嘉慶初年由江西傳入的四平木偶戲加以改造,建立禾洋村人四平戲班,編演《寶帶記》、《雙義記》等劇目,在禾洋、翠溪、洞宮一帶演出。數年后,又建立嶺頭村四平戲班,使政和縣四平戲由楊源村一個戲班發展為三個戲班,四平戲達到繁榮興盛的局面。
民國時期,楊源、禾洋一帶革命老區常遭國民黨反動派燒殺搶掠,四平戲藝人流落他鄉,四平戲漸趨衰落。建國初期,全縣僅有楊源、禾洋二個規模不大的四平戲業余劇團,1954年楊源村四平戲業余劇團曾整理演出了《沉香破洞》、《白兔記》等傳統劇目。“文革”期間,演出活動停止,劇本幾乎散失殆盡。
二、楊源四平戲的現狀及保護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四平戲演出活動恢復。1981年在老藝人張陳招(現任劇團團長張孝友之父)、張應選、李式舒等的主持下,重新整頓組織楊源、禾洋二個四平戲業余劇團,吸收一批青年演員,其中女演員四名,打破了四平戲一貫男扮女角的局面和傳男不傳女的舊傳統。八十年代,四平戲藝人收集整理出了清代四平戲手抄本《秦(陳)世美》、《二度梅》、《蘇秦》、《英雄會》、《九龍閣》、《蟠桃會》等傳統劇本,可演出的四平戲劇目有24個。目前楊源、禾洋二個業余劇團能演出的整本戲尚有《九龍圖》、《白兔記》、《英雄會》、《劉文錫沉香破洞》(《寶帶記》)、《蔡伯喈》(《琵琶記》)、《王十朋》(《荊釵記》)、《蘇秦》(《金印記》)等,折子戲則有《蟠桃會》、《轅門斬子》、《蘆林會》、《紅太襖》、《別嫂》、《拜月記》、《奏主》等三十多種。
也許楊源村的農民并不知曉四平戲傳到楊源村的確切年代(他們大多認為是張香國的祖先傳開的),但正是一個演員全部由農民組成的劇團,一個在大山深處默默生存的聲腔劇種,卻曾經有過昔日的輝煌,并在今日成為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從政和四平戲的現狀看,其戲班現有演員都是當地的農民。熱心四平戲的農民進入戲班跟班學習后,漸漸進入角色。他們農忙時種地,農閑時練戲,廟會時唱戲。1999年楊源村四平戲戲班在全縣慶祝建國50周年文藝晚會上表演了《蟠桃會》,榮獲優秀演出獎。
作為地方劇種的四平戲與其它戲曲相比較,藝術上尚處于較原始狀態。其表演動作有騰、挪、滾、打,隨鼓緩急、進退,不同的行當手、腳動作都有規定的口訣。其語言唱腔是“弋陽腔”遺存,屬于高腔系統,古樸粗獷,清新悅耳,優雅動聽。
四平戲唱腔語言從江西傳入政和,到現在已四百多年,仍原汁原味不變。后臺伴奏僅有鼓、鈸、鑼、板鼓四種打擊樂器,以鼓為主場指揮,每當臺上唱完一段唱詞,后臺就會跟著尾音唱起來,顯得韻味極長,富有生趣。主要角色有生(分正生、小生)、旦(分正旦、小旦)、凈(分大花、二花)、末、丑、貼、外、夫、禮等十二種行當(也即所謂“江湖十二腳色”)。劇本沒有標注唱腔音符,只有標注輕、重音符號,無譜有調,語言和唱腔完全靠口頭代代相傳。
葉明生先生認為,政和楊源之四平戲是以宗族形式與戲劇會社組織相結合的會社形式(梨園會)保存至今,雖然其作為一個古老劇種,在聲腔、劇目、表演藝術等方面都給今人研究古代四平腔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是,作為以廟會為依托、以宗族社會組織而存在、歷經滄桑保存至今之四平戲與梨園會,其在民間儀式與戲劇生存發展之關系方面很有代表性,對今人探討戲劇人類學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實證資料。[2]
據楊源鄉鄉長吳世清介紹,在官方(政府)尚未注意到四平戲時,正是有了英節廟與“迎翁會”、“梨園會”等祭祀、廟會的信仰、戲俗和民俗,四平戲才得以保存下來。74歲的鄉民張明甲是四平戲目前最老的藝人,他16歲便開始學唱戲,據他說,當時“學戲的人一批又一批,都是年輕人”,所以當地有諺語“楊源孩子三出戲”,就證明了四平戲在當地的影響。著名鄉土藝人張陳招,花了很大力氣組建新的四平戲戲班子,因缺少旦角,就讓自己的兒子張孝友去學。現在張孝友已經五十多歲了,還一直在唱旦角,他也是劇團現任團長。我們可以在楊源村看到這樣一出熱烈隆重的民間演出面貌:24桿土銃一起鳴放,上千人的踩街隊伍,穿著奇特的戲服,畫著古怪的臉譜,扛著祖宗的神位,敲鑼打鼓一路浩浩蕩蕩,直奔唱戲的場所當地的英節廟古戲臺,在流傳了幾百年的民俗活動“迎翁會”上,村民們要進行祭祖演出,連續上演三天三夜——四平戲是唱給祖宗們聽的!
政和縣為搶救、保護四平戲,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是保護作為戲曲載體的古戲臺。四平戲劇場——楊源英節廟,始建于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元、明時期均有修建,現存建筑中,大殿為康熙元年(1662)所建,戲臺為道光三十年(1850)重建。四平戲的戲臺建在英節廟內,完整保留著清代重建時的模樣,臺柱上兩幅楹聯寫到:“三五人可做千軍萬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聊把今人做古人,常將舊事重新演”。英節廟古戲臺為閩北古代戲劇活動場所代表作之一,戲臺照壁上保存著珍貴的戲神壁畫,被載入《中國戲曲志》。英節廟系紀念歷史人物張謹所建,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唐乾符年間(874—879),唐王朝以張謹為福建招討使,率官兵數萬與黃巢起義軍激戰于今鐵山鎮屯尾、石屯鎮長城村等處,官兵大敗,張謹身亡,葬于鐵山。后在張謹身亡地夏山(鐵山鎮元山村夏山自然村)修建張謹廟,北宋崇寧年間追謚昭烈,賜張謹廟為“英節大觀”,并增建縣城、楊源等三處英節廟。張謹后裔在楊源定居繁衍,楊源多數人姓張,因此楊源英節廟廟會祭祖味道十分濃厚。由于楊源英節廟歷史悠久,建筑風格獨特,1992年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二是支持開展廟會活動。與家族廟會結合,是政和四平戲生存的重要基礎。楊源英節廟與四平戲是相互依存關系,一方面廟會由楊源張氏宗族舉辦,為四平戲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四平戲為廟會助興做熱鬧,也是廟會的主要內容之一。每年農歷二月初九、八月初五,分別為張謹夫婦慶誕時,楊源村均要舉辦廟會活動(此風俗世代沿襲不斷)。楊源村四平戲班在英節廟內戲臺連演三天,以敬祖娛人;禾洋村四平戲則在每年農歷七月二十五連演三天。近年來,楊源鄉把楊源村每年的廟會活動定為洞宮山旅游文化節,把禾洋村每年的農歷七月二十五廟會活動定為民俗文化節,進一步重視并發揮了四平戲的作用。
三是合力扶助發展四平戲。四平戲的生存發展除了有廟會的支持、戲班演出的收入外,縣、鄉、村每年都撥出一定的經費支持四平戲劇團開展業務活動。縣文化部門也先后贈送了一批戲裝和道具,南平市、政和縣文化部門每年都有派專人前往觀看指導四平戲演出。
近年來,雖然政和四平戲仍然堅持在鄉間演出,但其生存發展的形勢卻仍不容樂觀,存在著許多困難與問題:(一)是現有四平戲藝人年紀偏大,最高年齡達七十多歲,最小的也有四十多歲,四平戲面臨后繼無人的危機。楊源鄉四平戲劇團團長張孝友說:“沒有新人來學,二十幾年了都是這么些人,好像自娛自樂。”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缺乏經費保障,學習、演出四平戲的人大多無償做奉獻,補貼酬勞很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與凝聚力。楊源鄉四平戲劇團二十幾個人全是農民,農忙時一樣到田里干活,只有在農閑時才抽空來排練戲文。(二)是開展四平戲活動經費嚴重短缺,縣、鄉兩級財政十分困難,無力投入經費扶持四平戲發展。因為資金困難,行頭很是寒磣。筆者在楊源村看戲時突然發現,有的演員穿的是草鞋,有的演員只是上身披著戲服,連褲子都沒換。(三)是四平戲演出設施破舊,古戲臺需要維修,服裝道具急需更新。(四)是由于四平戲是用官話演唱的,語言難以普及,很多年輕人聽不懂,其生存發展有一定的局限性。筆者注意到,在楊源村觀看《蟠桃會》的結尾時,臺上關公、周倉、八仙、金童玉女等各色人物紛紛登場,坐在臺下的幾位老太太很是陶醉地跟著哼唱,而旁邊幾個聽不懂戲文的小孩,則一直追問著劇情。
政和四平戲是全國少有的處于原始狀態的古老劇種,也是寶貴的民間的文化遺產。由于該劇種為家族歷代口傳心授,所以三百歲年來,始終保持著古樸的原始面貌。從目前現狀看,政和四平戲已處于絕代邊緣,岌岌可危。抓緊搶救四平戲,全面收集、整理四平戲文字資料與圖片,修建英節廟古戲臺,進一步完善其軟、硬件資料,把劇本、唱腔完整地保存下來,建立健全四平戲檔案,無疑是搶救保護四平戲的當務之急。幸運的是,2005年底,政和四平戲與屏南四平戲一道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個被稱為“中國戲劇活化石”的古老戲種,歷經數百年,在漸漸消逝的今天,又將慢慢地蘇醒……
注釋:
[1]《政和縣楊源村英節廟會與梨園會之四平戲》,原載《民俗曲藝》,2000年1月,第122、123合期,葉明生主編《福建民間儀式與戲劇》專輯。
[2]《政和縣楊源村英節廟會與梨園會之四平戲》,原載《民俗曲藝》,2000年1月,第122、123合期,葉明生主編《福建民間儀式與戲劇》專輯。
責編:鐘建華
作者單位:(閩江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