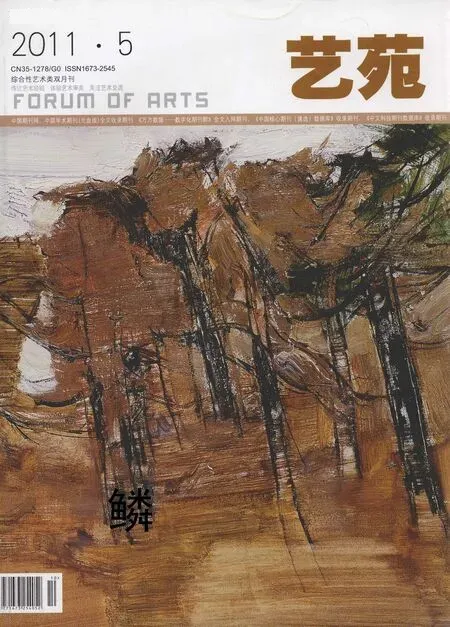浮華中,名士的本土道德
文/林顯源
經典作品的重排上演,通常最棘手的問題,總在于該如何適當地趨近原著的再呈現,及進行是否得宜的再創作尺度拿捏,二者間的權衡選擇比重問題,總是困擾著劇場工作者,尤其是導演者;更如歌德這樣的大文豪所創作之《浮士德》,一般早被公認為是德語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卻亦是極為艱澀難解的一部劇作,身為導演者,若有重排此劇的意圖,那亦可言是從創作動機伊始,就注定將會不斷地進行著一連串的挑戰。導演者就如同劇中的主人公,浮士德作為一個擁有了中世紀概念里無所不知的科學家,卻仍存在著不滿足與不安的心境,為追求世界的本質認知而陷入了深沉的苦惱,于此方與魔鬼訂立盟約以尋求解脫;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浮士德》導演徐曉鐘先生就是浮士德,其作為中國戲劇導演及教育大家,在耆老之年仍排出了此堪稱為壓卷之作的演出,若說是與魔鬼訂約,那此魔鬼究竟是何人?是誰誘惑及帶領著徐先生遍歷了中國劇場的“小世界”與“大世界”,讓來自德國的《浮士德》在中國卻出現濃厚的“本土味”?這魔鬼不是別人,正是這群廣大的當代劇場觀眾。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所演出的《浮士德》確實是“本土化”的。單純從演出文本的語言談起,公認為深奧難懂、連當代德國人都未必能讀透的巨作《浮士德》,在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肯定經過了仔細的推敲與琢磨;但一如中國的唐詩宋詞,不論經過多么精密的轉譯,成外文后,即使能表達原文的“意”,也很難完整表述其所要傳達的“境”。徐先生的《浮士德》不以德語演出,就如同普契尼用意大利語演出中國的故事《圖蘭朵》, 其所呈現的是意大利“本土化”后的中國元朝風情,那么徐先生的《浮士德》不也正是中國“本土化”后的中世紀德國情調?這樣的“本土化”并不是錯事,當然這是為了服務觀眾而必須為之,然而徐先生的導演術之高妙卻不等同于一般的“本土化”,其不僅能將翻譯劇本中已做到之“意譯”表述給完整保留了,還把語言文字翻譯很難傳達的“境”,用各種劇場藝術手段給補足了,具體體現在如全劇無所不在之波濤洶涌的海潮意象的大處、細微至各個書房架上的地球儀、骷髏頭等小處皆不勝枚舉,這可不是能一般等閑視之的“本土化”轉譯。
歌德的科學方法和浪漫主義的自然哲學不同,他的方法非是抽象推論,而是經驗主義的,但卻又跟實證論的經驗主義不同,它并不把人當成外在的觀察者,而是把人當成觀察對象內部,從屬于觀察對象的對象來對待;這是歌德的《浮士德》,所以我們正好用他的科學方法,來觀察徐曉鐘先生的《浮士德》,具體可從一個明顯的特點來看,就是舞美運用了圓形旋轉舞臺。在這個圓形轉臺上,陳設了一個半圓的立體裝置,這個裝置有階梯、平臺、斜坡等等,隨著場景的需要,可以時而為橋梁、洞穴等等,這些詩意濃郁的象征手法運用,原是眾所熟悉之徐先生的高妙導演術,然放于《浮士德》此劇中,卻正可令人窺探其創作背后所隱含的思維底蘊,即是體現了我國民族獨有的心理模式和習慣觀點,明確地說,縱使徐先生在演出作品中外顯出來的各種技法有諸多借鑒歐美的痕跡,但最底層內在的還是“中國式思維”,這是作為一直被認為是自外國學來的話劇“本土化”的最佳極致表現,最明顯地即可從《浮士德》這個圓的旋轉舞臺來探知。
《浮士德》中,不斷地提出各種二元對立辯證,那么在西方的傳統觀念中則常將方形視為對立的概念,如此,方形不是更方便地來表現《浮士德》中所存在的種種二元對立?然而徐先生卻用圓形,一種古中國人向來認為是沒有門或任何出口之封閉概念的圓形來構成舞臺的主表演區,這不正更能突出浮士德其所處之精神狀態與尋求突圍的急切? 再如劇中諸多角色的表演區位及走位動線,徐先生在走位安排上用的“直接強調”少、“間接強調”多,注重區位的“平衡”,具象可見的多運用象征與寫意(如天幕背景的投影),原本難以直觀得見的卻反用寫實(如酒吧里魔鬼所變化的魔法),這些無不是彰顯了我民族性格中之“圓融”與“和諧”特點,對應到中國觀眾自古以來對于戲曲程序符號等之觀賞習慣,在精神上,仍是一脈相承的。中國有著自己的根植于自身文化和傳統而建立起來的本土道德約束體系,徐先生《浮士德》的中國“本土化”,不止是在外顯可見的部分,其所蘊藏的中國人文底蘊及傳統道德價值判斷,是十分堅固的,這也是中國話劇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一個彌足珍貴的求索經驗總結。
羅素曾指出:“不同文化的接觸曾是人類進步的路標。”中國話劇的發展歷程最初雖是外來,但經過了中國“本土化”的過程,已逐漸走出一條適合我民族個性的道路。《浮士德》原本也是舶來品,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與徐曉鐘先生以向來中國觀眾早已習慣的象征、寫意、假定性這些手段,使得這出《浮士德》不僅僅只是“不同文化的接觸”而已,徐先生的《浮士德》雖然只排演了歌德的上半部,劇末并未見到浮士德如何使得魔鬼無計可施,但我們這些身為魔鬼的觀眾們,又再一次得不到浮士德的寶貴的靈魂,在他的帶領下,我們不僅認清了中國劇場的本質,也著實地能完全明白《浮士德》這般“本土化”的過程,確實是中國話劇進步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