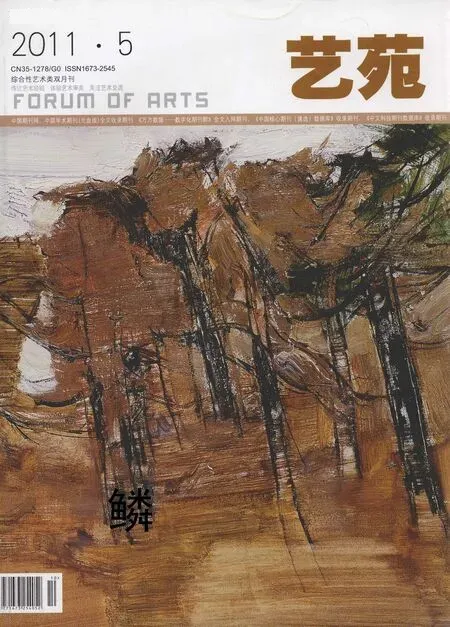詩意的舞臺、詩化的臺詞、詩感的節(jié)奏
文/洪春柳
歌德《浮士德》詩劇創(chuàng)作于19世紀初的德國,全劇分二部,長達1萬2千多行詩句,現(xiàn)以文本流傳于世。徐曉鐘版《浮士德》話劇公演于21世紀初的中國,取材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全劇演出時間2個半小時。兩位東、西方大藝術家隔著200年的時空,借著《浮士德》作了一場藝術心靈的嚴肅對話。
徐曉鐘版的《浮士德》話劇,完整保留歌德《浮士德》原著的哲學思考。不過,他的終場并非止于西方式的“天主最后審判”,而是以第二部第一幕“風光幽美的佳境”為尾聲。浮士德在美景中大夢蘇醒,感悟人生如夢,并繼續(xù)前行。這一個安排,倒是了讓全劇終場多添了幾分中國味的“黃粱一夢”。
歌德《浮士德》原著為詩劇,徐曉鐘版的《浮士德》話劇,以詩意的舞臺、詩化的臺詞、詩感的節(jié)奏來呈現(xiàn)全劇的美學追求。
詩意的舞臺,全劇以鋼架橋的旋轉舞臺為主,一方面藉舞臺的角度轉換來寫意地表達空間的改變,一方面搭配上簡單的實景,來落實空間的意義。如在舞臺上放置書桌、酒桶、魔鏡、花臺、床、井等物,虛實相間,結合寫意與寫實來呈現(xiàn)書齋、酒肆、魔界、庭園、閨房、井邊等不同的舞臺空間。
冰冷、凝重的鋼架橋,隱喻既定且無情的命運,旋轉的舞臺寓意輪回的人生,再加上時明時暗、時藍時紫的燈光,偶而的煙霧效果,如幻似夢。在命運的轉回里,幽微的人性時時受到魔鬼的試探,醒來如夢。
詩化的臺詞,詩,因為有韻,最不容易傳神翻譯。詩劇的翻譯,要求的標準不僅是信、達,還要雅。徐版的《浮士德》臺詞,將歌德原著融會貫通后,再換成全然中國味的詩歌來呈現(xiàn),透過一流演員作二度創(chuàng)作式的朗讀,兼顧生活化和詩韻化,不但觀眾聽得懂、聽得順暢,還聽得悅耳。
以酒店的“跳蚤歌”為例,“從前有一個國王,養(yǎng)了一只大跳蚤,國王對跳蚤愛得不尋常,就像愛他的兒子一樣”,歌謠通俗有味。再以“甘蕾青的居室”獨白為例,“我的心兒不寧,我的心兒沉沉,我再也靜不下心,我再也不能”,不論語句、韻腳,都已化身為中國味十足的心聲。
詩感的節(jié)奏,講求抑揚頓挫,一詠三嘆,更往往藉用復沓來強化意象或情感,以達成全詩的統(tǒng)一感。徐版的《浮士德》話劇,有群歌群舞與個人獨白的對比,有快樂戀愛與痛苦生離的對比,有民間節(jié)慶與魔界亂舞的對比等等,并借著這些對比來表達全劇節(jié)奏的抑揚頓挫。“牢獄”一場中,浮士德、魔鬼、甘蕾青定格1分40秒的演出,屏息寂然,更是無聲勝有聲。
此外,在場與場之間,以一貫的全黑燈光為間隔,以不時進出的鐘聲、海濤聲為終始,更形成全劇復沓的詩感。來自大地的海濤聲,聲聲如叩問。如“夜”一場中,浮士德拿著骷髏發(fā)問,如“城墻夾巷”一場,甘蕾青對著圣母懇求,背后都是傳來陣陣的海濤聲。來自天上的鐘聲,聲聲如警醒。同樣如“夜”一場中,復活節(jié)前夕,《光榮頌》的圣樂,鐘聲特別地響亮,如“牢獄”場景一進入,背景是大海浪濤,夾雜著鐘聲響起。復沓多次的暗燈、鐘聲、海濤聲貫穿全劇,是隱喻,是象征,是寓意,并達成全劇詩感節(jié)奏的統(tǒng)一。
以美學的追求,表達哲學的思考。徐曉鐘版的《浮士德》話劇,它的藝術魅力就建立在詩般簡潔、詩般精練、詩般雋永的典雅風格上。
面對前輩的經(jīng)典作品,后人常以借用或改編來處理之。比較歌德《浮士德》原著與徐曉鐘版《浮士德》話劇后,卻發(fā)現(xiàn)徐版《浮士德》似乎超越了借用或改編,而挑戰(zhàn)了重現(xiàn)經(jīng)典、移植經(jīng)典。
重現(xiàn)經(jīng)典,除了掌握哲理思考的主題外,徐版《浮士德》話劇還將重現(xiàn)的意義體現(xiàn)在情節(jié)、服飾上。經(jīng)典情節(jié),如黑狗變魔鬼、浮士德用血和魔鬼簽約、酒店的狂歡、浮士德和格蕾青對話宗教、群魔之舞、牢獄的拯救等等,徐版《浮士德》話劇仍注重原著細節(jié),不輕易更改。服飾上,中世紀歐式、古典的裝扮,穿梭全場,一再提醒觀眾,這是一出歌德的《浮士德》。
但移植經(jīng)典,又必須有所改良,才不致于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改良就是語言,如果觀眾聽不懂演員在講什么,戲就看不下去,移植的意義也就消失了。能否作出一部中國觀眾能夠看懂、能夠接受的《浮士德》,這是徐版《浮士德》話劇最大的挑戰(zhàn)吧!因此消化原著,融會貫通,語如己出,也成為移植《浮士德》最重要的改良。
200年前的西方經(jīng)典,對現(xiàn)代東方人來說,必有相當大的隔閡。中國的戲劇大師、戲劇教育家徐曉鐘領導其藝術團隊,以刪而不改的原則,完成了一部中國觀眾能夠看懂、能夠接受的《浮士德》話劇。隨著在上海、北京的公演,掌聲響起,戲劇界對此部作品已全面肯定。至于徐版《浮士德》話劇是否能引動大眾普遍性的回響,要問的是:浮士德是不是還存在于每個人的內(nèi)心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