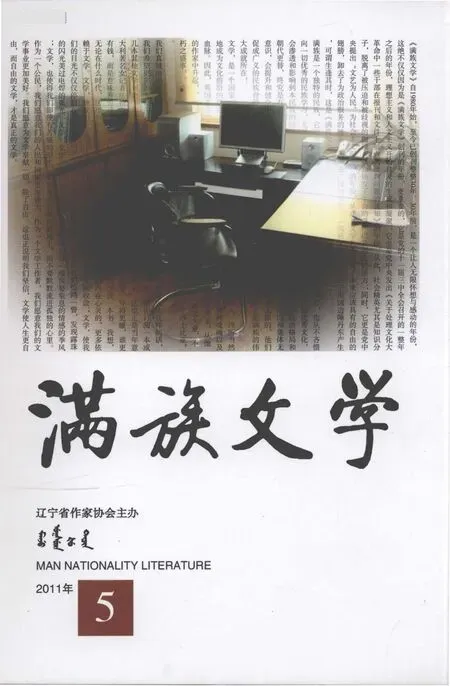藝術:足以讓人成為人嗎?
高海濤
去年11月,首屆東北亞語言文學與翻譯論壇在大連舉行,主辦方給我也發來了邀請,并向我建議了一個發言主題:文學批評與文學翻譯的關系。當時正趕上遼寧省第九次作代會召開,我因無法分身,沒去大連,但還是很認真地寄去了書面發言,以表達我對與會翻譯家和學者們的敬意。下面就是我發言的要點:
20世紀80年代我曾就讀和任教于大學外語系,并有幸去美國訪學。但后來我離開了外語界,從事職業性的文學批評至今。這就像美國詩人佛羅斯特在一首詩中所寫的:清晨的樹林中有兩條路,你走了這一條,另一條就只能隨風遠去。
然而這么多年,我從來也沒忘記自己學過的外語,在我孤寂的批評生涯中,正是年輕時學過的英語和法語給了我信心、勇氣和力量。特別是當我一個人在燈下寫作書評或論文的時候,英語中的每個單詞,法語中的每個音節,都讓我倍感親切和鼓舞。它們就像是遠在異國他鄉的導師,以類似書信那樣私密和值得信賴的方式向我傳遞著來自歐陸、來自北美、來自歷史與當今世界的思想資源和信息。恩格斯曾在致友人的書信中有一段話,我牢記在心,而且有時會恍然覺得,自己也有一個偉大的恩格斯,他就是這樣經常給我寫信的:“讓我用英語給你寫信——不,我還是用優美的意大利語吧,它像和風一樣清新而流暢,它的詞匯猶如最美麗的花園里盛開的百花;也用西班牙語,它酷似林間的清風;也用葡萄牙語,它宛如開滿芳草鮮花的海邊的浪濤聲;也用法語,它像萊茵河一樣發出淙淙的流水聲;也用荷蘭語,它如同煙斗里飄出的一縷煙香,給人以舒適、安逸的感覺。”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那么,多了解一種語言是否就多有一個家呢?維特根斯坦的話似乎印證了這一點,他說,是的,“你語言的邊界就是你思想的邊界”。所以我一向認為,因為批評家的思想視野和思想邊界要比作家更廣闊,更遼遠,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一個中國作家不懂外語,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的話,一個不懂外語的批評家卻很難稱得上是批評家。批評家必須是某種意義上的雙語寫作者。
有沒有不懂外語的批評家呢?當然有,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三位文學批評大師就是先例,特別是別林斯基,他幾乎從未離開過俄羅斯的土地和語言。但從境界和視野上來說,他們是不懂外語的雙語或多語寫作者。當代中國也有許多不懂外語的批評家,他們甚至構成了中國批評家的主體,那他們主要靠什么獲得新的資源和話語呢?靠翻譯,他們的閱讀范圍,基本上是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和外國理論批評。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批評家對中國的翻譯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種依賴或寄生的關系,可以說,文學翻譯是文學批評的直接宿主。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們當前的文學翻譯這個宿主本身并非生態十分良好。我在批評、寫作之外也時常搞點文學翻譯,主要是英美詩歌。我這樣做一是出于對專業的懷舊,二是出于好奇。我一直想不明白,英美那些大詩人的作品,包括獲諾貝爾獎詩人的作品,在被某些翻譯家譯成漢語后何以竟變得平淡無奇?我確信它們在原文中不可能是平淡無奇的。詩人的偉大在于“化腐朽為神奇”,可我們有些翻譯家卻只能化神奇為腐朽,這樣的所謂譯作被莫名其妙地發表和出版,我想恐怕不是翻譯理論或“信達雅”之類的翻譯標準所能解釋的,或者說,我們失去的不是具體的翻譯標準,而是比翻譯更重大的學術標準和文化標準。
美國有一本很權威的人文學通識讀本,作者是理查德·加納羅(Richard Janaro)和特爾瑪·阿特修勒(Thelma Altshuler),這是我非常喜歡看的一本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影印本,并譯出了書名和目錄。但我認為書名的譯法很有問題。英文書名本來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譯應該是“讓人更具有人性的藝術”,或“讓人成為人的藝術”,可北大影印本卻譯成了《藝術:讓人成為人》。這樣譯,語感上比直譯好,但問題是不正確。英文書名中的“藝術”僅僅是一個比喻,就像“談判的藝術”、“妥協的藝術”那樣,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藝術:讓人學會談判”,或者“藝術:讓人懂得妥協”。所以,這種譯法是說不通的。
藝術,足以讓人成為人嗎?我們看到許多藝術家,或者也包括作家和詩人,他們的藝術修為和人格修為不僅并非是統一的,而且即使從普通人的標準看,其在人格、人性及人的情感方面也存在較嚴重的瑕疵,難以讓人稱道。實際上,成為人,這是很高的、涉及人的全面發展的總體性目標,不用說哪一門藝術,就是所有的藝術加在一起,也很難達到這樣的高度。正如這本書的各章內容所表明的,它所討論的不僅僅是藝術,還有宗教與神話,語言與文學等等。這些顯然是更重要的主題,也是人文學的基點和靈魂。
我舉一個書名的譯法為例,不是為了輕慢藝術,也不是想要苛求翻譯,我感到驚訝和不解的是,為什么對這樣明顯的、也比較重大的翻譯失誤,卻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也許我們當前的翻譯界現狀是這樣的,那就是有翻譯,卻沒有翻譯標準;有翻譯,卻沒有翻譯批評。而當沒有人去捍衛翻譯標準,同樣也就沒有人去捍衛學術標準和文化標準了。
與其說是藝術讓人成為人,毋寧說是批評讓人成為人。批評作為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象征,從來就是人文學和人文精神當之無愧的代表。如果一個社會的批評有問題,批評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那可能就標志著人文精神的潰敗。近年來,大家所熟知的話題之一就是文學批評的危機,這種危機論一是指所謂“批評的缺席”,二是指所謂“批評的失語”,但意思都差不多,總之一句話,批評及其不滿,構成了世紀之交中國當代文學的特殊語境和現象。但實際上,我認為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最需要的是同情了解。因為公正地說,現在我們的批評不僅是缺席的,也是缺項的。比如,我們沒有翻譯批評,往大了說,我們沒有社會批評,沒有文化批評,沒有宗教批評。而正因為有缺項,所以才有缺席。道理很簡單,當我們的整個生活還沒有形成必要的批評氛圍和批評習慣的時候,僅僅指望文學批評或文藝批評大有作為,滿足公眾所有的精神和情感期待,是不現實也是不通情理的。
“宗教批評是一切批評的基礎”(The criticism of religion is the basis of all criti cism),這是馬克思說過的話,出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有一次批評家聚會,我引用了這句話,試圖說明批評的眼界應該是整個文化和廣闊的社會生活,沒想到,在座的許多教授竟認為我翻譯錯了,說這句話不是馬克思說的,馬克思也根本不可能說這樣的話。對此我只有莞爾一笑,然后無言。
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曼德爾斯塔姆曾這樣寫道:“韃靼人,烏茲別克人和涅涅茨人/整個烏克蘭民族/甚至伏爾加流域的德國人/都在等待自己的翻譯/或許在此一刻/某個日本人正在/把我翻譯成土耳其語/直接滲透進我的靈魂。”
總之,我對外語深懷感恩之心。有位已經故去的朋友生前曾對我開玩笑,說漢語是我的母語,外語是我的繼母語。我喜歡這個說法,為此我非常懷念這位朋友。我知道自己算不上翻譯家,但我知道什么是翻譯家,翻譯家就是在語言上既有生母也有繼母的人,不僅如此,他還要既傳承生母的美德也要弘揚繼母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批評家呢?批評家是翻譯家的兄弟,他通過翻譯家間接領略到異鄉語言文學的精神風采,然后能夠在世界的總體性上捍衛母語的尊嚴,并體現出對祖國文學與文化的耿耿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