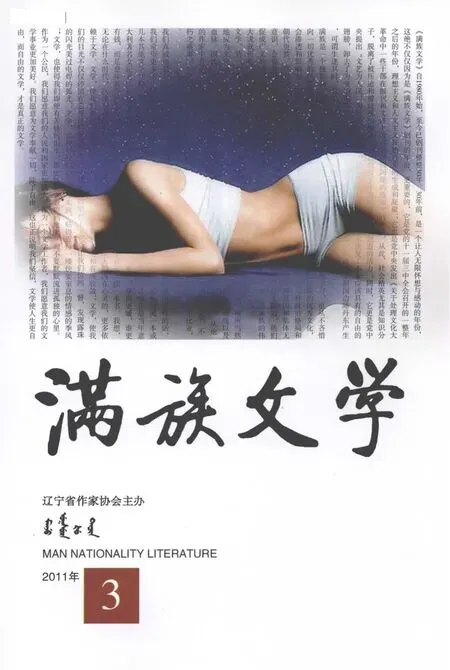子夜雨潺潺
聶鑫森
子夜雨潺潺
聶鑫森
一個個焦雷拽著紫藍的火花,在空曠寂寥的郊外滾動,好像是一個個瘋狂旋轉的車輪,互相撞擊著,發出宏重的聲響。大拇指一般粗的雨鞭,嘶叫著抽打遠近稀稀落落的幾棟漆黑的建筑物和這條坑坑洼洼的土石路面,濺起一大團大團濕漉漉的水霧。
墨黑的天幕上,不時地劃過一道燦白的閃電,如一把利剪“嚓”地剪開厚重的絨布。滿耳是風聲、雨聲、雷聲,卻沒有人聲。在此一刻,盡管時令已是初夏,我卻驀然感到了逼人的寒意。
剛才聽音樂會的興奮,采訪歌星們的愉悅,全在蹬車的途中被這場突如其來的雷雨洗涮得干干凈凈,襯衣濕透了,冰涼地粘在脊背上,讓人覺得難受。但難受總比被雷火擊成一段焦黃的“魚”來得瀟灑,當然在采訪歸途死去應該榮獲“烈士”稱號,可那時我什么都不會知道。
離家還太遠,無法一口氣蹬完這長長的路程,終至被逼到這空空洞洞的公園的門樓下。因為寒冷,因為孤獨,于是一種深重的寂寞便鋪天蓋地而來,幸而這門樓非常粗重非常結實,否則真有可能被壓塌。
這場雨什么時候會停下?不知道。至于我還得在這門樓下呆多久,同樣不可預測。
漸漸地,我的心情開始平靜下來。看看表,快十二點了,長長的夜對我來說,在哪里都一樣。回家?哪里是家?那只能叫“屋子”,所謂“家’,即表示在厚重的屋頂下活躍著幾個生命,妻子、孩子什么的,可我沒有!至今為止,還是光棍一條。
大學畢業,招聘到報社當記者,一晃就是幾年,自個兒去找過對象,多事的熟人也介紹過,就沒讓我碰到過只要見一次面、談一次話就為之神往的異性。并不是我條件有多高,我不問門第不問學歷不問職業,甚至連相貌也不怎么注重,只希望彼此間一個眼神一句淡淡的話,能達到一種默契一種心的共振,可是沒有。于是我開始耐心地等待。就像此刻等待雷雨停歇,我好蹬上車回我那空落落的屋子里去。
身后的這座公園漆黑一片,真靜,它離市區太遠,加上夜深人寂,加上這一場雷雨,再有雅興的人也不會在里面呆。只有我傻呆在這門樓下,孤零零地等待。
雷還在響,雨還在下。
我靠著門樓的石壁,希望想點兒什么,可又什么都不愿意想,腦子里空空的。
有一團黑影,急速地朝門樓撲來,一直撲到門樓下,才猛地剎住車。
又是一個躲雨的人。
我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該有多好,我不再孤獨不再寂寞,在這雨夜,總算有個可以搭腔的人了。但一剎那間,我又失望了,來人是一個女的!這門樓下將劃分出兩個世界,一個陌生的男人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彼此將互相警惕互相提防。在這寂靜的深夜,誰知道會發生些什么事呢。
盡管如此,借著微弱的燈光,我還是把她打量了一陣。她大約二十五六歲的樣子,一蓬短發濕濕地重重地覆在頭上,發梢不停地滴著水;但那張臉很白凈,眉目間充滿一種孩子似的天真;白色的連衣裙緊緊地繃在她身上,勾勒出各個部位很流暢的線條。
我的心不知道為什么“砰”地一響,臉頰竟有些發熱。
也許是她剛才倉皇之中馳入這門樓下,竟然疏忽了我的存在。她利索地支好車,然后抹了抹臉上的水珠子。但突然之間她感覺到了一點什么動靜,她的目光掃向了我。她萬萬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陌生的男人在避雨,抹水珠的那只手停住了,然后又飛快地抹了幾把,那動作分明透出她心底的慌亂。她低低地說了一聲:“這雨……這雨……”然后,迅速地用雙手抓住車把,把車頭調過來,準備離開這地方。
雨嘩嘩地下得挺有耐性。
她把我當成什么人了?一個流浪漢?一個在逃犯?一個無家可歸的小賴子?而且隨時會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進行襲擊!
一種受辱的痛苦和憤怒煎熬著我,心如一塊生鐵被一團烈火焚燒,扭曲成一個難看的形狀。這么大的雨,她一路淋回去,準會感冒的。既然這門樓下只能允許一個人的存在,作為一個男子漢,就應該毫不猶豫地離開這兒,闖到雨中去。
她已經把車頭調過來了。
我大聲說道:“喂,你別走,你留在這兒,雨太大,會感冒的。我就走!不過,我想對你說,我不是歹徒!”
我邊說,邊推上單車,朝門樓外走去,很有一點視死如歸的氣概。
她驚愕地停住了推車,轉過臉來,輕聲對我說:“先生,對不起。我……不走,你也別走,這雨實在太大了。”
“你不怕……”我揶揄地問。
她好看地笑了一下,搖搖頭,顯出一種調皮的樣子,說:“不怕。”
我松了一口氣,心頭一熱,升起一股感激之情,是的,我得感激她對于一個陌生人的信任。
我們重新支好車,各自靠著門樓的一邊,單車成了一道莊嚴的“三八線”,彼此默默地對望著。
我發現在她的發梢上,粘著一縷白色的棉絮,襯著濕漉漉的秀發,很是顯眼。她一定是一個紡織女工,對,這郊外有一爿國棉八廠,她準是下夜班回家,和姐妹們沒走在一道,在途中遇到了這場雷雨,急匆匆只好避到這門樓下來。
我注意到她不停地眨巴著眼睛,借著昏暗的燈光仔細地打量我。她準在猜測我是干什么的,為什么會在這兒避雨。我真想告訴她,我是記者,因為采訪一場音樂會,耽擱了時間才遇到了這場大雨,沒法子趕回去,只好躲到這門樓下來。可我沒有說,打著“記者”招牌行騙的人多著哩,誰信這個!那么向她出示記者證?荒唐。人與人之間,不是憑一個證件可以達到互相理解的。于是,我什么也沒有說,也沒有做,只是默默地靠著門樓。我真想抽一支煙,一摸口袋,煙早濕透了,只好悻悻地掏出來,丟到地上。男人有時可以靠一支煙擺脫尷尬,可我沒有煙,真他媽的晦氣!
她忽然“咯咯咯”地笑起來,笑聲如晶亮的珠子,滾落在石塊地上,滴溜溜地顫到我的腳邊,真好聽。
我問:“你笑什么?”
她不笑了,頓了一陣,才說:“我想起小時候,和哥哥到外婆家去,傍晚時候,遇上了雨,我們躲在一個屋檐下。天漸漸地黑了,雨真大,我好怕。哥哥只比我大兩歲,就哄著我,給我講故事,什么‘灰姑娘’啦,‘小人魚’啦,一直講到雨停了,星星出來了,我們手拉著手到外婆家去。”
這回輪到我笑了,我覺得挺有意思,于是說:“你想讓我哄你?”
她搖搖頭,說:“不過,你總可以講點別的什么吧,不講話,真讓人難受。”
“你喜歡聽什么?”
“我想,你講什么我都會愛聽的。”她有些調皮地說。
我說不清為什么竟有些激動,我說,我給你講《聊齋》的故事吧。
她捂上耳朵,說:“不聽,不聽,盡是鬼呀狐貍呀,怪駭人的。”
“那么,我給你講瓊瑤的《庭院深深》。”
伴著雷聲、雨聲,我繪聲繪色地講起來。
她聽得很認真,聽著聽著,眸子里盈滿了淚水,顯然她被這個故事感染了。
故事快結束的時候,一輛車“呼”地竄到門樓下。因為我們都沉浸在這讓人又辛酸又高興的氛圍里,所以當車猛地剎住,車閘與鋼圈發出難聽的驟然一響,我們都吃了一驚。
從車上跳下一個很粗壯的漢子,臉黑黑的,眉毛很濃,一個腦袋又圓又大。他支好車,走到她靠著的那面墻邊,蹲了下來。
我再沒有心緒講《庭院深深》了,她也再沒有心緒聽了,這個故事就這么被扼殺了,扼殺得悄無人聲。她把身子往旁邊移了移,盡量離那漢子遠一些。
我死死地盯著這漢子,努力地觀察著他。
他是干什么的,為什么這么晚還在外面游蕩?他這相貌,又無端地帶著幾分兇氣。
第二、駐村干部(“訪匯聚”工作組)幫扶。自治區督促各級駐村力量落實幫扶職責,自籌和協調引進幫扶資金、項目。
他勾著頭,理也不理我們,突然伸出手去,在腰部用力地掏著。那兒放著什么?一把匕首?還是一截鐵棍?我全身的每根神經都緊張起來,我得有所準備,別讓他打我一個冷不防!
掏了好一陣,他從腰間掏出了一個小煙鍋和一個小小的黑布煙袋,然后在煙鍋里裝上煙絲,又到腰間去摸了一陣,摸出一個打火機,“叭”地打出一束金黃的火苗,湊到煙鍋前。他鼓起腮幫使勁地吸起來,嗆人的生煙味立刻彌漫開來。
她咳嗽起來。
我依舊盯著他,心里說:你別跟我來這一套,我在看著你,真要動起手來,你也得使把勁兒,在大學我好歹是個田徑隊員,擲鐵餅的,手脖子粗著哩。
大約是風太大,雨斜著往門樓里飄,黑臉漢子又往里面移了移身子,嘟噥了一句:“這狗日的天!”
她臉上出現了莫名的惶恐,下意識地又把身子往里移了移,兩只手抱在胸前,很可憐的樣子。這樣子讓人想起是到了世紀末,仿佛災難不可避免地就要到來。
應該把她叫到我呆的這一邊來,可是該怎么稱呼她?直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但我似乎覺得有權力保護她,好像她真成了我的什么人了。
就叫她馬蘭吧。
“馬蘭,到這邊來吧。”好親切的口吻,我這是怎么啦?莫名其妙!
她自自然然地“喲”了一聲,迅速地繞過三輛單車,站到我身邊來,而且站得很近。她一定早就在等待著這一聲呼喚,要不絕不會反應這么快。
她側起臉,望了我好一陣,忽然說:“星期天,你來我家吧,我媽說給我們包餃子吃,你來嘛。”
“好。我來。”我爽快地答應著。
同時,我又對自己的回答覺得驚異,我這是犯傻還是怎么的?到她家去,她家在哪兒?她媽是什么模樣?一切都是謎,一切皆不可知。她是曲曲折折地告訴這個黑臉漢子我們是什么關系,警告他不要打什么鬼主意。那么說,我們是在演一個小品,而且彼此就這么順順當當地進入了角色。是可笑?還是可悲?一時真還說不明白。
“我媽好喜歡你。”
“嗯。”
“她還說,爸爸快轉業了,特地從廣州給我們帶回一臺錄放機。”
“嗯。是日本的還是美國的?”
“是美國的。”她認真地說。
我有些陶醉,這么說我們是戀人了,而且已經“戀”了不少日子,一剎那間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存在的,真實得連自己都沒有絲毫的懷疑。
黑臉漢子忽然站起來,努力對著我笑了一下,說:“你抽不抽煙?這煙味兒正哩。”
我冷冷地說:“不。謝謝。”
她驚慌地把身子靠住了我,說:“這雨,真討厭,媽準會急死的。”
我大聲說:“別怕,有我哩!”
黑臉漢子尷尬地收回拿著煙鍋、煙袋的手,然后望了望天,再望了望我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我該走了,這雨一時還停不了。”
他推起他的單車,緩緩地走出門樓,然后騎上車,飛快地蹬起來,很快就在大雨中消逝了。
我覺得很內疚。這黑臉漢子應該是個農民工,那煙鍋、煙袋昭示了他的身份。他剛才一定很痛苦,因為他被我們所誤解,正如我開始時被她所誤解一樣!這門樓下,本可以容納許多人的,因為隔膜和猜忌,使他無法呆下去,只好冒雨而去。
她利索地把靠近我的身子移開了,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繞過單車,重新回到門樓的那一邊去。一點也沒有牽掛,一點也沒有依戀。門樓下依舊是兩個互不關聯的世界。
沉默。
雨終于停住了。
到處彌漫著濕潤潤的氣息,一切都顯得很美好。
云縫間漏下了幾點星光。
假如她真是我的戀人,我會邀她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浴著稀疏的星光,去公園里走走,聽聽蟲鳴,看看幽藍幽藍的螢火,讓那些小徑寫下我們纏綿的情愫。可惜她并不是“馬蘭”,“馬蘭”只是她一個短暫的符號,這符號頃刻間就與我毫無關系了。
她望了我一眼,淡淡地說:“雨停了,我也該走了。”
她一邊說,一邊迅速地推出單車,慌慌張張地騎上去,連頭也沒有回一下,就使勁地蹬起來,仿佛為了躲避一場瘟疫。
她走了,如一縷煙,如一個夢。
我依舊靠著門樓,一動也不動,今晚發生的一切,我得細細地咀嚼,而且有一種想痛痛快快哭一場的欲望。
夜更深了。
聶鑫森,男,1948年6月生于湖南湘潭,漢族。中國作協會員、湖南作協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夫人黨》、《浪漫人生》、《霜天梅影》、《詩鬼畫神》;中短篇小說集《太平洋樂隊的最后一次演奏》、《愛的和弦與變奏》、《鏢頭楊三》(英文版)、《誘惑》、《都市江湖》、《生死一局》、《塑料人》、《鐵支子》、《吃官倉考》、《轎杠》、《老號手》;詩歌集《地面與地底的開拓》、《他們脖子上掛著鑰匙》;散文隨筆集《旅游最佳選擇》、《收藏世界的誘惑》、《優雅的存在》、《闌干拍遍》、《一個作家的讀畫筆記》、《觸摸古建筑》等文化專著共30余部。曾獲過“莊重文文學獎”、“湖南文學獎”、北京文學獎、萌芽文學獎等獎項。
〔責任編輯 宋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