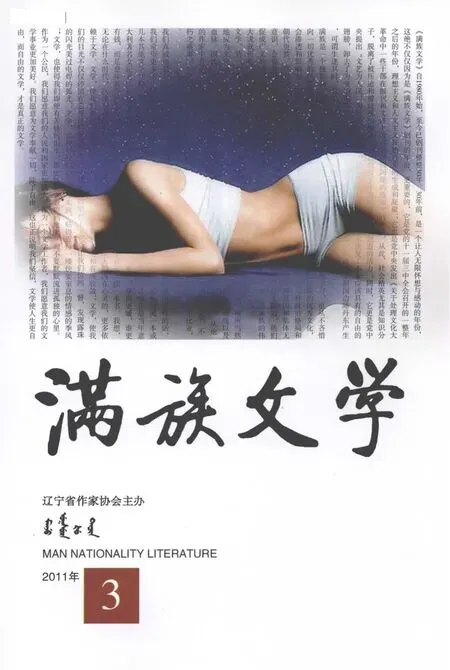薩滿文化圈中心論
趙志忠
薩滿文化圈中心論
趙志忠
一般來說,一種地域文化既然有文化圈,就應該有文化中心。我們認為,中國薩滿教信仰歷史悠久,部分古代民族還和現(xiàn)代民族都有信仰薩滿教的傳統(tǒng);中國東北、西北部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薩滿教信仰的根基;“薩滿”一詞來自中國的女真語。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是世界薩滿文化圈的中心。其理由如下:
1.中國是世界上記載和研究薩滿教最早的國家
在中國歷史上的《二十五史》中,從第一部編年史《史記》到最后一部史書《清史稿》,幾乎都有關(guān)于中國古代民族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記載。
《晉書》中說:肅慎人“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
《后漢書》中記載:“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古代朝鮮人:“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shù)十人相隨蹋地為節(jié)。十月農(nóng)功畢,亦復如之。諸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涂,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
遼代契丹人有祭天、祭祖、祭火種等儀式。據(jù)《遼史》記載:“歲除儀,初夕敕使及夷離畢率執(zhí)事郎君至殿前,以鹽及羊膏置爐中燎之。巫及大巫次贊祝火神訖閣門使贊皇帝面火再拜。”
金代女真人時期,中國的薩滿教比較完整。女真人亦有祭天之禮,據(jù)《金史》記載:“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
元代蒙古人的薩滿祭祀,在《元史》中亦有記載:“元興朔漠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zhì),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遠,報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強為之也。”“其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辭,蓋國俗也。”
從這些記載中,我了解到了古代肅慎人的靈魂不死觀念、匈奴人的祭天神儀式、古代朝鮮人的事鬼神活動、遼代契丹人的祭祀火神的場面、金代女真人的告祭天地祭儀以及蒙古人祭祖儀禮。嚴格地講,所有這些祭祀及儀式都應該屬于薩滿教的范疇。而其中出現(xiàn)的巫、大巫、巫祝等祭師,寶際上就是薩滿教中的薩滿。
清代乾隆年間刊行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書,是我國古代的第一部系統(tǒng)記載與論述薩滿教的著作,這本書比較詳細地記錄了滿族歷史上所信仰的薩滿教,包括各種祭祀規(guī)則、各種神祗以及一系列神歌等,在中外薩滿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薩滿”一詞出自我國的女真語
12世紀中葉,宋代學者徐夢莘在其《三朝北盟匯編》中,第一次記錄了女真語“珊蠻”(saman)一詞,成為中外薩滿教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頁。這個記錄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確的、毫無爭議的“薩滿”一詞的記錄。在清代,“薩滿”一詞使用得相當廣泛,許多學者將其記錄成“薩滿”、“薩瑪”、“薩麻”等,其實都是女真語或后來的滿語saman一詞的音記。乾隆年間出版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曲禮》中就用了滿語saman一詞,盡管后來譯成漢文時寫成“司祝”。
清嘉慶年間,西清在其《黑龍江外記》中,稱達斡爾跳神薩滿為“薩瑪”。光緒年間,曹廷杰在其《西伯利亞東偏紀要》中,將黑斤(即赫哲人)的薩滿記作“叉媽”。
民國年間,凌純聲在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將赫哲族的薩滿記作“薩滿”,與我們今天記錄的用字一樣。
從薩滿一詞的來源及其應用來看,它是北方民族語無疑,絕不是漢語,更不是外國語。眾所周知,西方人知道薩滿和薩滿教是比較晚的。薩滿一詞傳入西方大約是在18世紀。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沙皇彼得大帝派往中國的使節(jié)團中,有兩位荷蘭人——伊斯布蘭特·伊代斯和亞當·布蘭特,在他們撰寫的中國旅行記中,第一次把“薩滿”一詞介紹到歐洲。此后國際上才知道,在中國北方存在著一種原始的信仰,并把它稱之為“shamanism(薩滿教)”。從此,國際上就通用了“薩滿教”這一詞,成為一個專用術(shù)語。后來,許多俄羅斯學者踏上西伯利亞的土地,對當?shù)氐乃_滿教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diào)查,并發(fā)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日本學者又對我國的東北、內(nèi)蒙古等地的薩滿教進行了考察,使世界對于薩滿教有了較深的認識。
3.從地域上看,中國正處于薩滿教文化圈的中心
中國的東北、西北部廣大地區(qū)在歷史上是東北亞最發(fā)達的地區(qū),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國北方各族人民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燦爛的文化。我國古代民族,如鮮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曾經(jīng)在這里建立了地方政權(quán)和國家政權(quán)。元代的實力范圍甚至達到了歐洲大陸,清代的實力范圍也達到了西伯利亞。作為統(tǒng)治民族,作為具有高度發(fā)達封建文化的擁有者,他們的文化向四面輻射,影響到其他民族是極其正常的。而其中的薩滿文化,也會同其它的文化一起影響到周邊的民族。
西伯利亞地區(qū),歷來被認為是薩滿教保留較好的地區(qū)。但最早涉足這個地區(qū)的人,并不是俄國人,而是中國人。因為,在俄國人知道這個地區(qū)之前,他們的活動范圍還只局限于歐洲。俄國人真正涉足西伯利亞是從17世紀開始的。
據(jù)史書記載,自古以來中國北方的許多民族,比如肅慎、突厥、蒙古、契丹、滿等,就居住在貝加爾湖、外興安嶺以及庫頁島一帶,貝加爾湖是中國的“內(nèi)湖”,黑龍江也不過是中國的“內(nèi)河”。
根據(jù)史料記載,我國的鄂倫春人在17世紀中葉以前,一直居住在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北、西起石勒喀河、東到庫頁島的廣大地區(qū)。他們與這一帶的鄂溫克族人、赫哲族人、滿族人友好相處,并與達斡爾人、漢人以及庫葉島上的阿伊努人(蝦夷)等頻繁交往。
我國的達斡爾族在12世紀以后,從西拉倫河、洮兒河一帶北遷至黑龍江流域,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東至精奇里江(結(jié)雅河)、牛滿江(布里雅河)的廣大地區(qū)。在沙皇俄國時期的文獻中記載,這一帶被稱為“達斡爾地區(qū)”。即使是今天,在我國的滿洲里至俄羅斯境內(nèi)的赤塔之間還保留有“達斡爾里亞”火車站的站名。在《蘇聯(lián)大百科全書》第13卷中,還有“達斡爾里亞”的辭條:“一個歷史地理名稱,在外貝加爾湖的東邊,一部分在黑龍江流域(至17世紀為止),一直伸展到石勒河、額爾古納河、結(jié)雅河、布里雅河和部分松花江及烏蘇里江流域。這一區(qū)域的名稱來自達斡爾族。因為那時候他們即住在西達雅布羅諾威嶺以東的地區(qū)。”17世紀中葉,達斡爾人同沙俄武裝入侵者進行了近半個世紀的斗爭,為保衛(wèi)我國東北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后,達斡爾人受命于清王朝,南遷于嫩江流域,并且世代生息繁衍在這塊土地上。
庫頁島歷來屬于中國領(lǐng)土,只是在1840年以后才被沙皇俄國占領(lǐng)。在庫頁島世代生息的費雅喀、鄂倫春、庫頁等民族,也屬于我國北方民族的一部分。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1年)編著的《皇清職貢圖》中說:“庫野(頁)居東海島之雅丹達里堪等處。”“土語謂之庫野話,歲進貂皮。”“費雅喀在松花江極東,沿海島散處、以漁獵為生。男女俱衣犬皮,夏日則用魚皮為之。性悍好斗,出入常持兵刃。歲進貂皮。”19世紀中葉,黑龍江下游的費雅喀人有2679人,共140戶,居住在39個村屯中。此外,在鄂霍茨克海盼精灣海岸有15個村屯,在堪察加半島西北岸有6個村屯,俄留土爾灣海岸有9個村屯。據(jù)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的統(tǒng)計,當時在巴蘭、烏喀、俄留士爾等屯還有2500人,其中1750人游牧于北緯56度的堪察加半島上。也就是說,在俄國人占領(lǐng)庫頁島及其海域之前,我國的北方民族已經(jīng)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了,他們的足跡甚至到達了堪察加半島、阿留申群島。
今天,居住在俄羅斯境內(nèi)的一些西伯利亞民族,與我國的一些民族是同一民族。布里亞特人就是中國的蒙古人,納乃人就是中國的赫哲人,埃文克人就是中國的鄂倫春人。此外,烏德蓋人、埃文人、奧羅克人、愛斯基摩人等,都與我國北方民族在語言文化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美洲印第安人來源問題一直是一個令世人矚目的問題。大多數(shù)學者都比較贊成“白令海峽“說,即印第安人在大約1.5萬年前越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大陸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祖先是亞洲人。一些專家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屬蒙古人種,其語言文化與中國北方民族有一定的聯(lián)系。而其中薩滿教的信仰就是與中國北方民族最為相同的特點。很有可能,印第安人從西伯利亞到阿拉斯加的同時,也把傳統(tǒng)薩滿教信仰帶了過去,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如果“白令海峽”說成立,那么,中國北方民族與印第安人的關(guān)系就相當密切了,其語言文化也應該接近。毫無疑問,薩滿教文化是從亞洲帶過去的一種傳統(tǒng)的宗教文化。
4.中國北方民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薩滿教
在中國東北、西北部仍然有十多個民族,大約兩千萬人,保留著薩滿教的信仰,或者留有一些薩滿教的殘余。這一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所無法相比的,被稱作薩滿教基地的西伯利亞也不例外。突厥語民族雖然在歷史上改信了伊斯蘭教,蒙古語民族雖然也改信了藏傳佛教,但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歷史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薩滿文化的影子。在滿-通古斯語民族中,薩滿教的信仰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在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赫哲族、滿族以及朝鮮族中,薩滿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祭祖、祭神、續(xù)家譜等活動仍然繼續(xù)。
自古至今,中國的北方民族一直生息、繁衍在北亞和東北亞的廣大地區(qū)。他們在歷史上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權(quán),這在當時應該是世界上先進民族文化的代表。他們的文化,包括薩滿文化向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施加影響是極為正常的。美洲的印第安人、西伯利亞的眾多小民族、北極圈內(nèi)的愛斯基摩人以及東北亞的其他一些民族所信仰的薩滿教,與中國北方民族所信仰的薩滿教極為相似的事實,就足以說明中國是世界薩滿教文化圈的中心。
〔責任編輯 端木靜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