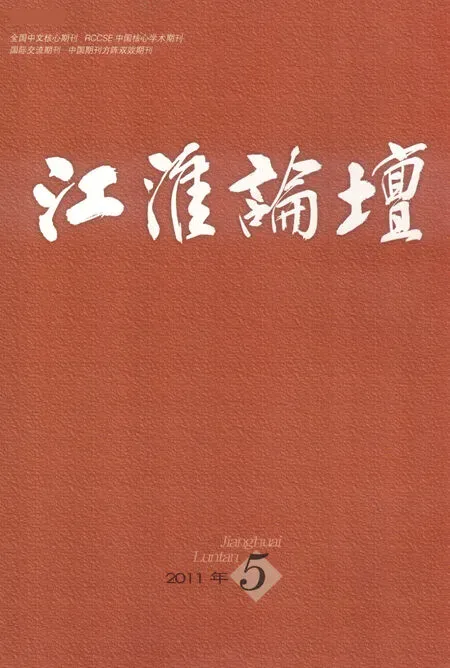方苞的文論思想及其散文創作特色*
江小角
(安徽大學歷史系,合肥 230039)
方苞的文論思想及其散文創作特色*
江小角
(安徽大學歷史系,合肥 230039)
方苞作為桐城派的創始人,一生注重名節,身懷天下之志,主張經世致用,體察下情,關注民生,這些對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也是桐城派之所以能綿延幾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方苞"義法"說的文論思想,為桐城派文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影響久遠。方苞的散文創作實踐,是以他自己創立的文論思想為指導,體現出文章布局結構嚴謹,創作內容講究取材的多樣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創作特色,主要表現為敘事簡潔傳神,說理透徹新穎,語言質樸雅潔,寫人生動形象。因此,從方苞的創作實踐來看,他也堪稱為桐城文派之正宗與楷模,為后世桐城派作家樹立了典范。
方苞;文論思想;清代散文;創作特色
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姚鼐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馀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1]904袁枚稱方苞為“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2]因此,方苞歷來被認為是桐城派的創始人,對桐城派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人稱:“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劉先生(劉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方苞是明初四川斷事方法的裔孫。曾祖象乾,官副使,避寇僑居江蘇上元(今南京市)。祖幟,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至興化縣教諭。父仲舒,字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詩人。贅于六合吳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其時,方氏家境衰落,因此他說:“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郁,旦晝嗟吁。吾母疲疴間作。”“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寧,業盡落。賓祭而外,累月逾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 ”[1]504“家無仆婢,吾母逾五十,猶日夜從灶上掃除,執苦身之役。”[1]502他在為胞弟椒涂寫的墓志銘中,也道出了其童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他說:“自遷金陵……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暄,至東墻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 ”[1]497
方苞很小就隨父遷至上元城內土街。時黃岡杜睿、杜岕兄弟皆寓于江寧(今南京),桐城錢澄之、方文亦時往來,與仲舒常相唱和。方苞說他“仆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為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1]174-175方苞20歲左右,外出授徒,往來江淮河濟。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獲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于學使高裔。23歲應鄉試,即遭落榜。后隨高裔去京師,游太學。其文章得到李光地等人的賞識,同時得交前輩學者、史學家萬斯同,鉆研經學。在劉言潔、劉拙修等人的影響下,讀研宋儒之書,遂傾心程、朱之學。以致他在25歲時,與姜宸英、王源論行身祈向時說:“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這也成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準繩。此后幾年,他在涿郡、寶應等地開館授經,曾兩次參加順天鄉試,均遭落第而南歸。康熙三十八年,在他32歲時,舉江南鄉試第一。次年至京師,后兩次參加禮部考試,均未及第。在京城結交思想家李塨,并與李交談,因學術觀點不合,旋即南歸。康熙四十五年,即其39歲時,再至京師,應禮部試,中進士,位列第四。就在將要參加殿試授官之際,方苞聞母病遽歸,失去殿試奪魁的機會。
康熙五十年(1711),是方苞一生的轉折點。這年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上奏康熙皇帝,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語多狂悖”為由,彈劾戴名世。方苞因給該書作序,牽連被逮下獄。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獄決,方苞被判死刑,只因“圣祖一日曰:汪霦死,無能古文者。”李光地等人極力營救,因此回答皇上說:“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因而他蒙皇恩赦免釋放,出獄隸籍漢軍。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諭旨:“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1]515旨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第二天,方苞被召入南書房,幾天之內,先后撰寫《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慶祝賦》等,每次呈奏康熙帝,都受到贊賞,以為“此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1]515此后命以白衣(即無功名而替官府當差的人)入直南書房。但其家人因受《南山集》案的牽連,仍全部沒入旗籍。
從《南山集》案蒙皇恩赦宥,入直南書房,方苞開始了他30余年的官宦生涯。作為皇帝的文學侍臣,他移直蒙養齋,教授諸皇子,編校樂、律、歷、算等書,潛心于《春秋》、《周官》研究,撰寫《周官辨》、《春秋通論》、《周官析疑》、《容城孫征君年譜》等書。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開始,他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等職達十年之久。
雍正皇帝即位后,對以張廷玉為代表的桐城學人非常信賴,垂愛有加,這也使方苞的政治處境較康熙朝有了進一步改善,方苞合族均被赦歸原籍。雍正九年,方苞64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后遷翰林院侍講、翰林院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一統志館總裁,奉命校訂《春秋日講》。雍正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副總裁;九月,高宗乾隆皇帝繼位,有意對方苞委以重任。乾隆二年六月,擢禮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辭;乾隆六年冬,《周官義疏》纂成,進呈皇上,留覽兼旬,一無所更,下命刊刻;第二年,方苞年屆75歲,以時患疾病,乞解書局之職,回家安度晚年,乾隆帝許之,并賜翰林院侍講銜。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里第,享年82歲。
方苞作為桐城派的創始人,一生注重名節,身懷天下之志,主張經世致用,體察下情,關注民生,這些對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也是桐城派之所以綿延幾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文論思想,不僅對后世桐城派作家的創作指明了方向,而且給清初文壇注入了新的活力,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以“義法”說為核心的文論思想
“義法”說是方苞文論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論形成的基石。他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1]58這里方苞把《易經》作為他“義法”說立論之本,這不僅抬高了“義法”說的地位,而且也明確指出了“義法’說中“義”與“法”的統一,“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即內容與形式要相符合。也就是說“義”包含在“法”之中,而“法”又是“義”的具體表現。因此方苞以“義法”論文,不僅注重文章的義理精當、深刻,而且要求作文必須遵循文章的體例和寫作的規則,如對材料的取舍和安排以及遣詞造句的要求等問題。所以說,方苞“義法”說的文論思想為桐城派文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影響久遠。
第一,方苞“義法”說形成的歷史背景。首先,方苞“義法”說的產生,是匡正時代文風的需要。明末清初,是中國社會王朝更迭的動亂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學術思想開始劇變的時期。文人士大夫多半經過農民革命和滿族入關的巨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沖擊,迫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或奮起反抗,或歸附于清;或削發為僧,隱跡山林,寄情山水。在文學創作方面表現為:一是重道輕文;二是空洞無物,無病呻吟,摹仿之風越演越烈。有識之士或激烈抨擊,或憂心忡忡,或無可奈何。如錢牧齋說:“今之人耳傭目僦,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即而視之,枵然無所有,則謂之無物而已矣。”[3]黃梨洲哀嘆:“世無文章也久矣!”古之文“奈何降為今之臭腐乎?”[4]戴名世對明末以來 “文風壞亂”、“文妖疊出”的現象,認識得更加深刻。他說:“往者文章風氣之趨于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5]107“文體之壞也,是非工拙,世無能辨別,里巷窮賤無聊之士,皆學為應酬之文,以游諸公貴人之門。然必濟之以狡譎諛佞,其文乃得售。不然,雖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世皆熟視之若無睹。”[5]293因此,戴名世以振興古文為己任,決心“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于日盛也”。方苞針對當時的文風,更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訓示門人沈廷芳時說:“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1]890方苞在批評這個時期文壇怪異現象的同時,提出了自己作文的一套主張,即要“言有物”、“言有序”,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自己的“義法”說,這是對清初文壇現象的一種撥亂反正,是代表時代和文學創作發展要求的,它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其次,方苞的“義法”說是在吸收同時代進步之士文論主張基礎上,加以升華、提煉形成的。戴名世、方苞為了振興古文,在他們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群。戴名世說:“余年十七八時,即好交游,集里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 ”[5]73他入京師后,廣交賓朋,討論文章得失。他常說:“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游四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皋、劉北固,長洲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皋年少于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類而得之。”[5]118這里可以看出,方苞作文及文論思想的形成與戴名世對他的影響和啟迪是分不開的。
方苞“義法”說的立論根據就是《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在方苞之前,戴名世就提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5]6這里可以看出,他們立論之源同是《易》。因此,“戴名世以‘言有物’為‘立言之道’,是方苞義法說的先導。 ”[6]
再次,萬季野、程綿莊等人對方苞“義法”說的創立,也產生過積極的影響。萬季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學家,他曾告誡方苞說:“子誠欲以古文為事,則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后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1]333程綿莊說:“古先圣賢之論文,大要以立誠為本。有物即誠也。言之中節則曰有序,如是則容體必安定,氣象必清明,遠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于是而止,故曰辭達而已矣。故為文之道本之以誠,施之以序,終之以達。”[7]因此,方苞“義法”說的理論,是在汲取同時代作家、學者文論成果的基礎上創立的。方苞高人一籌之處,就在于他把前人的理論,予以全面總結,使其具體化、理論化,并在實踐中廣泛運用。
第二,方苞“義法”說的主要內容及其影響。
首先,“義法”是指文章體裁對寫作內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從文學自身的主體性出發,在文章內容方面,強調“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強調“言有序”,并且認為內容決定形式。他通過評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學作品,得出各種文體在創作上的不同要求。他在《答喬介夫書》中說得非常清楚。他對寫作侍講公喬萊的表志或家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志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志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臃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截,俾情事不詳,則后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 ”[1]137他在文中還分別列舉了《國語》、《春秋》中列傳的例子,加以論述,認為在傳志、家傳等文體中,不能將奏議收錄其中,“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采擇,于義法乃安。 ”[1]138所以方苞在評論前人作品時說:“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每篇文章,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并且前后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這就是說寫作的內容必須符合文體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說的“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1]64。根據這一“義法”說的要求,創作出來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其次,“義法”是對文章選材以及材料取舍詳略提出的要求。方苞在《與孫以寧書》中說:“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1]136這里方苞明確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必須與人物的身份相符,“虛實詳略”要因人而異,即由“義”來決定“法”。方苞在《書漢書霍光傳后》中說:“《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后之良史取法焉。”還說:“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1]62-63這里方苞明確指出文章體裁的選擇以及材料的運用,都是“義法”所要討論的范疇。方苞在《史記評語》中,也是從繁簡詳略方面來規范“義法”的。他說:“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后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 ”[1]181這里他顯然是對《史記》、《漢書》中的長篇文章予以肯定,因為“事體之本大”,無需用長短去要求它們。他評《史記·項羽本紀》這一長文時,贊賞該文“先后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1]850他認為《項羽本紀》中對“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以三語括之。”是因為“其事與言不可沒,而與帝紀則不可詳也。”[1]851再次說明作文宜詳則詳,當略則略,必須符合“義法”的法度。所以方苞說:“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 ”[1]851
再次,“義法”要求作文追求言簡、雅潔的文風。方苞說:“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于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為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于斯矣。 ”[1]853這里方苞所言的潔,不僅指作文在語言文字方面要簡練,而且要在義法的原則下,對文章所要表達的內容有所取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符合他所說的“氣體最潔”。方苞特別稱贊《史記》行文的雅潔,如在《書蕭相國世家后》中說:“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于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最為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于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 ”[1]56他認為《史記》行文符合義法的準則,就能實現文風“雅潔”。因此他說《史記》“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1]856方苞常常以《史記》等文作為自己創作時的語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樸、簡潔的文風。方苞在創作中力求實踐自己的文論思想,寫出了一系列的精美散文,如《左忠毅公逸事》等。
方苞“義法”說的文論思想強調作文在內容與形式方面達到完美統一,并對文學創作上的藝術表現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具體要求,在我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頗具特色,具有一定的歷史地位。由于他的文論思想偏重于對古文傳統的繼承,注重對我國古文創作經驗進行全面科學的總結,評斥是非得失,使人們在創作實踐過程中便于運用。因此,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論思想日臻完善,文風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廣為流傳,一時傾倒朝野,這些與方苞“義法”說的理論容易被人們接受、符合時代發展需要是分不開的。因此后人稱頌他有“能集古今文論之大成”的歷史功績。[8]
二、情真義摯寓意深遠的散文創作特色
方苞的散文創作實踐是以他自己創立的文論思想為指導。他的文章結構嚴謹,講究取材的多樣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創作特色,主要體現為敘事簡潔傳神,說理透徹新穎,語言質樸雅潔,寫人生動形象。因此,從他的創作實踐來看,方苞也堪稱為桐城文派之正宗與楷模,為后人樹立了典范。
首先,方苞的散文創作注重寫實,強調詳略得當。他說:“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1]201他在《儒林郎梁君墓表》中寫到:“余謝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為表志,非敢重要,懼所傳之不實也;……君子之善善也,務求其實耳。”這說明方苞把創作的源泉,建立于真實生活的基礎之上,文章的生命力就在于有豐富多彩的生活實踐。如他在寫《孫征君傳》中,就很好地貫徹“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的創作要求。[1]136方苞在該文中,通過寫孫奇逢為楊漣、左光斗等人的營葬,上書孫承宗,斥責魏忠賢,入清后誓不為仕等事例,將孫奇逢不阿權貴、嫉惡如仇的高風亮節,表現得淋漓盡致,達到了“詳者略,實者虛,而征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的效果。[1]137再如他撰寫的《左忠毅公逸事》,突出重點地介紹左光斗與史可法交往中的幾個片斷。即初次相識,獄中探視,不忘師訓等,表現出左光斗的識才之智、愛才之心、護才之行。同時,方苞的人物描寫達到了出神入化、栩栩如生的境界。這也是他寫的許多人物傳記能被后人傳誦的主要原因。他在寫史可法打扮成清潔工,冒險入獄探望左光斗,看到他:“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脆,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地何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1]237-238這里方苞通過對左光斗、史可法兩人形貌、動作、語言對話的描寫,刻畫出左光斗身陷囹圄,仍心系國家大事的愛國情懷。同時方苞也深刻揭示了人物內心的矛盾,左光斗為了國家利益,為了保護人才,讓天下事有人來支柱,極力壓抑師生之誼,讀后令人肅然起敬,振奮不已。此外,他撰寫的《田間先生墓表》、《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石齋黃公逸事》、《獄中雜記》等文章,無不以形象生動的人物描寫而取勝,這也是方苞文名震天下的原因之一。
其次,方苞的散文創作,寓論理于敘事之中。顧炎武在論述太史公作史筆法時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于敘事之中,即見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9]方苞繼承了太史公的筆法。他在撰寫人物傳記之類的作品時,往往在文章的結尾或文章中間,插入自己的議論,或加上他人的評述,有的以傳贊的形式出現,有的言古道今,諷刺現實,抨擊時弊;有的借題發揮,抒發個人情懷,暢言對社會及人生的感悟,或褒或貶,無不暗含作者心志。方苞的《左仁傳》,寫左忠毅公后代左仁,其祖患了傳染病,家人害怕傳染,沒有一個人敢與之接近。其時左仁才只有十五歲,也知道此病有傳染的危險,但為了燠祖足寒,陪居六年,終染病而歿,鄉人以為“愚”,而方苞在文末卻說:“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遭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為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為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為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1]222方苞就是從家庭小事入題,小中見大,廣而推及國家大事,從篤于親人而推之為忠于君父,從而頌揚左忠毅公與同難諸君的孤忠大節和報國之志。又如他寫的《轅馬說》,文中說“馬”,其實處處指人,所寫的現象均為當時的社會現實。“嗚呼!將車者,其慎哉!”[1]79旨在點出本意,敬告統治者識馬用人,不可不慎重。有時在敘事過程中,插入人物對話或人物自白,對某事某人作出評價,點明旨意,起到一針見血的效果。如方苞撰寫的《獄中雜記》就是用這種筆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成為傳世典范之作。
再次,方苞的散文創作,運用各種藝術手法,力求散文語言的形象、生動。方苞認為文之工致,不在辭繁言冗,而在于“情辭動人心目”,即以真情來打動人心。他寫的《兄百川墓志銘》、《弟椒涂墓志銘》、《先母行略》、《書孫文正傳后》、《亡妻蔡氏哀辭》、《王瑤峰哀辭》、《仆王興哀辭》等文章,或講述家境、敘述兄弟手足之情;或感慨先賢生不逢時,難有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字里行間,或表達兄弟之情;或講述母子之情;或頌揚愛國憂民之情;或懷念夫妻之情;或暢言朋友之情;或描述主仆之情,言語質樸,情真義摯,讀之動人心魄,感人肺腑,回味無窮。
方苞在其寫作的文章中,還經常運用修辭手法,以增強文章的活潑性和感染力。他在《書老子傳后》里,為了講述老子確有其人,從老子的姓氏、籍貫、官守到他的子孫后代的封爵、居住等情況,運用整齊的排比句式,不厭其煩,詳細描述,旨在加深讀者印象,張揚文章氣勢,增強說服力,同時讓讀者欣賞起來,有一種美的享受。有時他還在文章中插些比喻,通過形象而又生動的比喻,來闡明抽象深奧的道理。如他在《與程若韓書》中,反對行文繁瑣冗長,認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粗礦去,然后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1]181可謂比喻生動貼切,寓義深刻明了。有的文章他還用比興手法,如在《題舒文節探梅圖說》中,以“芝蘭之萎折”,喻舒公遭遇之不幸;以“西山之梅”,喻舒公的人品及其處世原則。又如在《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中,以同樣的手法,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關心和焦慮,他說:“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學先圣之道,仁義根于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顛連焉;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 ”[1]637在上述文章中,方苞托物言志,喻人喻己,表現出他仰慕先賢、憂國憂民的人格魅力。
方苞還在與友人書信作品中,夾雜一些對山水風光、自然景色的描寫,讓人讀起來意韻深長、無枯燥之感,別有一番情趣。他在《與王崑繩書》中,就插入了精彩的山水風光描寫,他在信中寫到:“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饑驅宣、歙間,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云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郁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閑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這里他既贊揚山水之美,又懷念古人隱跡山林的清閑生活,并生羨慕之情。他說:“使苞于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為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1]667這里他借景抒懷,懷古思賢,表現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與世無爭的人生哲學。
總之,方苞以他簡嚴精實的文風,在“義法”理論指導下,追求道與文并重,把古文寫得清新雅潔、自然流暢,并富有極強的感染力,在清初文壇可謂獨樹一幟,開創了一代文章風氣之先。盡管后世之人論及方苞文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貶不一。譏之者謂:“先生文,嘆其說理之精,持論之篤。……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隊之聲。”“措語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閎放也”;[10]“旨近端而有時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11]尊之者則謂其文為清代 “百馀年文章之冠”,[1]904“源流極正”,[12]“宋以后,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1]902實事求是地說,方苞的文章氣勢略顯孱弱,文采略顯貧乏,不能說不是其缺陷;然而他的文章精煉平實,澄清淡雅,注重寫實,憂國思民,關注民生,寓意深遠,有很強的思想性和現實針對性,在當時可以說起到了矯正文風的作用。因此劉開評其文:“豐于理而嗇于辭,謹嚴精實則有余,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13]此論頗為精當。
[1]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第二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48.
[3]國立編譯館主編.清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上集)[M].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9.
[4]黃宗羲著.陳乃乾編.山翁禪師文集序[M]//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370.
[5]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C]//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
[6]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84.
[7]賈文昭主編.中國古代文論類編[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295.
[8]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4.
[9]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29.
[10]方東樹.書望溪先生集[M]//儀衛軒文集.清同治七年刻本.
[11]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M].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212.
[1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4: 1528.
[13]劉開.與阮蕓臺宮保論文書[C]//漆緒邦,王凱符選注.桐城派文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06.
(責任編輯 文 心)
I206.2
A
1001-862X(2011)05-0170-006
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桐城文派史”(09YJA751002);安徽大學211三期“桐城派研究”及科研創新團隊“安徽地域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
江小角(1963-),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