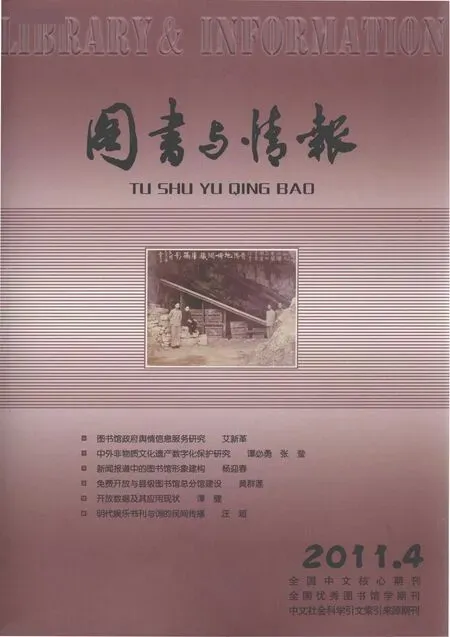文瀾閣《四庫(kù)全書》抗戰(zhàn)苦旅線始末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日本侵略者對(duì)文瀾閣《四庫(kù)全書》覬覦已久,虎視眈眈。浙江省圖書館館長(zhǎng)陳訓(xùn)慈先生預(yù)感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面臨被掠奪的危險(xiǎn),四處奔走呼吁,多方爭(zhēng)取協(xié)調(diào),緊急策劃,果斷決定采取轉(zhuǎn)移的辦法來(lái)保護(hù)《四庫(kù)全書》。
1 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抗戰(zhàn)大轉(zhuǎn)移始末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在中華大地肆意踐踏,隨后,滬凇戰(zhàn)爭(zhēng)打響。社會(huì)上傳言,東北淪陷后,日本侵略者將沈陽(yáng)文溯閣《四庫(kù)全書》已運(yùn)往東京,北京宮內(nèi)的文淵閣和圓明園的文源閣《四庫(kù)全書》也快要被日本侵略者搶走了。不日,上海、杭州屢遭敵機(jī)轟炸,杭州城危在旦夕,文瀾閣《四庫(kù)全書》隨時(shí)有被毀或被掠奪的危險(xiǎn)。
時(shí)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zhǎng)的陳訓(xùn)慈先生(圖七),意識(shí)到文瀾閣《四庫(kù)全書》面臨被略?shī)Z的危險(xiǎn)境地。乾隆年間繕抄的七部庫(kù)書,南三閣中只剩文瀾閣一部,他深感保護(hù)庫(kù)書責(zé)任之重大。陳訓(xùn)慈一面向教育廳報(bào)告情況,要求調(diào)撥庫(kù)書遷移經(jīng)費(fèi),一面動(dòng)員全體館員趕制木箱,準(zhǔn)備將庫(kù)書裝箱轉(zhuǎn)移。
1937年8月1日至3日,浙江圖書館全館職工集聚孤山分館,搶裝書籍共計(jì)228箱,其中庫(kù)書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凌晨,庫(kù)書離館運(yùn)往江干碼頭裝船,沿錢塘江逆行。8月5日午時(shí)許,抵達(dá)富陽(yáng)漁山江邊碼頭,雇工卸船,肩挑背扛至臨江十五里的石馬頭村密藏(圖三、圖十一),且將要緊的幾部藏入村口山上的墓穴里(圖八)。浙江圖書館毛春翔、葉守榮、夏定域三人留守,負(fù)保管之職。
密藏4個(gè)月后,日本侵略者轟炸杭州的炮火越來(lái)越烈,富陽(yáng)漁山可聞炮聲,漁山安全頓成問(wèn)題。1948年編修的《富春漁山趙氏家譜》中記載道:“由總務(wù)主任史君美誠(chéng)向當(dāng)?shù)刳w君坤良及夏君定域懇商,借得運(yùn)費(fèi)二百數(shù)十元……雇工租船,將庫(kù)書運(yùn)至富春江邊裝船運(yùn)往桐廬。船至半途,因船重又加上逆向,被擱淺。后向浙江大學(xué)借得幾輛卡車,卸船裝車,化了三天時(shí)間才運(yùn)抵建德北鄉(xiāng)松陽(yáng)塢暫存。”最后運(yùn)抵浙閩贛三省交界處的浙江省龍泉縣。
抗戰(zhàn)形勢(shì)日趨緊張,庫(kù)書在龍泉同樣不能久留。1938年3月27日,遵照當(dāng)時(shí)教育部的要求,文瀾閣庫(kù)書從龍泉向西轉(zhuǎn)移。幾大客車庫(kù)書轉(zhuǎn)輾迂回在江西武夷山和仙霞嶺之間,遇到困難與險(xiǎn)情不計(jì)其數(shù)。從浙江龍泉到福建浦城,又折回到浙江江山,僅這段路程,就經(jīng)歷了新嶺、王坊、八都、木岱口、供村、花橋、山路、富嶺、沙婆橋、十八里、仙陽(yáng)、杉坊、達(dá)塢、力牧、楓嶺關(guān)、二十八都、保安、峽口、茅坂、石后、淤頭、清湖等20多個(gè)鎮(zhèn)。
折回江山途中,車過(guò)江山峽口時(shí),因車輪爆裂,一車書側(cè)翻壑澗中,有11箱摔入江中,夏定域、毛春翔等護(hù)送人員急從水中打撈,借用江山縣城城隍廟,在天井中晾曬。后因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經(jīng)常落在江山縣城上空,庫(kù)書只能一邊轉(zhuǎn)移一邊保持車箱通風(fēng),防止霉變。庫(kù)書從江山上浙贛鐵路過(guò)江西,到湖南長(zhǎng)沙,從湘北到湘南,直奔貴州貴陽(yáng),至4月底運(yùn)抵貴陽(yáng),存西郊張家祠堂。
1938年9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對(duì)貴陽(yáng)進(jìn)行轟炸,庫(kù)書又被迫轉(zhuǎn)移。1939年2月,文瀾閣《四庫(kù)全書》再次轉(zhuǎn)移至貴陽(yáng)城10里之外的金鰲山山腰的地母洞內(nèi)(封面圖)。此洞四周一片荒涼,人煙罕至,較為安全。洞深漏水,陰暗潮濕,保管員夏定域、李潔非、史美誠(chéng)等視庫(kù)書為己命,為使庫(kù)書減輕損壞程度,他們?cè)O(shè)法找來(lái)石灰,撒于四周,墊于書箱底下;找來(lái)工具將地母洞外邊開挖溝道,以利卸水;不顧勞累,經(jīng)常搬動(dòng)書箱位置;每年晾曬一次改每年晾曬二次。他們恪盡職守,歷時(shí)六年。
1944年,日本侵略者從廣西北犯貴州,11月貴州全面告急,12月8日至23日,文瀾閣庫(kù)書被迫再度轉(zhuǎn)移,長(zhǎng)途西遷至四川重慶青木關(guān)。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無(wú)條件投降,中國(guó)人民八年抗戰(zhàn)取得勝利。重慶方面成立了以陳訓(xùn)慈等人為常務(wù)委員會(huì)的“文瀾閣四庫(kù)全書保管委員會(huì)”。1946年5月15日,在保管會(huì)的籌劃安排下,庫(kù)書取道川南入黔,經(jīng)湘贛重回浙江,7月5日抵達(dá)杭州。從1937年8月4日《四庫(kù)全書》裝箱離館,到1946年7月5日重回杭州西湖孤山文瀾閣,經(jīng)歷了長(zhǎng)達(dá)8年又11個(gè)月的“抗戰(zhàn)苦旅”。
2 見證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抗戰(zhàn)大轉(zhuǎn)移的幾位當(dāng)事人
陳訓(xùn)慈(1901—1991),字叔諒,慈溪官橋村人。1924年畢業(yè)于國(guó)立東南大學(xué),歷任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編譯、中央大學(xué)史學(xué)講師、浙江大學(xué)史地系教授。1932年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zhǎng),10年任職中,推行普及社會(huì)教育與提高學(xué)術(shù)研究相兼顧的辦館方針,實(shí)行通年全日開放制度,先后創(chuàng)辦《文瀾學(xué)報(bào)》、《浙江圖書館館刊》、《圖書展望》、《讀書周報(bào)》等。“七·七”事變后,聯(lián)絡(luò)浙江大學(xué)、浙江博物館等單位,創(chuàng)辦《抗敵導(dǎo)報(bào)》,呼吁抗日。新中國(guó)成立后,歷任浙江省政協(xié)委員、民盟浙江省委顧問(wèn)、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huì)主任委員等職。90歲壽辰時(shí)捐獻(xiàn)《丁丑日記》手稿及148封各界名人信札給浙江圖書館。工古文詞,尤精歷史,著有《五三慘史》、《世界大戰(zhàn)史》、《晚近浙江文獻(xiàn)述概》等。
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為使文瀾閣《四庫(kù)全書》及時(shí)轉(zhuǎn)移,陳訓(xùn)慈在多次求助教育廳只領(lǐng)到300元轉(zhuǎn)移經(jīng)費(fèi)后,以個(gè)人名義四處舉債。他在日記中記述:“民國(guó)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為運(yùn)輸款,已向張君曉峰借二百金,自墊二百金,今悉馨。無(wú)應(yīng)挑工的工資,乃往訪振公僅借得六十金,應(yīng)付頗不易。”[1]
1940年10月,陳訓(xùn)慈應(yīng)兄長(zhǎng)陳布雷邀請(qǐng),辭去兼職到重慶任國(guó)民政府軍事委員會(huì)第二處秘書。這期間,他利用一切機(jī)會(huì),多次向蔣介石、陳立夫匯報(bào)文瀾閣《四庫(kù)全書》轉(zhuǎn)移密藏貴陽(yáng)的詳細(xì)情況及困境,使重慶國(guó)民政府更為關(guān)注文瀾閣庫(kù)書安危。1943年春,蔣介石電逾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囑“地母洞潮濕,藏書恐霉?fàn)€,應(yīng)另覓安全處所遷藏。”
夏定域(1902—1979),字樸山,浙江富陽(yáng)里山鎮(zhèn)古溪塢人。1923年入揚(yáng)州揚(yáng)子淮鹽總棧公立初級(jí)中學(xué)任教,后任廣州中山大學(xué)助教。1932年任教杭州之江大學(xué),次年任浙江省立圖書館編纂,參與《浙江圖書館館刊》和《文瀾學(xué)報(bào)》編輯事宜。
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文瀾閣《四庫(kù)全書》及浙江圖書館特藏書籍急需轉(zhuǎn)移。館長(zhǎng)陳訓(xùn)慈召集全館會(huì)議,商議庫(kù)書轉(zhuǎn)移路線與方案。夏定域急館長(zhǎng)之急,馬上趕往老家富陽(yáng)尋覓勘察藏書之地,后選定在漁山石馬頭村趙坤良家老屋。筆者在其小兒子夏錫元家里,見到一本長(zhǎng)方形的略顯古樸的發(fā)黃的筆記本,其中記載了1937年《四庫(kù)全書》從杭州遷移家鄉(xiāng)漁山的經(jīng)過(guò)。夏定域在日記(圖二)里寫道,七·七事變后,省圖書館館長(zhǎng)陳叔諒為轉(zhuǎn)移文瀾閣庫(kù)書著急,他作為圖書館的一員就為這事動(dòng)腦子,后來(lái)想到在東南日?qǐng)?bào)工作的鄉(xiāng)友趙坤良:“他家有余屋,不住人,不起煙火,距江岸10多里,系山里。在該處庫(kù)書移好后,即滬戰(zhàn)八一三開始,杭州速遭轟炸。”
漁山與夏定域老家里山相距不過(guò)三四里路,自庫(kù)書到達(dá)漁山石馬頭村密藏,夏定域與省圖書館毛春翔、葉守榮受命負(fù)保管之職。從8月5日抵達(dá)漁山至12月3日離開,在漁山停留120天期間,夏定域沒顧得上回家一趟。直到要隨庫(kù)書轉(zhuǎn)移那天,他方回家一次,向家人提出帶上長(zhǎng)子即11歲的夏錫楚。夏定域此舉是想給這次未知的長(zhǎng)途碾轉(zhuǎn)一個(gè)精神的寄托,也想給兒子一次歷練成長(zhǎng)的機(jī)會(huì)。
1937年12月3日,夏定域帶上長(zhǎng)子踏上了保護(hù)國(guó)寶文瀾閣《四庫(kù)全書》的征程。8年里,夏定域與家人斷了給養(yǎng)和通信。長(zhǎng)子夏錫楚,由于跟隨父親一路顛沛流離,正長(zhǎng)身體的他缺少應(yīng)有的營(yíng)養(yǎng),患上了骨傷病病變?yōu)楣前?7歲那年離開親人永遠(yuǎn)地去了。為此,夏定域受到家人深深的責(zé)備,他悲愴地流下內(nèi)疚的淚水,在日記中寫道:“原擬將楚兒托四弟從金華帶回家鄉(xiāng),但因交通問(wèn)題,才顧自己帶往后方,不愿竟鑄成大錯(cuò)也!”
趙坤良,字敬濂,富陽(yáng)漁山鄉(xiāng)五愛村石馬頭自然村人,家境富裕。畢業(yè)于國(guó)立上海商學(xué)院新聞學(xué)專修科專業(yè)。抗戰(zhàn)前服務(wù)教學(xué)界,歷任上海市立敬業(yè)中學(xué)教員、浙江省立杭州民眾教育館教導(dǎo)干事等職。抗戰(zhàn)后從政,歷任金華、富陽(yáng)等縣政府秘書,金華縣動(dòng)員委員會(huì)民眾動(dòng)員指導(dǎo)組副主任兼戰(zhàn)時(shí)服務(wù)團(tuán)主任等職。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先后在金華東南日?qǐng)?bào)、麗水東南日?qǐng)?bào)、杭州東南日?qǐng)?bào)工作。
夏定域?yàn)楦魂?yáng)里山人,趙坤良為富陽(yáng)漁山人,里山和漁山為鄰鄉(xiāng),加上夏定域、趙坤良都有一定文化背景,在外工作,二人既是老鄉(xiāng)又是朋友,相互間熟悉情況。夏定域遇上省圖書館重要館藏庫(kù)書急需轉(zhuǎn)移之大事,首先想到了鄉(xiāng)友趙坤良。經(jīng)聯(lián)系,趙坤良滿口答應(yīng)。筆者在《富春漁山趙氏家譜》(圖九)中,發(fā)現(xiàn)浙江圖書館館員葉守榮撰寫的題為《文瀾閣庫(kù)書戰(zhàn)時(shí)初遷漁山記》文章:“趙君坤良昆仲富有資產(chǎn),待人和善,號(hào)召力強(qiáng),一聲令出,數(shù)百挑夫立至,故搬運(yùn)書箱毫不費(fèi)力。趙君坤良合家居住新廈,其舊宅棄置未用,閣書即藏其中。余偕工友居樓下。樓下正屋一間原作廚房,供宅前店伙用,自閣書遷入,趙君即命拆灶。余與工友飲食由新廈供應(yīng),其照應(yīng)周到如此。至待余至厚,更非楮墨所能罄。”
張水木(圖五),富陽(yáng)市漁山鄉(xiāng)石馬頭村人,當(dāng)年親歷文瀾閣庫(kù)書轉(zhuǎn)移的搬運(yùn)者。2008年1月22日,筆者前往漁山鄉(xiāng)石馬頭村,采訪91歲高齡的張水木老先生。一提起搬運(yùn)文瀾閣庫(kù)書書箱的事,老人興奮地回憶道:“船上書箱有二百多箱,搬運(yùn)書箱的人很多,重的一箱二個(gè)人抬,輕的一人挑二箱。從漁山江碼頭到石馬頭村有10多里路,來(lái)回一趟需走二個(gè)多小時(shí),力氣大的一肩挑到村里,快的跑二趟,慢的跑了一趟,將船上運(yùn)來(lái)的書箱全部搬運(yùn)到趙坤良家老屋天已黑下來(lái)了,每人工錢是二毛五分錢,后因戰(zhàn)事吃緊,把要緊的幾箱庫(kù)書密藏到村口王家山上的墓穴里。”[5]
3 開發(fā)文瀾閣《四庫(kù)全書》抗戰(zhàn)苦旅線的意義
文瀾閣《四庫(kù)全書》抗日大轉(zhuǎn)移的成功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shí)教育意義。我們建議沿途擇點(diǎn)修葺曾經(jīng)庋藏過(guò)、密藏過(guò)《四庫(kù)全書》的老房子,擇點(diǎn)新造幾座標(biāo)志性建筑物,重建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2000公里抗戰(zhàn)苦旅線,以示紀(jì)念。
3.1 重建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2000公里抗戰(zhàn)苦旅線,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有效途徑
《四庫(kù)全書》是中國(guó)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和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共收書346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cè),可以稱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國(guó)之寶”。《四庫(kù)全書》共繕寫七部,北四閣中,文源閣本毀于1860年英法聯(lián)軍火焚,文淵閣本20世紀(jì)40年代移至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從承德移藏于北京圖書館,文溯閣于上世紀(jì)60年代從沈陽(yáng)故宮移藏甘肅省圖書館。南三閣中,文宗、文匯閣本太平天國(guó)戰(zhàn)爭(zhēng)期間被毀,文瀾閣本幾經(jīng)磨難才保存下來(lái)。抗戰(zhàn)爆發(fā),日本侵略者對(duì)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虎視眈眈,所以,對(duì)文瀾閣庫(kù)書抗日大轉(zhuǎn)移獲得成功,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加以宣傳,是對(duì)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敬重,是對(duì)中華文脈的傳承。
3.2 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2000公里抗戰(zhàn)苦旅線,是弘揚(yáng)中華民族精神的有效載體
1937年,中華民族處于十分危難的關(guān)頭,每一個(gè)炎黃子孫,中華兒女,都以滿腔熱血及憤怒,用自己的方式積極地投入抗戰(zhàn)。浙江圖書館職工在文瀾閣庫(kù)書面臨被毀、被掠奪的境況下,以館長(zhǎng)為首,每個(gè)人都竭盡全力投入到保護(hù)《四庫(kù)全書》的戰(zhàn)斗當(dāng)中,特別是毛春翔、葉守榮、夏定域等館員,歷經(jīng)千難萬(wàn)險(xiǎn),跋山涉水2000多公里,經(jīng)受了8年又11個(gè)月磨難,保護(hù)國(guó)寶文瀾閣《四庫(kù)全書》,這是一曲悲壯的史詩(shī)。
文瀾閣庫(kù)書抗戰(zhàn)苦旅處在特定的時(shí)代背景,發(fā)生在中華民族萬(wàn)分危難的時(shí)刻,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不僅僅是一代圖書館人無(wú)私的奉獻(xiàn)精神、敬業(yè)精神,而且已經(jīng)上升到愛國(guó)情懷,上升到民族精神。
3.3 杭州文瀾閣《四庫(kù)全書》2000公里抗戰(zhàn)苦旅線,是愛國(guó)主義教育難得的好教材
沿文瀾閣庫(kù)書轉(zhuǎn)移路線,選擇相關(guān)曾經(jīng)庋藏過(guò)、密藏過(guò)《四庫(kù)全書》的房子,民宅或祠堂廟宇(圖一、圖四、圖十二),加以修葺,并新建幾處標(biāo)志性建筑,如首站富陽(yáng)漁山——建德北鄉(xiāng)松陽(yáng)塢——龍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城隍廟——江西——湖南長(zhǎng)沙——貴州貴陽(yáng)張家祠堂——地母洞——四川重慶青木關(guān)等當(dāng)年文瀾閣《四庫(kù)全書》落過(guò)腳的地方。
沿途可以用講故事的形式,把當(dāng)年組織、參與《四庫(kù)全書》大轉(zhuǎn)移的圖書館人的事跡,以及沿途對(duì)文瀾閣《四庫(kù)全書》予以幫助的普通百姓及社會(huì)名士的事跡編寫成故事,用碑文的形式予以展示;并為《四庫(kù)全書》大轉(zhuǎn)移的有功之臣塑像、立碑,置于沿途。還可以組織圖書館人重走《四庫(kù)全書》西遷之路,也可以組織廣大青少年重走《四庫(kù)全書》的西遷之路,從而激發(fā)人們對(duì)中華民族文化的敬仰之情及愛國(guó)情懷。
[1]呂洪年.陳訓(xùn)慈與文瀾閣庫(kù)書的抗日大轉(zhuǎn)移[J].文瀾,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