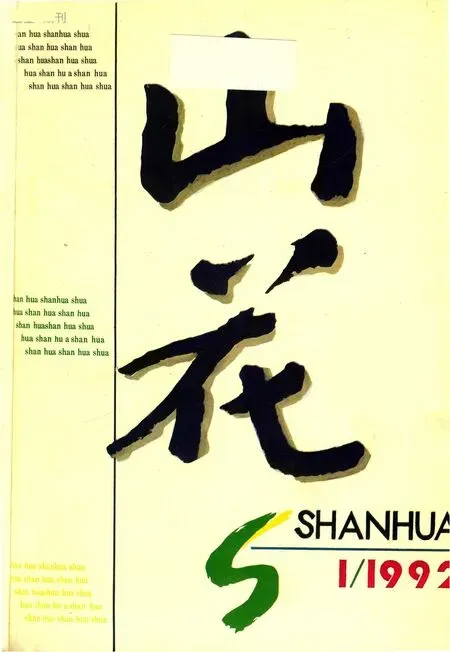赫塔·穆勒,或雙語(yǔ)百合(外一篇)
王家新
赫塔·穆勒,或雙語(yǔ)百合(外一篇)
王家新
赫塔·穆勒,或雙語(yǔ)百合
這座港口城 有冒著泡泡的 水肚子
有西瓜瓤做成的天空 有鄉(xiāng)間路
給側(cè)軌用 有一座信號(hào)塔 而沒(méi)有逆向軌
有滿滿一嘴的風(fēng)
有一駝背 玉米
……
這是我從赫塔·穆勒的詩(shī)集《托著摩卡杯的蒼白男人》中隨手摘錄的一節(jié)詩(shī)。僅僅是“西瓜瓤做成的天空”這一句,就足以讓我“傾倒”了,而接下來(lái)的詩(shī)句,恐怕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寫出來(lái)的,因?yàn)槟遣粌H是寫景,也是現(xiàn)代集權(quán)社會(huì)的隱喻,那是一個(gè)來(lái)自前東歐地區(qū)的詩(shī)人才會(huì)給我們帶來(lái)的“發(fā)現(xiàn)”。
我想,即使僅僅就詩(shī)而言,去年的這位諾獎(jiǎng)得主也是很獨(dú)到、很厲害的。許多作家都曾寫詩(shī),但她的《托著摩卡杯的蒼白男人》和《在頭發(fā)打的結(jié)中住著一位女士》(李雙志譯,江蘇人民出版社)這兩部詩(shī)集,卻并非一個(gè)小說(shuō)家的偶爾遣興,它們集中體現(xiàn)了一個(gè)詩(shī)人在詩(shī)藝上的探索及其不凡的特質(zhì)。人們說(shuō)英語(yǔ)中的納博科夫作為小說(shuō)家遠(yuǎn)遠(yuǎn)優(yōu)于他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這種不平衡則被講德語(yǔ)的赫塔·穆勒打破了。當(dāng)然,我猜她無(wú)意于與里爾克、策蘭這樣的偉大詩(shī)人比肩,但她卻寫出了別人都不能寫出的詩(shī)。“你帶手絹了嗎?”年少時(shí)每次出門她母親都要這樣問(wèn)她。帶了,她不僅一直悄悄地帶著,還用它玩起了詩(shī)歌的變戲法。她也只有以這種方式——以詩(shī)的想象力和語(yǔ)言的魔咒般的力量,才能給她的生活講出一個(gè)故事來(lái):
而那位國(guó)王 微微鞠了個(gè)躬
而那深夜 通常是步行來(lái)的
而從那家工廠的屋頂?shù)胶永?/p>
兩只鞋子發(fā)著亮光
顛倒了 而且這么早成了氖的蒼白
而其中一只 把我們的大嘴踩住
而另外一只 把我們的肋骨踩軟
在早上 消散了氖做成的那雙鞋
而那木蘋果興致勃勃 那楓樹紅了臉
那些天空里的星星 像爆米花一樣運(yùn)行
而那國(guó)王 鞠躬 然后殺人
這有點(diǎn)像卡夫卡的世界了,但又帶著幾分家族敘事或鄉(xiāng)村敘事的風(fēng)味,或者說(shuō),帶著幾分童話的色彩。的確,在一個(gè)繃緊了臉的世界里,講講童話有時(shí)還真管用,至少不會(huì)讓人發(fā)呆或發(fā)瘋。讓我嘆服的是她那精靈般的感受力(如果說(shuō)和她一樣來(lái)自羅馬尼亞、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的策蘭有一種幽靈般的感受力)。在她那里,一切都荒誕不經(jīng),而又充滿“無(wú)理之妙”,其詩(shī)思的運(yùn)作,還有那些隱喻、那些詞語(yǔ)的蹤跡,一切都顯得怪異而又詭秘,“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寫作就是在泄密與保密間走鋼絲”(《沉默讓我們令人不快,說(shuō)話使我們變得可笑》)。看來(lái)她真得感謝她所生活的羅馬尼亞了,讓她練就了這一身絕技。不過(guò),在她詩(shī)中那“無(wú)法表達(dá)的一半”,往往并不是政治性暗語(yǔ),而是詞語(yǔ)的存在本身,正是它們“在頭腦中引發(fā)迷失,打開詩(shī)意的震撼”。她當(dāng)然有著她的政治性,但她首先是一個(gè)詩(shī)人。她不會(huì)讓任何政治來(lái)傷害她的藝術(shù)。她寫一只被宰殺的珍珠雞,表達(dá)的也不是簡(jiǎn)單的廉價(jià)的同情,她仍是在寫“只有詩(shī)才能表現(xiàn)的東西”:
一只掛在絲線上的商店里的珍珠雞
有一個(gè)口袋型的脊梁骨
那翅膀沾了污點(diǎn) 那脖子也一樣
那軟骨部分的匆忙口哨吹綠成藍(lán)
快兩點(diǎn)的時(shí)候 那尸體腐爛成釉光
毫無(wú)疑問(wèn),赫塔·穆勒是德語(yǔ)作家、德語(yǔ)詩(shī)人。“在我們德國(guó)……”,那些花店或面包店的大媽總是愛對(duì)她這個(gè)來(lái)自羅馬尼亞的移民這樣說(shuō)話,“我不就是在你們的德國(guó)嗎……”,她差點(diǎn)要這樣反問(wèn)。不過(guò),又何必讓那些大媽們尷尬呢。她的這些詩(shī),就是一種讓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存在。很可能,這是德語(yǔ)詩(shī)歌中從未有過(guò)的物種。作為一個(gè)徹底的、毫不妥協(xié)的藝術(shù)家,她拒絕把生活詩(shī)意化(她的“人質(zhì)的黑眼眶”不允許她這樣);作為一個(gè)文學(xué)移民,她的詩(shī)給德語(yǔ)詩(shī)歌帶來(lái)了一種獨(dú)特的風(fēng)味和口音。作為一個(gè)作家,我們還可以說(shuō)她給慣于抒情的詩(shī)歌帶來(lái)了一種敘述的語(yǔ)調(diào)和細(xì)節(jié)的表現(xiàn)力,甚至還帶來(lái)了小說(shuō)的懸念,如“在這一年 或者一輛送貨車 人們應(yīng)該問(wèn)誰(shuí)/那個(gè)店主有一支單簧管/和一把刀在脖子上……/他是一個(gè)賊 一個(gè)獸醫(yī) 還是/音樂(lè)家 我們必須上車 事情才會(huì)/自見分曉”。不過(guò),與其說(shuō)這帶來(lái)了某種懸念,不如說(shuō)給詩(shī)歌帶來(lái)了一種“敘事”的可能性,帶來(lái)了對(duì)人性和存在的想象力。的確,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她和德語(yǔ)傳統(tǒng)意義上的“抒情詩(shī)人”已很不一樣了。她刷新了我們對(duì)詩(shī)和存在的認(rèn)知。她經(jīng)歷了那么多,恐怕早已變得“羞于抒情”了。她抒起情來(lái),也遠(yuǎn)遠(yuǎn)不同于那些文學(xué)青年:
我說(shuō)白天好
問(wèn) 嘿 發(fā)生了什么事兒%讓
其中一個(gè)鬢角同時(shí)從自己
和另一個(gè)那里
抽出了這些 白色的屋檐
請(qǐng)注意這里用的是“嘿”,而不是“啊”。也許就是這一個(gè)“嘿”,使她在當(dāng)今的德語(yǔ)詩(shī)歌世界里占據(jù)了一個(gè)微妙的、但也恰如其分的位置。

王承云作品·詩(shī)人 200×150cm 布面丙烯 2008
不過(guò),如果說(shuō)在詩(shī)歌中,赫塔·穆勒是一位變化莫測(cè)、愛做鬼臉的精靈,讀她的一些散文,我們的感覺就不一樣的。說(shuō)實(shí)話,她的這些隨筆和散文使我感到更親切,我也更切實(shí)地感受到其在場(chǎng),感受到她自身的獨(dú)特存在和思想的脈搏。“如果一個(gè)人,一個(gè)單個(gè)的人說(shuō)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么同這個(gè)人交往我會(huì)覺得困難。然而如果一個(gè)政客,一個(gè)德國(guó)的政客說(shuō)‘我們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則會(huì)感到一種悚然。”這是《一滴德國(guó)水,杯子便滿了》的開場(chǎng)白,僅憑這一句話,我想我們可以在一起“交流”了!
《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劉海寧譯),讓我受到異常的感動(dòng),“我從來(lái)沒(méi)有像在烏拉爾的五年流放那樣,那么經(jīng)常地夢(mèng)到吃飯,”那個(gè)曾被流放到蘇聯(lián)的羅馬尼亞德裔幸存者這樣說(shuō)。“我在夢(mèng)中吃得撐得要命,醒來(lái)時(shí)卻餓得發(fā)抖。”“知道嗎,熱騰騰的土豆直到今天對(duì)我來(lái)講一直都是最溫馨的菜,”“一顆土豆即便是在今天,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溫馨得如同一張溫暖的床,”他說(shuō),“如果我用手掰開一顆燒熟的沒(méi)有削皮的土豆,我的淚水會(huì)涌上來(lái)。不,那個(gè)時(shí)候不會(huì)涌眼淚……”
這樣的文字讀了真讓人發(fā)抖。這樣的作家是永遠(yuǎn)不會(huì)浮到生活的表面上來(lái)的。這樣的文字也不是用來(lái)“消閑”的,不,它是專門用來(lái)撕開我們的記憶的創(chuàng)傷的!
縱然如此,縱然穆勒有時(shí)會(huì)直接介入到一些政治問(wèn)題中,但她的這些散文和那些歷史文獻(xiàn)和時(shí)事評(píng)論卻有著性質(zhì)上的不同。它們發(fā)出的不僅是個(gè)人獨(dú)特的聲音,它們同時(shí)也是“延伸成散文的詩(shī)”。布羅茨基說(shuō)茨維塔耶娃寫散文,“是有意識(shí)地?cái)U(kuò)大她的孤立領(lǐng)地的范圍,即挖掘更多的語(yǔ)言潛力的努力”,說(shuō)在茨維塔耶娃那里,“詩(shī)歌的思維方式植入散文作品,詩(shī)歌延伸成散文”(布羅茨基《詩(shī)人與散文》,王希蘇譯)。穆勒的這些作品,也正如此。它們甚至比許多分行文字濃縮了更多的詩(shī)的精華。“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一般的散文作家會(huì)這樣說(shuō)話嗎?恐怕他們做夢(mèng)也不會(huì)。“‘我們可以自由活動(dòng)。’這是其中一個(gè)婦女的話。這話什么意思。拴在長(zhǎng)繩子上的自由。”這最后的一句是多么“酷”!它一下子打開了我們的存在之思。德國(guó)漢學(xué)家、詩(shī)人顧彬在我面前,就曾多次贊嘆穆勒的語(yǔ)言。不僅是語(yǔ)言,還有那種詩(shī)一般的結(jié)構(gòu)和寫法。如果說(shuō)一般的散文以其線性的陳述“牽著讀者的手”,穆勒的這些散文則是“連推帶拉”式的——它們充滿了詩(shī)的斷裂、跳躍和出乎不意的置換。如“旁邊桌子上的國(guó)家”,它本來(lái)是在維也納車站咖啡店里瞅見的“旁邊桌子上的那個(gè)男人”,隨著喇叭播報(bào)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車進(jìn)站,隨著記憶的襲來(lái)和一種痛苦的辨認(rèn),它最后竟變成這樣一副“詩(shī)的特寫”了。
的確,這不僅是一位無(wú)所畏懼地言說(shuō)著真實(shí)的作家,也是一位“以語(yǔ)言為對(duì)象和任務(wù)”的作家。在她的散文中如同在她的詩(shī)中,她挖掘著語(yǔ)言的潛力,也充滿了東歐式的“詞語(yǔ)游戲”。房間里掛著的那些照片,“您千萬(wàn)不要說(shuō)是馬克思,”“您千萬(wàn)不要說(shuō)是鐵托,”“這些都是我們斯洛文尼亞的民族詩(shī)人!”物質(zhì)匱乏,商店里沒(méi)有肉可賣,只有熏豬蹄作為替代品,但那卻不是豬蹄,而是蘇聯(lián)老大哥的“體操鞋”!如此等等,詞與物之間的固定關(guān)系脫節(jié)了,或者說(shuō)被瓦解了,一種可怕的美已經(jīng)誕生。

王承云作品·L先生 200×150cm 布面丙烯 2008
她的長(zhǎng)篇隨筆《每一句話語(yǔ)都坐著別的眼睛》,談的就是她在羅馬尼亞成為一個(gè)作家的語(yǔ)言經(jīng)歷,它使我深感親切,也給我?guī)?lái)了諸多啟示。德語(yǔ)為她的母語(yǔ),“它是不經(jīng)意間產(chǎn)生的一種天賦”,但是,“在遲來(lái)的異域語(yǔ)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語(yǔ)詞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閃現(xiàn)。”在學(xué)羅語(yǔ)的頭兩年,她也深感困難,羅語(yǔ)就像“口袋里的零錢”不夠用。然而隨著時(shí)間,“事物因?yàn)檫@全新的語(yǔ)言而生出不同的面貌……羅語(yǔ)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一個(gè)鳥的名字,同時(shí)也在描述燕子黑壓壓并排坐在鐵絲上的情景。在我還沒(méi)有接觸羅語(yǔ)的時(shí)候,每個(gè)夏天,我都會(huì)看到這樣的風(fēng)景。我慨嘆人們能如此美麗地稱呼燕子。”
這兩種語(yǔ)言的相遇,“成全”的是她自己對(duì)語(yǔ)言的敏感和驚異,還有她那神秘的聽力,“村里的方言德語(yǔ)說(shuō):風(fēng)在走;學(xué)校的標(biāo)準(zhǔn)德語(yǔ)說(shuō):風(fēng)在吹;羅語(yǔ)則說(shuō):風(fēng)在打,叫你立刻聽到運(yùn)動(dòng)的聲響……德語(yǔ)說(shuō):風(fēng)躺下了,是平坦的、水平的;羅語(yǔ)說(shuō):風(fēng)站住了,是直立的、垂直的。”就是以這樣的聽力,“忽然有一天,羅語(yǔ)就變成了我自己的語(yǔ)言。不同的是,當(dāng)我――我也不情愿這么做――不得不用德語(yǔ)詞匯和它們做比較時(shí),羅語(yǔ)詞會(huì)睜大了眼睛。它的紛雜具有一種感性、調(diào)皮、突如其來(lái)的美。”
當(dāng)然,穆勒一直是在用她的母語(yǔ)寫作,但是“每一句話語(yǔ)都坐著別的眼睛”,羅語(yǔ)早已內(nèi)在于她的思維了。讓我難忘的,是她對(duì)“百合”這個(gè)詞的談?wù)摗0俸显诹_語(yǔ)中是陽(yáng)性,在德語(yǔ)中為陰性,“人們?cè)诘抡Z(yǔ)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在羅語(yǔ)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擁有兩種視角的人,二者在頭腦中交織在一起,它們分別敞開自己,一個(gè)男人和一個(gè)女人蕩著秋千,蕩進(jìn)對(duì)方的身體去。……百合在兩種同時(shí)奔跑的語(yǔ)言中變成了什么?一個(gè)男人臉上的女人鼻子?一個(gè)長(zhǎng)長(zhǎng)的淡綠的上腭?……它散發(fā)來(lái)和去的氣味,還是讓我們嗅出超越時(shí)間之上的停留?……雙體百合在大腦中無(wú)法停歇,不斷講述著有關(guān)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
這種獨(dú)特的語(yǔ)言經(jīng)歷,暗含著一個(gè)作家成長(zhǎng)的秘密,暗含著赫塔·穆勒之所以成為“赫塔·穆勒”的秘密,也暗含著我們今天這個(gè)時(shí)代的某種文學(xué)趨勢(shì)。的確,這是一朵奇異的“雙語(yǔ)百合”。只不過(guò)它不是語(yǔ)言學(xué)的溫室里的產(chǎn)物:它扎根于歷史的痛苦的土壤。它以“赫塔·穆勒”的方式綻放著。
寫到這里,我就不禁再次想起這位女作家在《空中醞釀的往往不是好東西》的結(jié)尾處所描述的她告別羅馬尼亞的情景。那是她命運(yùn)的轉(zhuǎn)折點(diǎn),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那也是永不消逝的過(guò)去:一個(gè)小小的邊境火車站,“登上列車前的最后一次威脅是:不論走到哪兒,我們都找得到你,然后我像一件無(wú)人大衣坐在了火車上,感覺又一次走進(jìn)他們布置好的圈套。火車嗚嗚叫著。那是二月,夜幕早早落下的傍晚。雪花順著鐵軌悄悄地將白光向前推進(jìn)。火車的確是火車,我們的確坐在火車上,但我還是不能完全相信……”

王承云作品·不離不棄 200×150cm 布面丙烯 2009
“列車駛?cè)胄傺览hF路兩旁是匈牙利的越冬草,是匈牙利的雪花,和匈牙利的街燈。天亮以后,是奧地利的天空,奧地利的雞鳴,奧地利的籬笆和楊樹。和列車一起行進(jìn)的周圍的一切,似乎還沒(méi)有進(jìn)入自由之地……邊境使人們違逆風(fēng)景,違逆頭腦和自然理性。但首先,有它就很好,否則我無(wú)法在延續(xù)的風(fēng)景中到達(dá)另一個(gè)國(guó)度……已然是奧地利的楊樹掠過(guò)我的雙眼,用它的小提琴為我大腦的第一站自由演奏一曲風(fēng)之歌:無(wú)論走到哪里,我們都找得到你。”
就這樣,那久久壓抑的、足以把一個(gè)人擊垮的音樂(lè)終于響起來(lái)了。讓它也一次次為我們演奏吧。的確,赫塔·穆勒女士,無(wú)論你走到哪里,無(wú)論你住在“頭發(fā)打的結(jié)中”還是在“雙語(yǔ)百合”里,我們都找得到你,我們也愿意去找你!
策蘭與海德格爾的對(duì)話之路
在策蘭研究中,策蘭與海德格爾的關(guān)系一直是一個(gè)熱點(diǎn)。他們一個(gè)是里爾克之后最有影響的德語(yǔ)詩(shī)人,一個(gè)是舉世公認(rèn)的哲學(xué)大師;一個(gè)是父母雙親慘死于集中營(yíng)的猶太幸存者,一個(gè)則是曾對(duì)納粹政權(quán)效忠并在戰(zhàn)后一直保持沉默的“老頑固”。因此他們的關(guān)系不僅涉及到“詩(shī)與思”的對(duì)話,還緊緊抓住了戰(zhàn)后西方思想界、文學(xué)界所關(guān)注的很多問(wèn)題。的確,只要把“策蘭”與“海德格爾”這兩個(gè)名字聯(lián)系起來(lái),就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

王承云作品·輪回 600×200cm 布面丙烯 2010

王承云作品·水患 200×600cm 布面丙烯 2009
詹姆斯·k·林恩是對(duì)的,和其他的研究相比,他的這本《策蘭與海德格爾:一場(chǎng)懸而未決的對(duì)話》(李春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把研究的焦點(diǎn)和“故事”的重心放在了策蘭身上,并且他看到:策蘭之所以受到海氏的影響和吸引,完全是有自身根源的,“在策蘭逐漸成長(zhǎng)為一名詩(shī)人的過(guò)程中,在沒(méi)有閱讀海德格爾的情況下,他已經(jīng)是一個(gè)正在成長(zhǎng)的海德格爾了。”在1948年為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畫家熱內(nèi)所寫的《埃德加·熱內(nèi)與夢(mèng)中之夢(mèng)》中,策蘭就這樣宣稱:“我想我應(yīng)該講講我從深海里聽到的一些詞,”這還是策蘭第一次發(fā)表他的藝術(shù)觀,“我越來(lái)越清楚,人類不僅僅在外在生命的鏈條上受苦,而且也被堵上嘴巴以致不可以說(shuō)話……那些自從遠(yuǎn)古時(shí)代就在內(nèi)心深處竭力爭(zhēng)取表達(dá)的東西,也伴隨著被燒盡的感覺的灰燼,而且不止這些!”
策蘭所面對(duì)的,也正是海德格爾哲學(xué)一開始就面臨的任務(wù):變革和刷新語(yǔ)言,由此革新對(duì)存在的思考。這就是為什么他會(huì)把目光投向荷爾德林、里爾克、特拉克爾等詩(shī)人,“詩(shī)歌是源始的語(yǔ)言,即處于發(fā)生狀態(tài)的語(yǔ)言”。他要回到這種“源始語(yǔ)言”中,也即從傳統(tǒng)哲學(xué)中擺脫,回到存在的未言狀況。
可以說(shuō),這就是這場(chǎng)相遇或?qū)υ挼淖畛醯慕粎R點(diǎn)。只不過(guò)策蘭所說(shuō)的“灰燼”,不僅是現(xiàn)代詩(shī)歌表達(dá)困境的一個(gè)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奧斯維辛所留下的“灰燼”。他一生的寫作,就是要接近這個(gè)“灰燼的中心”。而這,不用說(shuō),正是海德格爾所一直回避的。
顯然,在最初,策蘭在維也納時(shí)期的戀人、當(dāng)時(shí)正在撰寫“批判地吸收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博士論文的奧地利女詩(shī)人巴赫曼,對(duì)于策蘭更多地了解海德格爾起了促進(jìn)作用。“我們交換著黑暗的詞”,這是策蘭寫給巴赫曼的《花冠》中的一句詩(shī)。他們是否也交換過(guò)對(duì)海氏哲學(xué)的看法?我想是的。在策蘭后來(lái)寫給巴赫曼的一些詩(shī)中,就有一些來(lái)自海德格爾的隱喻,如《白與輕》中的“風(fēng)影”,《日復(fù)一日》中的“一個(gè)明日/跳入昨日”——它幾乎馬上使人想到海德格爾的“死亡的先行性”!
回到林恩的研究,他不僅根據(jù)策蘭的生平資料和作品,也根據(jù)策蘭在他讀過(guò)的20多種海氏的著作如《存在與時(shí)間》、《林中路》、《何謂思想》中留下的各種標(biāo)記,來(lái)研究策蘭對(duì)海德格爾的吸收和思想對(duì)話。海德格爾如此吸引了策蘭,一是他的“存在主義”哲學(xué),一是他對(duì)荷爾德林、里爾克等詩(shī)人的闡釋、他由此所提出的“詩(shī)人何為”等重要命題、他從哲學(xué)層面所揭示的在、思、言、詩(shī)的關(guān)系,等等;另外,在海氏的全部思考活動(dòng)中所貫穿的“詩(shī)性”敏感、獨(dú)特的哲學(xué)隱喻及其語(yǔ)言表述方式,也深深吸引了策蘭。以下摘出一些策蘭在閱讀海氏過(guò)程中劃出、標(biāo)記的句子:
“此在在本質(zhì)上就是與他者共在。”
“任誰(shuí)也不能從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如果人類想要再次接近存在,他就需要首先學(xué)會(huì)存在于一種無(wú)名的狀態(tài)中。……在說(shuō)話之前,他必須允許自己被存在言說(shuō)……”
“不是我們?cè)诤驮~語(yǔ)游戲,而是語(yǔ)言的本質(zhì)在和我們游戲。”
“詩(shī)人并沒(méi)有發(fā)明這首詩(shī)特有的東西。它是被賜予的。他服從并跟隨著這種召喚。”
“今天我們說(shuō):存在把它自身獻(xiàn)給了我們,但是,如此一來(lái),同時(shí),他在本質(zhì)上又退卻了。”
如此等等,或是直接激發(fā)了策蘭創(chuàng)作的靈感,或是引發(fā)了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說(shuō),他不得不讓海德格爾來(lái)到他的頭腦中思考。總之,海德格爾的影響已漸漸滲透在策蘭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活動(dòng)中,1958年在接受不萊梅文學(xué)獎(jiǎng)的獲獎(jiǎng)致辭中他一開始就講:“思考(Denken)和感謝(Danken)在我們的語(yǔ)言里同出一源,并合二為一。只要溯源而上,就有以下詞語(yǔ)含有以上兩詞的意義:‘想念’,‘掛念’,‘紀(jì)念’,‘虔誠(chéng)’等等。請(qǐng)?jiān)试S我因此感謝你們”。這顯然就是一種對(duì)海德格爾之思的反響。另外,策蘭在這里說(shuō)的“我們的語(yǔ)言”,也顯然不是他所屬的東歐猶太人所講的混雜語(yǔ)言,而是由海德格爾所確立的荷爾德林——里爾克這一路“正宗”的德國(guó)詩(shī)性語(yǔ)言。他顯然很希望他能加入到這一詩(shī)性傳統(tǒng)中來(lái)。
即使在同友人談他從事的詩(shī)歌翻譯時(shí),他也這樣說(shuō):“這是一種練習(xí)。它們都是練習(xí)。如果我可以借用海德格爾的話來(lái)說(shuō),那就是等待語(yǔ)言向我說(shuō)話。”
總之,海德格爾的音調(diào),在策蘭的作品中處處發(fā)出回響。海德格爾的影響,對(duì)策蘭由早期的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抒情詩(shī),轉(zhuǎn)向一種德國(guó)式的“存在之詩(shī)”,起了重要、深刻的作用。
但是,策蘭對(duì)海德格爾并不是盲目、無(wú)條件接受的。他堅(jiān)持從自己的根基出發(fā)。比如說(shuō),在1958年對(duì)巴黎福林科爾書店的回答時(shí)他這樣談到寫作:“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詩(shī)意’;它命名,它確認(rèn),它試圖測(cè)度被給予的和可能的領(lǐng)域。真實(shí),這永遠(yuǎn)不會(huì)是語(yǔ)言自身運(yùn)作達(dá)成的,這總是由一個(gè)從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發(fā)的‘我’來(lái)形成其輪廓和走向。現(xiàn)實(shí)并不是簡(jiǎn)單地在那里,它需要被尋求和贏回。”可以說(shuō),這至少是對(duì)海德格爾的“語(yǔ)言是說(shuō)話者”的一種必要的補(bǔ)充或修正。
海德格爾與納粹的歷史關(guān)系顯然是策蘭的一個(gè)無(wú)法克服的障礙。只不過(guò),策蘭并沒(méi)有因此而盲目否定或輕視海氏的哲學(xué)思想。策蘭的朋友、哲學(xué)家奧托·珀格勒回憶說(shuō),策蘭曾在他面前為海德格爾的后期哲學(xué)辯護(hù)。就策蘭的讀書標(biāo)記來(lái)看,除了對(duì)海德格爾的詩(shī)學(xué),他對(duì)海氏對(duì)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批判也很認(rèn)同。海氏很早就對(duì)日益擴(kuò)張的現(xiàn)代技術(shù)和工業(yè)文明提出了質(zhì)疑。耐人尋思的是,這位對(duì)歷史一直保持沉默的人,1949年在一次講演中還把工業(yè)化了的食品生產(chǎn)同集中營(yíng)聯(lián)系在了一起,“本質(zhì)上同尸體和毒氣室的生產(chǎn)一樣”。他的一句廣被引用、耐人尋思的名言是:“技術(shù)的白晝是世界的黑夜。”的確,正如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在《海德格爾傳》(靳希平譯)中所說(shuō)“海德格爾關(guān)于技術(shù)的思想觸及到時(shí)代的恐懼”。他還認(rèn)為海氏對(duì)“技術(shù)統(tǒng)治”的分析伴隨著對(duì)“趨向于權(quán)力意志”的歷史的反思,“或公開或隱含地包含了對(duì)‘奧斯維辛’的批判。”
雖然這種看法不免會(huì)引起爭(zhēng)議,但很多人包括策蘭的確對(duì)海氏抱有這樣的期望。
林恩的這部專著于2006年首次出版,雖然他聲稱要根據(jù)已掌握的全部文獻(xiàn)資料,就策蘭與海氏的關(guān)系“給出一個(gè)前所未有的更完整的故事版本”。但現(xiàn)在看來(lái),它并不那么“完整”。2008年德國(guó)出版界的一個(gè)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蘭書信集《心的歲月》的出版。這部書信集共收入策蘭和巴赫曼自1948年至1967年間的196封書信,它本來(lái)要到2023年才可以問(wèn)世,蘇爾坎普出版社征得雙方親屬的許可,提前十五年出版了。這些書信意義重要,它們不僅是兩個(gè)心靈之間的傾訴和對(duì)話,也是與政治歷史有廣泛關(guān)聯(lián)的個(gè)人檔案,其中就記載著策蘭拒絕給海德格爾生日慶祝專輯寫詩(shī)這一重要事件。
1959年8月5日,巴赫曼寫信給策蘭詢問(wèn)關(guān)于海德格爾生日慶祝專輯的事, 表示她對(duì)海氏在政治上所犯的錯(cuò)誤的看法不會(huì)改變,但她愿意給慶祝專輯寫點(diǎn)東西,但策蘭還是拒絕了。拒絕的原因倒不主要是因?yàn)楹5赂駹柋救耍且驗(yàn)椴邉澱邇?nèi)斯克,“在一年前,我就告訴內(nèi)斯克,他要先告訴我專輯里有些別的什么作者,再?zèng)Q定是否寫文章。然而,他沒(méi)有那樣做,相反,我的名字卻出現(xiàn)在名單上”。另外,策蘭對(duì)專輯中出現(xiàn)的一些“專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實(shí)則“并不干凈”的名流(如信中提到的著名作家伯爾)也很不屑,“你知道,我絕對(duì)是最后一個(gè)可以對(duì)他(指海氏)的弗萊堡大學(xué)校長(zhǎng)就職演說(shuō)及別的行為忽略不計(jì)的人;但是,我也對(duì)自己說(shuō)……那些被自己所犯錯(cuò)誤卡住、卻不掩飾自己的污點(diǎn),也不表現(xiàn)得好像自己從來(lái)都沒(méi)有過(guò)錯(cuò)的人,實(shí)在比那些當(dāng)初就具有好名聲(實(shí)際上,我有理由質(zhì)問(wèn),所謂好名聲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并在這上面建立起最舒服最有利地位的人要更好。”在再次致巴赫曼的回信中他又強(qiáng)調(diào):“我是不能與這些人為伍的。我只是說(shuō)過(guò),我希望他,內(nèi)斯克,如果他在海德格爾75歲壽辰時(shí)再出類似的集子,就應(yīng)該及時(shí)告知我……”,信的最后,策蘭還這樣對(duì)巴赫曼講:“我也同樣,上帝知道,不是個(gè)‘存在的牧人’”。
這個(gè)引語(yǔ)出自海德格爾的《關(guān)于人文主義的通信》,其中有“人類是存在的牧人”這樣的話。這說(shuō)明,縱然策蘭在態(tài)度上絕決,在內(nèi)心里也很苦澀,但他在思想上卻無(wú)法擺脫與海德格爾的關(guān)聯(lián)。
依然不改的,是策蘭對(duì)海德格爾一貫的尊重。正是在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他依然希望海氏能讀到他的詩(shī),珀格勒回憶說(shuō)策蘭在那時(shí)想把他的一首詩(shī)《條紋》贈(zèng)寄給海德格爾,詩(shī)中有這樣的耐人尋味的詩(shī)句:“眼中的紋影/它珍藏著/一個(gè)由黑暗孕育的記號(hào)”。
海德格爾是否讀到了或讀懂了這個(gè)“由黑暗孕育的記號(hào)”,不得而知,但策蘭后來(lái)的確送給了他另一首詩(shī)。1961年,策蘭通過(guò)珀格勒向海氏寄贈(zèng)詩(shī)集《語(yǔ)言柵欄》,在題獻(xiàn)上寫下“這些是一個(gè)尊敬您的人的詩(shī)”,并附上了這首只有四行的短詩(shī):
蕁麻路上傳來(lái)的聲音:
從你的手上走近我們,
無(wú)論誰(shuí)獨(dú)自和燈守在一起,
只有從手上閱讀。
這四行詩(shī)出自策蘭的組詩(shī)《聲音》。有人解讀說(shuō)“蕁麻路”暗示著基督受難的“荊棘路”,但這太明確。我想它也許出自詩(shī)人早年?yáng)|歐生活的經(jīng)驗(yàn)(策蘭的早期詩(shī)《眼睛》中就有這樣一句:“我采摘著蕁麻/并鏟去諺語(yǔ)的陰影”),總之,這是一個(gè)荒涼的、多刺的、但又讓人深感親切的意象,隱隱約約的摸索著的“聲音”就從那里傳來(lái)。引人注目的,是接下來(lái)出現(xiàn)的“手”的形象。我想,這既是對(duì)海德格爾的“思想是一件手藝活”的反響,也體現(xiàn)了策蘭對(duì)人的存在、對(duì)交流的獨(dú)特體驗(yàn)和期待。在1960年間給漢斯·本德爾的信中他這樣說(shuō):“技藝意味著手工,是一件手的勞作。這些手必須屬于一個(gè)具體的人,等等。一個(gè)獨(dú)特的、人的靈魂以它的聲音和沉默摸索著它的路。只有真實(shí)的手才寫真實(shí)的詩(shī)。在握手與一首詩(shī)之間,我看不出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在握手與一首詩(shī)之間,我看不出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說(shuō)得多好!法國(guó)著名猶太裔哲學(xué)家列維納斯在《保羅·策蘭:從存在到他者》一開始就引用了這句話,說(shuō)這樣的“握手”是一次“給予”,真正的“相遇”就在這一刻發(fā)生。
無(wú)論對(duì)這樣的詩(shī)怎樣闡釋,策蘭期待著與海德格爾有一次真實(shí)的“握手”,這是可以肯定的。
這樣的時(shí)刻終于到來(lái),并被銘刻進(jìn)了歷史,它甚至被很多人稱為“一場(chǎng)劃時(shí)代的相遇”,這就是1967年7月25日策蘭與海德格爾在弗萊堡托特瑙山上的會(huì)面。該年7月24日,策蘭應(yīng)鮑曼教授邀請(qǐng)赴弗萊堡大學(xué)朗誦。在這之前,鮑曼給海德格爾寄上書面邀請(qǐng),海德格爾隨即熱情回信:“我很久以來(lái)就想結(jié)識(shí)策蘭。他遠(yuǎn)遠(yuǎn)站在最前面,卻常常回避與人交往。我了解他的所有作品,也了解他自己從中擺脫出來(lái)的艱難的危機(jī)。”海氏不僅欣然接受邀請(qǐng),在策蘭到來(lái)之前,他甚至到弗萊堡書店走了一趟,請(qǐng)他們把策蘭詩(shī)集擺在書店櫥窗最醒目的位置。這使我們不禁想起了他那句著名的話:“我們這些人必須學(xué)會(huì)傾聽詩(shī)人的言說(shuō)。”
弗萊堡大學(xué)的朗誦會(huì)上,聽眾如云,而德國(guó)的“哲學(xué)泰斗”就坐在最前排認(rèn)真地聆聽。在策蘭精心選擇朗誦的詩(shī)中,有一首《剝蝕》,該詩(shī)的最后是:
等待,一陣呼吸的結(jié)晶
你的不可取消的
見證。
“見證”,這真是一個(gè)對(duì)戰(zhàn)后的德國(guó)人、尤其是對(duì)海德格爾來(lái)說(shuō)具有刺激性的詞。他們的這次相遇,仍處在歷史的陰影里。朗誦會(huì)后,有人提議合影,策蘭不愿意。但海德格爾仍熱情地邀請(qǐng)策蘭第二天訪問(wèn)他在弗萊堡附近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策蘭本來(lái)不愿意去,他對(duì)鮑曼說(shuō)和一個(gè)很難忘記該人過(guò)去的歷史的人在一起感覺很困難,但他還是去了。他們?cè)谏缴闲∧疚菡劻艘簧衔纭K麄冊(cè)谝黄鹁烤拐劻诵┦裁矗两袢詿o(wú)人得知。人們只是看到,這次會(huì)見竟使一向憂郁沉重的策蘭精神振作了起來(lái)。
在小木屋的留言薄上,策蘭寫下了“在小木屋留言薄上,望著井星,心里帶著對(duì)走來(lái)之語(yǔ)的希望”。回巴黎后,又寫下了一首題為《托特瑙山》的詩(shī),并特意請(qǐng)印刷廠制作了一份收藏專用版本,寄贈(zèng)給了海德格爾本人。下面即是這首著名的詩(shī):
金車草,小米葉,

王承云作品·十月頌歌 200×450cm 布面丙烯 2009
從井中汲來(lái)的泉水
覆蓋著星粒。
在
小木屋里,
題贈(zèng)簿里
——誰(shuí)的名字留在
我的前面?——,
那字行撰寫在
簿里,帶著
希望,今天,
一個(gè)思者的
走來(lái)
之語(yǔ)
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紅門蘭與紅門蘭,零星,
生疏之物,后來(lái),在途中,
變得清楚,
那個(gè)接送我們的人,
也在傾聽,
這走到半途的圓木小徑
在高沼地里,
非常
潮濕。
這是一首“即興寫生”或“抒情速記”式的詩(shī),卻引起了廣泛的關(guān)注和眾多不同的解讀。
我本人曾訪問(wèn)過(guò)海氏小木屋,它處在托特瑙山上一個(gè)雄渾、陡峭的開闊斜坡的上端,幾乎就要和黑森林融為一體。海氏夫婦于1922年建造了此屋,他的許多著作都寫于此地,后來(lái)在弗萊堡任教期間,他經(jīng)常懷著“還鄉(xiāng)”的喜悅重返山上小屋。也許正是在此地,“海德格爾使哲學(xué)又重新贏得了思維”(漢娜·阿倫特語(yǔ))。因此我們不難想象這次造訪給策蘭帶來(lái)的喜悅。
“金車草,小米葉”,詩(shī)一開始就出現(xiàn)了這兩種花草。策蘭對(duì)地質(zhì)學(xué)、礦物學(xué)、植物學(xué)等等一直很關(guān)注,并很擅長(zhǎng)把它們轉(zhuǎn)化為詩(shī)歌的資源,海氏后來(lái)就曾經(jīng)告訴伽達(dá)默爾,就在黑森林中,策蘭所知道的植物和動(dòng)物比他還要多。但是用在這里的“金車草,小米葉”,不僅出自當(dāng)?shù)鼐拔铮€有著更豐富的聯(lián)想和隱喻意義。首先,這兩種草木都有療治瘀傷和止痛的效用。金車草的淺黃色,還會(huì)使人想到納粹時(shí)期強(qiáng)迫猶太人佩帶的黃色星星。小米葉,據(jù)林恩的考察,在策蘭早年寫于勞動(dòng)營(yíng)期間的詩(shī)中也曾出現(xiàn)過(guò):“睫毛和眼瞼丟失了小米草”。而現(xiàn)在,這種帶有安慰意味的花草又出現(xiàn)了!

王承云作品·軟中華 200×150cm 布面丙烯 2010
同樣,“從井中汲來(lái)的泉水/覆蓋著星粒”,也暗含著某種重返存在的“源始性”的喜悅。在小木屋左側(cè),有海氏夫婦親自開鑿的井泉,引水木槽上雕刻有星星。很可能,策蘭像其他的來(lái)訪者一樣,暢飲過(guò)這久違的甘甜、清澈的泉水。
“題贈(zèng)簿里/——誰(shuí)的名字留在/我的前面?”這一句也很耐人尋味。策蘭深知海氏的重要位置,他是思想史的一個(gè)坐標(biāo),也是連接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重要一環(huán)。他也許知道他的朋友、法國(guó)著名詩(shī)人勒內(nèi)·夏爾在他之前曾來(lái)訪問(wèn)過(guò),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前納粹分子來(lái)這里拜謁過(guò)他們的大師呢?
但無(wú)論如何,仍有“希望”存在。“走來(lái)之語(yǔ)”,讓人想到海氏《在通向語(yǔ)言的途中》中談到的“走來(lái)的神”,還有他的著名短句“不是我們走向思,思走向我們”。值得一提的是,在1967年曾寄給海氏本人的第一稿上,“一個(gè)思者的/走來(lái)之語(yǔ)”后面還有“(莫延遲之)”這句補(bǔ)充語(yǔ),在后來(lái)收入詩(shī)集《雪部》時(shí),這句補(bǔ)充語(yǔ)刪掉了。那么,策蘭對(duì)他面對(duì)的“思者”有何期望?什么可能是他期待的“走來(lái)之語(yǔ)”?法國(guó)著名哲學(xué)家拉巴爾特在他論策蘭的講稿集《作為經(jīng)驗(yàn)的詩(shī)》中猜測(cè)是“請(qǐng)?jiān)彙保谙乱恢v中很快修正了這一點(diǎn),“我這樣想是不對(duì)的……認(rèn)為請(qǐng)求原諒就足夠了是不對(duì)的。那是絕對(duì)不可原諒的。那才是他(海氏)應(yīng)該(對(duì)策蘭)說(shuō)的。”
當(dāng)然,也有另外的解讀。在2001年9月4日在北京大學(xué)所作的論寬恕的演講中,德里達(dá)針對(duì)波蘭裔法國(guó)哲學(xué)家楊凱列維奇提出的“不可寬恕論”(“寬恕在死亡集中營(yíng)中已經(jīng)死亡”),主張一種絕對(duì)的無(wú)條件的寬恕。在這次演講中,德里達(dá)就引證了策蘭這首詩(shī),認(rèn)為這首詩(shī)是一種“贈(zèng)予”,同時(shí)它也是一種“寬恕”(見《德里達(dá)中國(guó)演講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這些不同的解讀各有側(cè)重,也各有道理,但都不是定論,接下來(lái)我們讀到的是:“森林草地,不平整,/紅門蘭與紅門蘭,零星”。這即是寫景,但也暗示著心情。策蘭寫這首詩(shī)時(shí)的心情,正如那起伏的“不平整”的森林草地。
至于“那個(gè)接送我們的人”,林恩把他解讀為接送策蘭去托特瑙山的司機(jī),的確,他參與了、見證了這次歷史性的會(huì)見。但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海德格爾本人呢?他邀請(qǐng)?jiān)娙藖?lái)訪并陪同他漫游草地、森林、峰頂,在隱喻的意義上,他也正是那個(gè)在存在的領(lǐng)域“接送我們的人”。而他“也在傾聽”。“傾聽”用在這里,一下子打開了一個(gè)更開闊的空間。它首先使我們想到的是沉默。因?yàn)闆](méi)有沉默,就沒(méi)有傾聽。海氏本來(lái)一直關(guān)注聲音與寂靜、存在與命名、言說(shuō)與沉默的關(guān)系,他的哲學(xu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沉默的傾聽。我想,這是海氏哲學(xué)中最為策蘭認(rèn)同的一點(diǎn)。這樣一位思者,在會(huì)見策蘭時(shí),他可能和策蘭一樣,變得更為沉默了(這正如他在后來(lái)寫給策蘭的信中所說(shuō)“從那時(shí)起,我們交換了許許多多的沉默”)。正是這沉默,相互交換的沉默,造成了他們的傾聽。

王承云作品·信仰 200×300cm 布面丙烯 2010
至于詩(shī)最后的“這走到半途的/圓木小徑/在高沼地里,/非常/潮濕”,把這首詩(shī)推向了一個(gè)更耐人尋思的境地。“圓木小徑”,可能有意取自海氏一本小冊(cè)子的名字,“走到半途”,也讓人聯(lián)想到海氏的“在通向語(yǔ)言的途中”。而這“走到半途的/圓木小徑”,通常被理解為是通向?qū)υ捴泛秃徒庵罚胺浅?潮濕”!詩(shī)的暗示性在這里達(dá)到最充分的程度。它暗示著對(duì)猶太人大屠殺之后民族和解的艱難(實(shí)際上,策蘭本人對(duì)德意志/猶太“共存”甚或“重歸言好”的可能性愈來(lái)愈不抱希望),暗示著創(chuàng)傷的難以彌合。不過(guò),從普遍的意義上,它也暗示著人生的艱難、思想的艱難以及通向語(yǔ)言之途的艱難。
就在這次歷史性會(huì)見之后,他們?nèi)杂幸娒婧屯ㄐ磐鶃?lái)。在收到策蘭贈(zèng)寄的《托特瑙山》的收藏版后,海氏給策蘭回了一封充滿感謝的信,信的最后甚至這樣說(shuō)“在適當(dāng)?shù)臅r(shí)候,您將會(huì)聽到,在語(yǔ)言中,也會(huì)有某種東西到來(lái),就像詩(shī)歌對(duì)您說(shuō)話一樣”。在1970年春,海氏甚至想帶策蘭訪問(wèn)荷爾德林故鄉(xiāng),為此還做了準(zhǔn)備,但他等來(lái)的消息卻是策蘭的自殺身亡。
這就是這個(gè)“故事”的悲劇性結(jié)局。著名作家?guī)烨性陉P(guān)于策蘭的文章《在喪失之中》中這樣說(shuō):“對(duì)拉庫(kù)—拉巴爾特來(lái)說(shuō),策蘭的詩(shī)‘全部是與海德格爾思想的對(duì)話’。這種對(duì)策蘭的看法,在歐洲占主導(dǎo)地位……但是,還存在另一個(gè)流派,費(fèi)爾斯蒂納(美國(guó)學(xué)者,策蘭傳的作者)明顯屬于該流派,該流派將策蘭作為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猶太詩(shī)人來(lái)閱讀……”“在法國(guó),策蘭被解讀為一個(gè)海德格爾式的詩(shī)人,這就是說(shuō),似乎他在自殺中達(dá)到頂點(diǎn)的詩(shī)歌生涯,體現(xiàn)了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藝術(shù)的終結(jié),與被海德格爾所斷定的哲學(xué)的終結(jié)可以相提并論。”
“故事”結(jié)束了嗎?結(jié)束了,我們聽到的不過(guò)是回聲——而那卻是永無(wú)終結(jié)的回聲。

王承云作品·2009101 200×450cm 布面丙烯 2010
[注:文中策蘭的詩(shī)論、詩(shī)、通信和一些研究資料,大都為筆者自己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