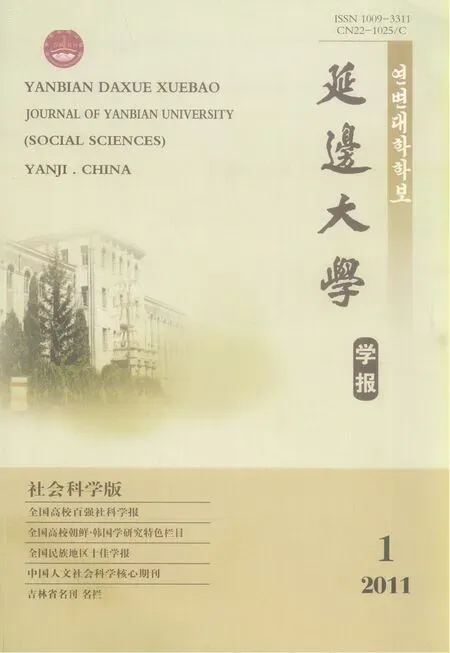毛澤東與儒家思想
邢 梅 玲
(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吉林延吉133002)
自漢武帝推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真正成為了維護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統治和禁錮人們思想行動的最強且最有效的工具。這也就決定了始創于孔子的儒家思想,歷經兩千多年的傳承,不斷被一代又一代諸子名儒所重視、充實、發展、細化,繼而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價值觀。
1893年毛澤東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時值清朝末年。那是一個將儒家思想尊為正統的封建時代,人們的言行舉止皆被嚴格限定于由儒家思想為中心所構建出的條條框框之中,“不逾矩”為世人稱頌。可以說,毛澤東是中國最后一代受過傳統儒家思想系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從《三字經》到“四書五經”,他的成長自然沉浸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和價值觀的熏陶之中。
這樣的成長軌跡,按理毛澤東應該成為一個當時最常見的迂腐秀才,但從他的生命歷程來看,毛澤東卻選擇了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并在晚年發起了對孔子及儒家思想強烈否定的思想運動。從尊儒到貶儒,這樣的轉變緣何而來?對儒家思想是單純的繼承還是批判的繼承?其個中原因值得我們去發掘和探討。
一、少年時期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機械式尊崇信服”
如前所言,毛澤東生在一個將儒家思想尊為正統的封建時代,少年時期接受的是那個時代最為傳統的私塾教育。雖然在當時清朝統治機構內部出現了一系列圍繞守舊與維新之爭的大辯論,但是由于地處偏遠農村地區,信息滯后、閉塞,以至于許多新思想未能給毛澤東幼年生活帶來改變和影響。
自8歲入南岸私塾就讀以后,毛澤東啟蒙于《三字經》、《論語》等儒家幼兒學前讀物,1904年轉到韶山關公橋私塾后,開始系統學習“四書五經”等經典著作,1905年至1906年復又轉至橋頭灣私塾,埋首于《公羊春秋》、《左傳》等一系列經史中。經年累月的儒家正統思想教育使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對孔子和儒家思想自發地產生了“機械式尊崇信服”,即對儒家思想及其經典著作進行機械記憶后,年幼的毛澤東并沒有能力去辯證看待自己所學的知識,因而會對儒家極為尊崇的圣人孔子產生機械式的尊崇信服。這一點在1936年毛澤東同美國友人斯諾的談話中有所提及:“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四書,讀了六年,可是不到位。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1]
少年時期的這些機械式記憶的印跡,毛澤東終其一生也難以抹去。美國學者霍勒布尼奇在20世紀60年代對《毛澤東選集》作了一次統計,說其中所引用的全部語錄里面,儒學和新儒學所占的比重達到22%,居各種語錄之首。[2]但有一點必須強調,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對儒家思想更多的是迫于那個時代尊儒、尚儒的形勢而被動地對其進行的有限接受,并非發自內心的信服。當時,毛澤東正處于一個迥異于儒家經典著作宣揚的現實社會:內憂頻繁,外患不斷,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處于社會底層的廣大勞動人民飽受剝削與壓迫。正是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以及尖銳的階級對立,逐步瓦解了毛澤東對儒家思想依稀產生的“機械式尊崇信服”,引發出少年毛澤東心中懵懂的對儒家思想的質疑。這為后來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二、五四運動后至建國初期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揚棄”
結合毛澤東在五四運動期間的隨筆、論文和友人書信來看,渴望成就一番事業的他,熱衷于發掘儒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他繼承了儒家思想形式上的具體框架,而對于實質內容大加鞭撻,更傾向于運用當時所學去填充他所繼承下來的形式上的框架。盡管少年時期的“正統”烙印無法磨滅,但自走出鄉關、投身于新文化運動浪潮中之后,毛澤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開始逐漸有了質的轉變,特別是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俄國于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一事件,給當時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可以說,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揚棄”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的做法。這樣一來,不僅能滌蕩儒家思想中的腐朽糟粕,而且能批判地汲取其中有利于革命事業的養分和精華。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言,“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珍貴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3]總的來看,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揚棄”,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關于儒家“倫理”思想
前文提到毛澤東本人繼承了儒家思想形式上的具體框架,而儒家“倫理”思想,正是其中最能起到深刻影響中國人民作用的支架。正因看到了這一“支架”強有力的作用,他屢屢與周邊友人探討對儒家“倫理”思想進行改革的必要性。1917年7月23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道:“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陽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他的這種“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的思想傳播并未止步于此。時隔一個月,毛澤東與張昆弟相約暢游湘江之后一同前往蔡和森家,三人再次圍繞其倫理革命的主張進行交流。他說:“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4]
毛澤東認為個人意志是一切人類改良計劃的關鍵所在,既肯定了個人在自然規律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又強調了個人自我修養的重要性。毛澤東批判地繼承了儒家倫理模式中對意志和自我修養的看法,但這種繼承的前提在于,能否把它們與中國革命緊密聯系起來,始終以革命為首要的服務對象。意志與自我修養,盡管在毛澤東有關人的行動和人的意識變化的思想中占有首要地位,但它們都服務于毛澤東的目的,服務于革命意識的創造,而不是被導向為儒家稱頌的對圣賢和血緣宗室盲目服從的關系。就這一意義而言,毛澤東顛覆了儒家千百年來的核心價值觀,從當時武裝革命的需要出發摒棄了儒家思想中諸如“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等消極因素,在吸收了儒家“倫理”思想中積極因素的同時,創造出符合革命建設實際的新的倫理機制。
(二)關于儒家“民本”思想
“民本”出自《尚書·五子之歌》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民”乃是國家的根本,只有重視“民”,國家才能安寧。而孟子在繼承孔子仁愛思想的同時,進一步發展出“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在《孟子·盡心下》中明確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后,歷代儒家的有識之士對民本思想都進行了不同程度上的闡發,重視民本思想。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民本思想是一種理想色彩濃厚的理論,尤其在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時代更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存在。即便出現了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古代社會少有的治世,也有幾位開明帝王不同程度地實踐過民本思想,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民本”作為儒家學派的一種政治價值理想,是建立在鞏固王權秩序這一基礎之上的,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其對“民”的封建統治和剝削壓迫。在統治階級看來,重“民”多少,原先固有享受的特權和利益就會失去多少。因此,在封建王朝中,“重民”的實現與否以及具體實現的程度,由于過分依賴于統治階級內部對自身既得利益和特權的讓渡許可,其實踐效果總難免會大打折扣。
儒家的民本思想,為毛澤東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營養,也為毛澤東的政治實踐提供了豐富的歷史借鑒。在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著重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對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在他看來,人民群眾不但是歷史的開拓者,更是人類社會全部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蘊藏著無限的智慧和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以及革命戰爭的磨礪,使毛澤東深刻領悟到讓人民群眾當家做主可實現千百年來尊儒家思想為正統的封建王朝無法企及的“民本”,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以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為根本的社會理想。這也是他長期一直堅持“始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5]的深層原因。
綜上所述,毛澤東結合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批判地繼承了儒家“民本”思想,形成了具有實踐意義的民主政治理念,創造出了尊重、相信、依靠和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人民觀,把傳統儒家的民本思想升華到一個更高、更新的理論層面。
(三)關于儒家“知行”思想
綜觀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活動,他既重視對國家社會的直接變革,也重視對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思想的改造,強調認識和行動的統一。在毛澤東青年學生時代的筆記中,提到了“寧都三魏”之一的魏禧,并運用魏禧著作的序言解釋了他所謂的有用學問——作為明白推理的結論并能付諸實用的學問。這是毛澤東關于“知行統一”最早的看法,直至后期,毛澤東才逐漸認識和吸收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從毛澤東的《實踐論》來看,他本人也自覺把自己當成了馬克思和王陽明的實踐理論之間的中介。
可以說,毛澤東能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因為馬克思和王陽明的實踐理論之間仍有很大的差距,至少它們對哲學研究的態度就不一樣。馬克思的實踐是直接反對唯物主義忽視人的意識的那種赤裸裸的庸俗性的,[6]他把認識置于行動之前,試圖運用辯證法來解決西方哲學史上抽象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間所謂的二元論問題。而王陽明的實踐形式不是作為解決真理問題的邏輯方法提出來的,而是為了預防因過分追求抽象的諸如“善”的存在之理,從而忽略了從事世俗活動的必要性。王陽明堅持強調“良知”在對意志做出判斷時所促成的對具體行為的道德規范,從而使得認識更加依賴于事實。它的解決方法是一種平等相容的一元論,是一種包含整個宇宙和強調變革事物以知之的實踐。
毛澤東把這兩種實踐形式進行了結合,強調特殊革命意識的重要地位,在他看來,行動取決于個人意志和歷史普遍性,只有把這兩者聯系起來才能真正運用到實踐中去。
三、20世紀50年代以后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革命性批判否定”
在此之前,毛澤東對待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角度進行揚棄,批評態度是科學的且趨于溫和的。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出于現實性的需要,毛澤東開始逐步否定儒家思想,文革期間更為強烈,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將對儒家思想的革命性批判和否定推向了高峰。據此,本文按時間順序分兩個階段進行論述。
(一)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階段
這一時期,毛澤東保持了先前對待儒家思想的基本態度,但對孔子及儒家思想漸漸顯現出排斥和不滿的情緒,這種不滿大多來自于當時儒家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的“植根式”的滲透,認為其一定程度上拖了新中國發展前進的后腿。為解決當時局面,他在保持揚棄的同時,采取了漸進式的批評孔子的方法。如“曲阜縣是孔夫子的故鄉,他老人家在這里辦過多少年的學校,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要好過多少倍”。[7]到了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直接給儒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貼上了“階級”的標簽,說“孔子是唯心主義,荀子是唯物主義,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隸主、貴族,荀子代表地主階級”。[8]
毛澤東正式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1973年3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談到“批林”問題時,就談到了要批尊孔思想。這表明在他眼里,儒家思想已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已不再需要“揚棄”對待了。此外,在批評孔孟儒家觀點的同時,毛澤東特意引入了法家,多次公開表示自己認同法家、輕視儒家。他還給江青詳細講解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儒法斗爭,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在歷史上一般說是向前進的。這些人都主張法制,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是開倒車的。”[9]毛澤東還列舉出當前黨內修正主義派和歷史上反動階級的代表人物,目的是擴大“批孔”的影響力。這說明,毛澤東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否定日益尖銳,“批林批孔”運動應運而生。
(二)1974年至1975年“批林批孔”運動階段
如前所述,全國各大報刊陸續發表了許多“批孔”文章,對毛澤東提出的“批孔”加以積極熱烈的響應。一時間,“批孔”聲勢大振。為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批判尊儒思想的活動,1974年元旦發表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社論強調:“黨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討論,埋頭干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那么什么是大事呢?社論提出:“要繼續深入搞好批林整風。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①這篇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姚文元撰寫的元旦社論向全國公開放出的政治信息表明,“批林批孔”作為當年的政治任務之一被提了出來。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正式下達《關于印發〈林彪與孔孟之道〉的通知》。《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②以中央這個文件為標志,“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此時的毛澤東,在對待儒家思想的態度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原來的揚棄轉向了革命性批判。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批準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絕不是希望再度出現動亂局面,而文革帶來的長期社會動亂、國民經濟的嚴重破壞和人民的強烈不滿,本來就違背了他“大亂導致大治”的初衷。這時因“批林批孔”運動而再度出現的嚴重混亂局勢,使得毛澤東逐漸意識到運動中許多做法所潛伏的危害性。這時的他,盡管仍然對儒家思想抱有批判否定態度,但出于穩定局勢的需要,毛澤東隱約有了結束“批林批孔”的意思。
四、毛澤東對儒家思想前后轉變的原因分析
為何毛澤東對儒家思想前后轉變如此之大呢?
(一)由“機械式尊崇信服”轉向“揚棄”
之所以產生這一轉變,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受五四運動的影響。1918年,懷揣著救國于危難、救民于水火的赤子之心的毛澤東走出鄉關,來到北京大學——當時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大求學的這段時間,毛澤東與當時思想進步的各地新青年知識分子頻繁交流,尤其對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有諸多認識和獨到的見解。隨著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不斷深入,毛澤東開始反思質疑自己先前所受的儒家正統教育。而青年時期也曾信仰過儒家思想的毛澤東,在清楚認識到儒家思想的僵化教條、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之后,嘗試著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新的救國救民的思想武器。
第二,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20年前后,毛澤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儒家思想不再是他個人信仰的絕對權威,他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但他早年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令其無法從根本上對儒家思想進行切割。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后,毛澤東找到了兩全齊美的辦法:主張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采取批判繼承,即揚棄的態度,批判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華,摒棄了諸如“三綱五常”等糟粕和對革命事業起阻礙作用的東西。
(二)由“揚棄”轉向“革命性批判否定”
由“揚棄”轉向“革命性批判否定”,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取決于更強的“現實性”的需要。“文革”后期,晚年毛澤東在思想上陷入了深刻的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希望結束文革帶來的長期社會動亂局面,重振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以及安撫人民強烈不滿的情緒;另一方面,他內心深處卻始終堅持認為“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他對“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主持的“糾左”工作非常不滿意,認為“糾左”將走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地步。因此,如何防止否定“文革”成為他晚年關注的核心問題。
經過長期思考,毛澤東意識到擁護或反對“文革”與中國古代歷史上堅持或反對變革的“儒法之爭”有著某種相通之處,希望通過批孔和肯定法家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從而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和出現“修正主義”。然而,毛澤東發現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植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他試圖找到某種可能的方式來保證“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的實現。
作為經歷過五四運動的一員,毛澤東清晰地目睹了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做法對中國歷史走向的巨大影響力,它把幾個世紀以來的已經僵化教條的儒家思想、不適應世界新形勢和中國社會發展要求的舊道德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沖擊,打破了封建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上的桎梏,這無疑對當時中國的前進起到了強大的助推作用。正因為認識到這一做法對掃除舊思想、舊道德的高效性和可操作性,毛澤東根據政治運動和改造人民“尊儒”思想的需要,借鑒了這個做法。因此,解決對“文革”的態度問題,才是毛澤東對儒家思想進行“革命性批判否定”的根本原因。
五、結語
一言以蔽之,毛澤東與儒家思想之間的關系表現在階段性和非延續性轉變之上,經歷了尊儒、揚棄、貶儒三個階段。盡管毛澤東晚年發起了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批判,但他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仍然保留了對其哲學基礎與其基本特征的揚棄。毛澤東本人對待事物的揚棄態度,值得每一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借鑒和學習。面對在中國傳承了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只有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為我所用,為構建和諧社會所用,才能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所用。也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夠從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充分汲取先賢圣人的智慧養分,以此啟迪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
注釋:
①《人民日報》、《紅旗》、《解放軍報》社論:《元旦獻詞》,1974年1月1日。
②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于印發〈林彪與孔孟之道〉的通知》,1974年1月18日。
[1]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劉思齊.毛澤東的哲學世界[M].北京:中國書店,1993.31.
[2] [美]霍勒布尼奇.毛澤東的辯證法[J].中國季刊,1964,(19).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澤東早期文稿[Z].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639.
[5] 榮晨,鐵纓,楊柳.評說毛澤東[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21.
[6] [美]魏裴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M].李君如,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249.
[7] 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4.
[8] 陳晉.毛澤東之魂[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271.
[9] 蔣建農.毛澤東全書:第4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