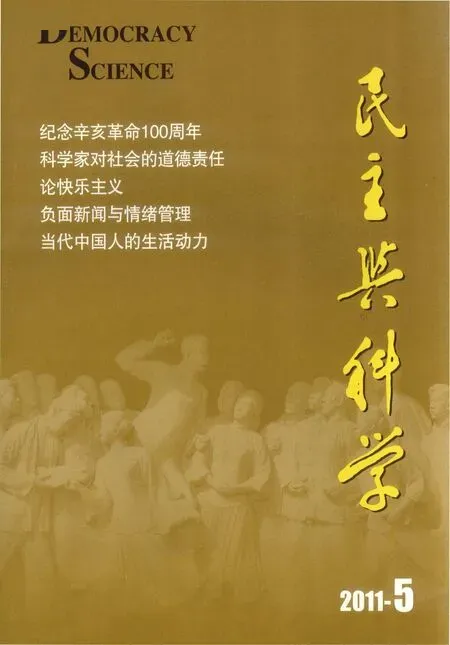也談民主與科學(xué)
■武際可
民主和科學(xué)的親密關(guān)系曾經(jīng)被許多先賢研究過。科學(xué)和民主是一對孿生姐妹。沒有民主也就不會有現(xiàn)代科學(xué);而沒有科學(xué),處于蒙昧?xí)r期的民族,更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一
什么是科學(xué)?給科學(xué)下一個(gè)準(zhǔn)確的定義很難,我們可以從各種層面去了解科學(xué)。美國社會學(xué)家默頓說,科學(xué)必須遵從非贏利性原則、普遍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和可懷疑性原則。我國學(xué)者顧準(zhǔn)說:“所謂科學(xué)精神,不過是哲學(xué)上的多元主義另一種說法而已。”我們不妨把這些說法引申一下:所謂科學(xué),就是對自然和社會規(guī)律認(rèn)識上的民主。這種民主不是簡單地以多數(shù)人的意志來決定真理,而是靠擺事實(shí)講道理的方法來判定真理。所謂擺事實(shí)就是實(shí)驗(yàn)和觀測的事實(shí),所謂講道理就是靠嚴(yán)密的邏輯推演包括數(shù)學(xué)推理和演算。科學(xué)的結(jié)論要在一定專家的范圍內(nèi)有相當(dāng)多數(shù)人認(rèn)可才能成立。不過任何個(gè)人或團(tuán)體,只要是經(jīng)過實(shí)驗(yàn)或觀察、或經(jīng)過嚴(yán)格的推理發(fā)現(xiàn)多數(shù)人認(rèn)可的結(jié)論是錯(cuò)誤的,都可以對它提出批評。一部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史,就是不斷由少數(shù)人掌握了新的理論推翻以往多數(shù)人認(rèn)可的理論,然后為多數(shù)人承認(rèn)的歷史。
什么是民主?要給民主下一個(gè)準(zhǔn)確的定義恐怕更難。有的人把民主集中制解釋為集中指導(dǎo)之下發(fā)揮下級的積極性,下級在上級給定的框架里,提出各種建議,供給上級集中的豐富的材料,以便上級集中下級的合理建議,按照這種說法,民主就成為上級剽竊下級創(chuàng)造的代名詞。還有一種對民主的理解,認(rèn)為是:按照統(tǒng)計(jì)多數(shù)人的意愿來決策。這種說法也過于簡單,如果多數(shù)人的意愿是要損害少數(shù)人的利益,這在許多情況下就會成為多數(shù)人傷害弱勢群體的理論根據(jù)。還有一種解釋是,民主是對集中而言的,自由是對紀(jì)律而言的,民主和自由要有一個(gè)度。超過了這個(gè)度,民主就要破壞集中,自由就會傷害紀(jì)律。這樣解釋,有一個(gè)根本困難,就是誰來掌握這個(gè)度,最后還是要救世主來掌握,最后必然落入權(quán)威主義或歷史唯心主義的圈套中。
到底應(yīng)當(dāng)怎樣理解民主呢?我的體會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是在一定范圍內(nèi)以統(tǒng)計(jì)多數(shù)人的意愿達(dá)到集中的目的。不過單靠這一點(diǎn)并不能保證所得到的集中意見是正確的,為此真正的民主必須要給少數(shù)人留有說服多數(shù)人的空間,多數(shù)人必須留給少數(shù)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充分發(fā)表意見的權(quán)利,即給少數(shù)人以自由。這種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jié)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只有和自由連在一起的民主才是真正完全的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一個(gè)問題的兩個(gè)方面。當(dāng)我們提到民主時(shí),不言而喻地應(yīng)當(dāng)包含給予少數(shù)人的這種高度的自由。少數(shù)人要服從多數(shù)人的決策,而多數(shù)人要尊重少數(shù)人發(fā)表不同意見的自由。其實(shí),多數(shù)和少數(shù)是相對而言的,一個(gè)人在一個(gè)問題上屬于多數(shù),在另一個(gè)問題上就可能屬于少數(shù)。所以這種給少數(shù)人的所謂自由,實(shí)際上是人人都可以充分享用的自由。
所謂自由,就是發(fā)表錯(cuò)誤意見的自由。因?yàn)槎鄶?shù)人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意見,往往是真理。如果沒有上面說的這種自由,實(shí)際上就是一種專制制度。法國伏爾泰曾經(jīng)猛烈抨擊過盧梭的一部書,但是,當(dāng)伏爾泰得知當(dāng)局要查禁盧梭的這部書時(shí),他挺身而出為之辯護(hù)。他對盧梭說:“我堅(jiān)決反對你的觀點(diǎn),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這種話的權(quán)利!”這就是真正民主中多數(shù)派應(yīng)當(dāng)遵從的一種精神。不過,上面所說的自由,也僅到上面所說為止,它不允許在行動上破壞多數(shù)人的決策,不能破壞執(zhí)行,更不能訴諸武力來對抗執(zhí)行,尤其不能搞暗殺、搞恐怖活動。中國古人說:“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說自己雖然不同意,除了上述允許的表達(dá)意見的方式外,還要使多數(shù)人的決定能以執(zhí)行,這才是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決定所應(yīng)當(dāng)持有的態(tài)度,這也是一種美德。那種我的事辦不成,也要讓你的辦不成,大家都辦不成事,這不僅不是君子所為,也是不符合民主精神的。
二
科學(xué)的發(fā)展需要民主的環(huán)境。這里有兩層意思:
一方面,一種新的科學(xué)見解和理論出現(xiàn)之初,都只是少數(shù)人理解和掌握,而且總是被多數(shù)人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如果沒有民主的環(huán)境,多數(shù)人不給少數(shù)人以說服多數(shù)人的空間,即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新的科學(xué)見解和理論就會被扼殺而很難為多數(shù)人掌握。現(xiàn)在各行各業(yè)都在提倡創(chuàng)新,科學(xué)的本質(zhì)也就是創(chuàng)新,可是如果不給少數(shù)人充分的自由,新的東西是永遠(yuǎn)出不來的。一個(gè)社會如果嚴(yán)格禁止錯(cuò)誤言論,也就不會有科學(xué)和創(chuàng)新。
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的偉大啟蒙學(xué)者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quán)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quán)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jīng)驗(yàn)。有權(quán)力的人們使用權(quán)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歷史事實(shí)證明,那些握有權(quán)力的人不僅會濫殺無辜、草菅人命、制造冤獄、搜刮民財(cái),而且在對自然和社會規(guī)律的認(rèn)識上也要把自己裝扮為全知全能的圣人,壟斷認(rèn)識,不許不同的認(rèn)識傳播。這方面的例子多不勝舉。
在科學(xué)史上,即使是不掌握權(quán)力的學(xué)者,也總是利用自己已經(jīng)形成的權(quán)威或依靠和投靠有權(quán)的人,企圖使自己的學(xué)說更為永恒。量子力學(xué)的奠基人,大物理學(xué)家普朗克說得好:“一種科學(xué)革新打開道路,很少是由于逐漸征服和改變它的對手來實(shí)現(xiàn)的,很少是把Saul變成Paul的(來自圣經(jīng)的典故,指原來堅(jiān)決反對后來成為堅(jiān)決支持的人),而是靠它的對手逐漸地死亡而新成長的一代從一開始就熟悉它的思想。”所以,新的學(xué)說要戰(zhàn)勝老的學(xué)說,一般說來是要經(jīng)過很艱苦的斗爭的。真正民主制度,就在于能夠充分保護(hù)新學(xué)說傳播的自由,其中尤其是培養(yǎng)人的教育系統(tǒng)。不過一切都不能那樣理想。
遠(yuǎn)的說,我國古代嚴(yán)禁民間研習(xí)天文,犯禁者將被處以極刑,所以我國古代許多天文著作多失傳。入清,傳教士湯若望等還由于推行新歷被判凌遲處死,后來雖然湯本人獲赦,同案的5人被處死。意大利的布魯諾因堅(jiān)持哥白尼日心說,而被宗教勢力活活燒死。伽利略因?yàn)槌霭妗秲煞N世界觀的對話》支持日心說而在1633年被判管制,并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遲至1992年才正式獲得羅馬教庭的平反。
近的說,二戰(zhàn)期間,由于希特勒的排猶政策,侵犯猶太人科學(xué)家研究和教學(xué)的權(quán)利。其后果明顯表現(xiàn)在科技人員嚴(yán)重的流失。僅在1933至1938年間,一千八百八十位第一流的科學(xué)工作者從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學(xué)流亡。據(jù)英國生物學(xué)家李約瑟教授估計(jì),其中有德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百分之二十五強(qiáng)。到1937年,在德國大學(xué)從事自然科學(xué)的學(xué)生人數(shù)只有1932年學(xué)生人數(shù)的大約三分之一。在蘇聯(lián),20世紀(jì)30年代,李森科為迎合斯大林的階級斗爭理論,提出所謂獲得性遺傳和生物種內(nèi)斗爭的理論受到斯大林的青睞,從而青云直上,1940年蘇聯(lián)現(xiàn)代遺傳學(xué)的開拓者瓦維羅夫被逮捕并于次年被判死刑,在執(zhí)行前瓦維羅夫病死獄中。隨后在蘇聯(lián)掀起了在生物學(xué)中批判摩爾根學(xué)派、在化學(xué)中批判共振論、在數(shù)學(xué)中批判控制論,在物理界批判量子力學(xué)和相對論等等的熱潮,致使蘇聯(lián)在遺傳學(xué)、電子計(jì)算機(jī)等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國家。20世紀(jì)50年代我國在這些領(lǐng)域中,由于緊跟蘇聯(lián)老大哥也不同程度地開展過類似的批判。
在我國,1949年之后的歷次學(xué)術(shù)批判運(yùn)動大部分是把意識形態(tài)和學(xué)術(shù)認(rèn)識問題當(dāng)做政治問題來批判。更不要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也出現(xiàn)過批判相對論,批判熱力學(xué)第二定律之類的荒唐事,甚至導(dǎo)致一些學(xué)者被迫害致死。再例如關(guān)于黃河三門峽建壩,事實(shí)證明黃萬里教授反對建壩的意見是正確的,可是黃萬里卻因此而戴上了右派帽子。而迎合“黃河清”的專家卻炙手可熱居于重位。事實(shí)是,三門峽大壩自1958年攔洪,到1961年導(dǎo)致關(guān)中平原的水災(zāi)。陜西省人民代表不得不于1962年正式向人代會提出議案要求解決三門峽大壩所帶來的問題。
著名科學(xué)家愛因斯坦在講到為了推進(jìn)人類對自然和社會規(guī)律的認(rèn)識,必須有“在一切腦力勞動領(lǐng)域里的言論自由和教學(xué)自由”,而為此要有這樣的社會條件,即:“一個(gè)人不會因?yàn)樗l(fā)表了關(guān)于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的意見和主張而遭受到危險(xiǎn)或者嚴(yán)重的損害。”“為了使每個(gè)人都能表白他的觀點(diǎn)而無不利的后果,在全體人民中必須有一種寬容的精神。”“人不應(yīng)當(dāng)為著獲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沒有時(shí)間也沒有精力去從事個(gè)人活動的程度。而沒有這第二種外在的自由,發(fā)表的自由對他就毫無用處。如果合理的分工問題得到解決,技術(shù)的進(jìn)步就會提供這種自由的可能性。”此外,“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可以稱為內(nèi)心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權(quán)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guī)和習(xí)慣的束縛。這種內(nèi)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難得賦予的一種禮物,也是值得個(gè)人追求的一個(gè)目標(biāo)”。愛因斯坦認(rèn)為這種“自由的理想是永遠(yuǎn)不能完全達(dá)到的,但如果要使科學(xué)思想、哲學(xué)和一般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得到盡可能快的進(jìn)步,那就必須始終不懈地去爭取這種自由”。
事實(shí)上,盡管我們的社會比起專制的封建時(shí)代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jìn)步,我們還是有阻礙人們自由探討科學(xué)問題的現(xiàn)象發(fā)生。所以還是要不懈地去爭取這種自由。
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大學(xué)校長蔡元培先生,在民國時(shí)代深感于當(dāng)時(shí)的言論不自由,于1919年6月15日向當(dāng)局提出辭職書。辭職書中有這樣一段:“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xué)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xué)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shí)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他的大學(xué)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xué),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jìn)去了,想稍稍開點(diǎn)風(fēng)氣,請了幾個(gè)比較有點(diǎn)新思想的人,提倡點(diǎn)新的學(xué)理,發(fā)布點(diǎn)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diǎn)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diǎn)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dāng)?shù)霓q論法來干涉了,國務(wù)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xué)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xué)的校長么?”
這里應(yīng)當(dāng)少加說明的是,蔡元培1906~1916年間赴德法留學(xué),他深深體會到德國由洪堡在1810年創(chuàng)辦的柏林大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自由和學(xué)校高度自治,是西方現(xiàn)代教育最重要的革新原則。也正是由于德國教育的這些新的原則,開創(chuàng)了空前的學(xué)術(shù)自由的空氣,所以才迎來了19世紀(jì)末量子力學(xué)和相對論在德國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代新人,從而推進(jìn)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革新。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之后所倡導(dǎo)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是要在中國實(shí)現(xiàn)這些原則。遺憾的是,蔡元培僅僅當(dāng)了兩年校長,就已經(jīng)感覺到處處掣肘,沒有絲毫活動的空間,不僅主管部門干涉,當(dāng)時(shí)一部分民眾也不那么寬容,所以才不得已辭職。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在中國發(fā)展科學(xué)和營造發(fā)展科學(xué)所需的自由氛圍是多么艱巨的任務(wù)。我們的社會有了不少進(jìn)步,不過要做到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境界,要做到學(xué)校高度自治和高度學(xué)術(shù)自由,我們還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
另一方面,只有民主的環(huán)境,才能發(fā)展和產(chǎn)生科學(xué)和實(shí)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邏輯學(xué)。邏輯學(xué)是民主政治和科學(xué)共同的必要基礎(chǔ)。
事實(shí)上,既然民主是要靠統(tǒng)計(jì)多數(shù)人去說服別人以獲得多數(shù)。辯論就成為表決前的必經(jīng)的階段。在專制制度之下是無需也不允許辯論的,哪怕皇帝是一位糊涂蛋,他說的話也要被當(dāng)作金科玉律。事實(shí)是,哪里有辯論哪里就需要邏輯學(xué),而沒有邏輯學(xué)的辯論只能是胡攪蠻纏。佛教中不同教派為爭取信徒產(chǎn)生辯論,于是就有“因明學(xué)”也就是邏輯學(xué)產(chǎn)生。我國在戰(zhàn)國時(shí)期,有諸子百家的辯論,所以產(chǎn)生了《墨經(jīng)》中的《墨辯》,是邏輯學(xué)的萌芽。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政治產(chǎn)生在古希臘,在大約公元前800~公元前100年,長達(dá)700年的貴族民主政治氛圍中,產(chǎn)生了許多辯論家。由于辯論的普及,就發(fā)展了進(jìn)行辯論所必須遵從的規(guī)律以及怎樣在辯論中取勝的學(xué)問,這就是邏輯學(xué)。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工具論》是古希臘邏輯學(xué)的大成,直到1787年德國哲學(xué)家康德在他的哲學(xué)名著《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邏輯學(xué)沒有能前進(jìn)一步,因此看起來,邏輯似乎是完成并且結(jié)束了。”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尊稱亞里士多德為《邏輯學(xué)》之父。由于邏輯學(xué)的發(fā)展,古希臘產(chǎn)生了推理的數(shù)學(xué)。世界上的文明古國都有自己的數(shù)學(xué)傳統(tǒng),有埃及的古數(shù)學(xué),有印度的古數(shù)學(xué),有中國的古數(shù)學(xué),然而產(chǎn)生推理數(shù)學(xué)的唯一的地方只在古希臘。而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古希臘推理數(shù)學(xué)的巨著。阿基米德關(guān)于力學(xué)的著作則是古希臘推理數(shù)學(xué)和力學(xué)相結(jié)合從而產(chǎn)生現(xiàn)代精密科學(xué)萌芽的典范。17世紀(jì)歐洲產(chǎn)生的以力學(xué)為開端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xué)正是繼承和發(fā)揚(yáng)了以阿基米德為代表的古希臘科學(xué)傳統(tǒng)的結(jié)果。古希臘被羅馬滅亡后幸虧有阿拉伯人翻譯和保存了古希臘的科學(xué)文獻(xiàn),才使它在后來歐洲文藝復(fù)興中重新發(fā)揮作用。所以愛因斯坦說過:“西方科學(xué)的發(fā)展是以兩個(gè)偉大的成就為基礎(chǔ)的,那就是:希臘哲學(xué)家發(fā)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德幾何學(xué)中),以及通過系統(tǒng)的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有可能找出因果關(guān)系(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
綜上,我們看到民主不但為科學(xué)提供發(fā)展的外部條件,也推進(jìn)構(gòu)成科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方面邏輯學(xué)的產(chǎn)生和成熟。而近代科學(xué)的發(fā)展也只有在歐洲文藝復(fù)興之后、在推翻了專制制度之后,才得到飛快的發(fā)展。我國的情形也是一樣,只有在充分掃清封建殘余之后才迎來科學(xué)和技術(shù)的空前發(fā)展。
三
社會民主的推進(jìn)需要有科學(xué)的進(jìn)步。科學(xué)不僅推動技術(shù),新的技術(shù)推進(jìn)新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產(chǎn)生,從而推 進(jìn)社會的變革。更重要的,科學(xué)發(fā)展的結(jié)果逐漸掃除了人類的蒙昧和迷信。在專制社會,統(tǒng)治者總是利用人民的愚昧和迷信,來散布他們高居統(tǒng)治地位的合理性。世界各國早期都有所謂“君權(quán)神授”的說法,就是說,他們的權(quán)力是上帝所授予的。不僅他們自己是這樣,他們的子女也是高貴的。科學(xué)的發(fā)展破除了這類迷信,暴君被聯(lián)合起來的市民按照多數(shù)人的意愿廢除或絞死。
歷代專制暴君和惡勢力都是千方百計(jì)反對科學(xué)真理的傳播,而科學(xué)的真理總會沖破重重阻力而被廣大群眾所掌握。科學(xué)真理沖破專制制度的過程也就是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因此科學(xué)的發(fā)展和社會的民主化進(jìn)程,大體上來說是同步的。
英國數(shù)十年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xué)者李約瑟不僅發(fā)現(xiàn)民主和科學(xué)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他還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推進(jìn)科學(xué)的學(xué)者群在心理上也自然地傾向于民主。他說:“現(xiàn)代的科學(xué)與民主顯然是同時(shí)發(fā)生的。例如歐洲文藝復(fù)興、宗教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是這個(gè)運(yùn)動的一部分。我們早已知道希臘民主與科學(xu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考諸中國科學(xué)與技術(shù)的發(fā)展,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類似的情形。最有趣的是我們發(fā)現(xiàn)科學(xué)與民主在理論上甚至心理上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李約瑟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中國歷史上“道家對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識,全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匹敵,而為一切中國科學(xué)的根基”。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儒家接受封建社會而道家強(qiáng)烈的反對之”。所以呂不韋說:“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說明科學(xué)要求尊重客觀規(guī)律,這和儒家為了當(dāng)官和向上爬主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盲從的態(tài)度是完全不同的。尊重客觀規(guī)律既是科學(xué)精神的需要,也是民主精神的需要。科學(xué)的發(fā)展從社會心理狀態(tài)上也為社會的民主化準(zhǔn)備了條件。
為人類破除迷信和推進(jìn)民主進(jìn)程是科學(xué)最為重要的社會功能。
科學(xué)是對自然和社會規(guī)律認(rèn)識上的民主,而民主可以認(rèn)為在某些群體活動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合乎科學(xué)規(guī)律的運(yùn)作。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科學(xué)與民主是同一種精神在對待客觀規(guī)律的認(rèn)識和群體活動、國家政治生活上的兩種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它們是孿生的彼此不能分割的一對。
正因?yàn)榭茖W(xué)和民主有如此密切的關(guān)系。它們對于推進(jìn)社會進(jìn)步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五四運(yùn)動之前,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喊出了“民主與科學(xué)”的口號,陳獨(dú)秀寫道:“西洋人因?yàn)閾碜o(hù)德(democracy)賽(science)兩先生,鬧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xiàn)在認(rèn)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xué)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yàn)閾碜o(hù)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在21世紀(jì)的今天,為了科學(xué),為了民主,仍然是我們努力奮斗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