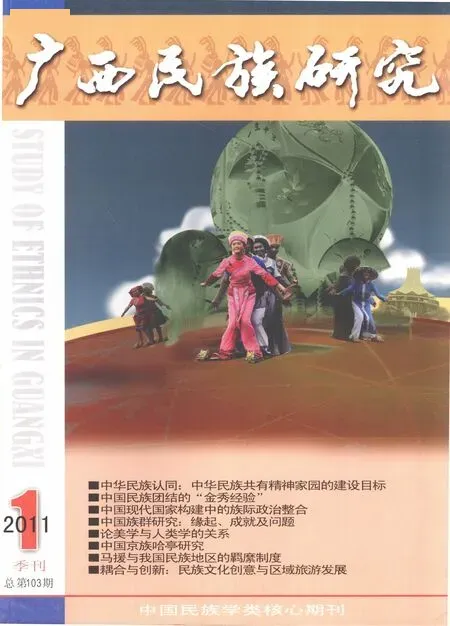民族旅游文獻中的文化認同研究*
吳其付
民族旅游文獻中的文化認同研究*
吳其付
文章對近年來國內外民族旅游與文化認同的研究進行了詳細的梳理,發現國外對于民族旅游與文化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認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變遷以及民族藝術品的轉化與復興等四個方面。而國內對民族旅游與文化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身份與文化認同、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復興等兩個方面。文化認同既有來自主流社會的建構,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認知。在旅游發展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場景中,頻繁的人員流動和文化之間的交往接觸引起地方民族對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別,進而形成了對本民族文化認同的考量。
民族旅游;文化認同;文化變遷
Abstract:The article has carried on detailed combing ethnic tourism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research to the recent years,through analyzing we may discovered,that overseas regarding ethnic tour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nation-state cultural identity,ethnic cultural identity,ethnic cultural vicissitude as well as ethnic art transformation and revival.But domestic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ethnic status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the modernization and the ethnic cultural revival and so on.The cultural identity has come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s construction,also had the ethnic self-cognition.In this kind of specific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tourism between the frequent personnel flowing and the cultural contact caused the ethnic about what culture distinguished between me and them,and then has formed the consideration on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ethnic tourism;cultural identity;cultural vicissitude
文化認同問題在旅游文獻研究中經常出現,旅游作為一種現代人評估他們的世界,界定自我的認同感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霍爾 (Hall)指出,旅游是一個國家或民族表明它者形象的一種手段,通過旅游吸引國內外游客的到訪可以增加對該國家或民族的認識和理解。[1]“我們是誰”,“我們怎樣讓您們看到我們”等信息滲透在各種旅游促銷活動中,每個國家或民族都希望突出自己獨特的個性和身份以提升和強化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認同。
一、西方文獻中的旅游與文化認同研究
西方文獻中關于旅游與文化認同研究,重點關注的是旅游與族群符號、物質文化復興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具體體現在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認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變遷以及民族藝術品的轉化與復興等四個方面。
1、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
旅游對于促進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有著重要力量。各級政府都傾向于鼓勵各種與文化和政治認同一致的旅游方式,而且也通過各種官方宣傳材料向人們傳遞出一種該國的政治文化認同。政府在通過它的旅游開發政策和各種旅游促銷手段向國外旅游者宣傳時,力求凸出本國在外界中的好印象,以確保自己獨特的精神價值和文化認同能夠得到外來旅游者的尊重與賞識。鄧肯·賴特 (Duncan Light)在《羅馬尼亞的恐怖旅游:文化認同與國家》中指出,政府是文化含義的仲裁者,它在旅游發展、計劃編制與政策制定方面扮演著重要作用。許多國家進行了很多向外國游客促銷本國遺產和文化的活動,其目的是通過讓游客體驗和理解他們自己的歷史和生活方式,更大程度上激勵出該國家的民族文化認同。對于那些希望吸引可觀的外來投資進行國內建設的國家來說,旅游體現出的本國文化認同成為影響外來投資的重要力量。[2]
自從1989年共產主義體系解體以來,中東歐國家正在試圖重新構建他們的文化認同。一是要否定四十多年來構建起的社會主義國家認同,二是要構建起民主、多元、資本和向西方看齊的后社會主義國家認同,而旅游在這個認同構建過程中扮演著重要作用。鄧肯·賴特 (Duncan Light)在《凝視共產主義:德國、匈牙利、羅馬尼亞的遺產旅游與后共產主義者認同》一文中,通過對德國的柏林墻、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雕像以及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的民眾之家三個共產主義遺產旅游考察后指出,由于忽略了旅游者對共產主義遺產的興趣,使得這種重塑民族國家文化認同的過程在后社會主義時期依舊艱難與漫長。[3]
2、地方族群的文化認同
族群意識由不同群體的相互影響產生,族群發展既是里群 (in-group)同一性和差異性結構關系變化的產物,也是不同群體各自冠冕堂皇表述的產物。麥克納爾 (MacCannell)在《族群重建:第三世界的旅游與文化認同》中指出,旅游對于族群邊界的保持、轉化、重建有重要影響,旅游訴求的重要目標就是族群文化認同。[4]范·登·貝 (Van den Berghe)、奧僑亞 (Ochoa)在《旅游與庫茲科的民族意識形態》中探求了民族旅游開發與印加本地意識的關系。雖然印加文明與旅游沒有關系,但他們卻是共存共生的,都是一種精英現象。前者是當地自豪感的典型表現,是區域認同的象征,印加人保護對游客具有吸引力的遺產,為旅游商品化包裝注入了豐富的文化內涵。[5]伊斯特曼 (Eastman)以肯尼亞的斯瓦希里族群為例,指出雖然斯瓦希里語已經成為肯尼亞的官方語言,但斯瓦希里人和他們的話語權力相對于其他族群而言仍是邊緣化的。不過,他們的語言與文化開始向政治經濟方面傾斜,以期獲得族群發展與經濟增長。作者認為,在肯尼亞進行國家重建和經濟變化時,說斯瓦希里語的族群也正在獲得他們以前沒有過的族群認同。[6]
民族旅游的核心是對異質文化的尋求,這種尋求強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認同意識。伊斯曼 (Esman)在《保存族群的旅游:路易斯安娜的克基人》中指出,旅游通過強化克基人 (Cajuns)與外來者之間的文化差異保存了獨立的族群認同。雖然克基人喜愛美國的主流文化,但他們仍舊保留著強烈的族群認同感和自豪感。克基人是他們自己文化的旅游者,他使外來旅游者沉浸在“地方臉譜”的文化之中。克基人文化成為了地方和外來者的“旅游舞臺”。這種舞臺有助于使可能遭受文化變遷而消失的族群邊界永存。[7]亞當姆斯 (Adams)在《旅游與尼泊爾的夏爾巴人:互惠與重建》中指出,尼泊爾的夏爾巴人 (Sherpas)通過為旅游者充當向導和提供相關旅游服務,獲得了經濟發展,提高了生活水平。旅游業體現了他們在登山探險中的獨特性作用,加強了他們的族群認同。[8]瓦倫·L·史密斯 (Smith)在《愛斯基摩人的旅游業:微觀模式和邊緣人》中指出,大量游客的到來,對愛斯基摩文化的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這使愛斯基摩人認識到他們的文化對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出高價來極地一游,看看愛斯基摩人的生活,這強化了族群的自我價值意識。[9]麥基恩在《走向旅游業的理論分析:巴厘島經濟的雙重性和內在的文化變化》中指出,旅游業的產生有助于巴厘人的“民間、民族或地方文化”的幸存,傳統和現代化的特點共同強化了巴厘的文化生產力和自我身份。更年輕的巴厘人發現他們作為巴厘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得靠旅游業作為關照,這使得許多人繼續充滿激情地發揚自己的傳統。[10]大衛·庫利爾 (David.Cuillier)和蘇珊·登特·羅斯 (Susan.Dente. Ross)在《認同下的賭博:美國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網站》中通過對美國224個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網站的分析,考察了帶有吸引旅游者到賭博場賭博動機的印第安部落在網站上怎樣表達了他們的認同,作者指出娛樂場的廣告宣傳表現了一種單方面的認同來取代整個印第安部落認同傾向。近40%的具有賭博場的印第安部落通過利用歷史文化遺產——主要是依賴于異域風情的它者,比如圓形帳篷和酋長頭巾來留住過去,這是一種吸引非印第安人旅游者的標志,也是設有賭博場的印第安部落傾向于白人印第安人認同的營銷策略。作者認為不管有賭博場的部落還是沒有賭博場的部落如何描述他們的歷史遺跡,事實上他們都是美國印第安人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不同于歐美主流文化的認同表現。[11]
文化的商品化會重新喚起地方族群的認同,為了獲得旅游經濟效益,他們會轉而恢復已經消失的地方文化,以營造出一種旅游的真實性。勞里·克羅蘇斯·麥迪娜 (Medina)在《文化商品化:旅游與瑪雅族群的認同》中指出,旅游開發前,當地的瑪雅文化認同相當混亂,且不明顯,而旅游發展卻為當地人帶來了一種宣稱或再次宣稱瑪雅文化認同的可能性。作者認為旅游者對瑪雅文化的特殊興趣促使了當地人,包括地方導游、藝術家、地方居民等重新認識到了瑪雅文化的重要性。雖然當地大多數村民已經拋棄了土著瑪雅人的文化認同,但對旅游的回應卻需要他們利用不同于傳統渠道的新方式去再現傳統,以體現出最為精萃的瑪雅文化,這種新方式就是轉為利用考古學家和碑銘研究專家對瑪雅古代文化研究出版的著作。他們通過向考古學家、金石學家學習古代的瑪雅文化知識,增強了自己對于祖先的理解,并將其運用在日常的旅游實踐中,從而獲得了更多的旅游收益。[12]
文化認同的構建或者傳統的創造發明是人類心智不斷變化發展的產物,并在當代語境下不斷被重塑。面向旅游者的文化商品化不僅沒有破壞族群自身文化產品的重要意義,而是成為了一個族群認同或文化認同區別的新標志。羅德里戈·阿熱里德·古內瓦爾德 (Grunewald)在《旅游與文化復興》中指出,巴西政府專門開發旅游的漫長海岸線地區,成為了強化巴西安人文化認同運動的先鋒。巴西安人的族性以及生活韻律,與美麗的海濱和陽光一起,構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對游客產生著巨大吸引力,而游客的蜂擁而至,又強化了東道主地區巴西安人自身的文化認同。最明顯有趣的是許多帕泰克斯人也迎合旅游者的這種需求,自豪的宣稱他們自己也是巴西安人。于是該區域普遍形成了巴西安人的認同意識,而這種在旅游需求下構建起來的文化認同很快得到私營企業、政府和媒體的推廣、提升和宣傳,從而確保了作為巴西安人標志的旅游吸引物的文化特色。[13]
旅游節慶活動在地方認同方面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個非常小的節慶都可能達到強化地方認同的顯著結果。美國卡薩斯河沿岸社區舉辦的“羅林跳河節”就是這樣。“羅林跳河節”主要包括卡薩斯河舞蹈、鄉村懷舊、土著美國舞蹈、自然環境體驗、地方農事慶典等內容。盡管“羅林跳河節”帶有旅游商品化的特征,但這些事件卻對地方社區的自我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克倫·德·布里斯 (Bres)、詹姆斯·戴維斯 (Davis)在《集體慶典與地方認同:一個新地域節慶的個案研究》中通過對1997年羅林跳河節的分析,指出社區節慶活動有利于提高族群和地方認同,族群認同和地方認同與節慶內涵有著緊密的聯系。[14]
近年來國際貿易、全球化、移民和旅游的發展,也引起了對族性和族群認同的消費與市場營銷行為的理論研究。艾哈邁德·賈馬爾 (Jamal)在《跨文化世界的零售業:零售業、民族認同與消費的相互影響》中以英國為例,指出移民選擇的移民方式、基于本國宗教聯系的文化認同和在英國的居住方式等族群亞文化,導致了少數族群企業主擁有的商業企業的出現,這些企業的通常特征是有著強烈的族群認同,他們互相依賴家族名譽和相互信任的信息網絡,以及擁有受到各自社區支持的強大資源。[15]
但旅游發展也可能加劇族群之間的矛盾,對于已經存在的緊張關系或合作基礎,旅游有可能成為一種催化劑,瓦解族群認同,消融族群邊界。賈米森 (Jamison)在《旅游與族群:椰子們的兄弟關系》中以肯尼亞·馬林迪 (Malindi)沿海地區的民族旅游為例,分析了旅游開發對東道主社區的民族沖突起著促進還是緩和的影響。作者認為對于當地社區那些依賴于旅游產業或商業活動 (受其影響)的成員認同的重新表述,旅游扮演著催化劑的作用。通過對社區民族關系的考察,作者發現旅游強化了族群內部認同,但同時也加劇了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16]甘伯 (Gamper)在《旅游對奧地利族群關系的影響》中指出,幾百年來,奧地利兩大族群都各自在相同的地理區域內進行著貿易和畜牧活動。但隨著近代旅游業的介入,兩大族群之間的接觸頻繁,彼此相互參與到對方事務的運作中,從而引起了長達千年的族群邊界的瓦解。[17]
3、地方族群的文化變遷
旅游是一種涵化和發展形式,它使目的地的社會文化發生變化,產生文化變遷。文化變遷通常產生四方面的影響:提高民族內部的凝聚能力和傳承能力;民族傳統文化出現加速變遷的現象;族群文化的內/外兩分制度的產生;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市場化。[18]1975年,北美人類學協會專門在圣佛朗西斯科召開了一次“旅游與文化變遷”的學術研討會,該會對旅游給墨西哥的波爾多·瓦拉塔、希臘的米克羅斯島等地帶來的文化影響給與了關注。[19]
旅游通過文化表演的形式展示民族認同,引起傳統文化在吸收外來文化下實現創新與發展,民族文化得到復興。如巴厘人的宗教儀式表演,雖然為了迎合游客需求進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其地方族群的標志并沒有改變,巴厘人的文化表演體現了民族主義問題以及民族認同是如何通過文化表演獲得協商的。[20]科勒爾 (Connell)在《小島之夢:波利尼西亞天堂的沉思》中通過對波利尼西亞島上塔西提人的研究,完整地再現了當地的文化變遷過程。偏遠貧乏、不斷散發著迷人魅力的小島是塔西提人的生活中心,優美的理想化的田園詩歌般景象是旅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小島最先給予外來者的影像。然而,由于不斷遭受外來族群的影響,特別是男性外來者,“糟糕的社會”、“粗俗的野蠻人”、“需要外來的救贖”成為了島嶼永遠不能取代的印象,小島也最終陷入了荒涼之中。不過理想化的田園詩歌般圖景仍舊保持在藝術與文學的形式里,以及照片、風景明信片、郵票、影片 (包括旅游見聞錄)、倍受歡迎的人類學和地理學著作里,還有旅游和電視里。后來,小島居民通過對舊有圖象的補充完善,在向后殖民地轉變過程中又建構起了新的小島形象。[21]古內瓦爾德 (Grunewald)在《旅游與文化復興》中以巴西波爾圖·塞古羅·帕泰克斯 (Pataxo’Indians of Porto Seguro)的印第安人為例,指出隨著新旅游景點的開發,東道主社會常常會出現文化變遷。而這些變化體現在為滿足游客需求提供有形文化產品的具體工作上,這些工作為東道主社會提供了經濟選擇和謀生方式。它體現的是一種“文化復興”的進程,因為他們通過舞臺化的商業性展示復活了傳統,這種舞臺化展示為民族旅游帶來了勃勃生機。[22]約瑟夫 (Joseph)和卡夫里 (Kavoori)在《阻礙的媒介:旅游與東道主社區》中以印度普西卡這個朝圣小鎮為例,探討了在印度宗教社區語境下理解西方旅游影響的框架。旅游帶來的經濟利益讓很多人受益,但也是對傳統和宗教的一種威脅。作者以“阻礙的媒介”來形容人們這種好惡交織的情感,即一方面允許東道主社區譴責旅游,同時也允許東道主社區以個體為主參與到旅游中去。[23]范·登·貝 (Van den Berghe)在《旅游與族群工作的分化》中描述了克里斯托波鎮的旅游發展對族群工作的分化以及對族群關系的影響。作者指出克里斯托波鎮已經逐漸成為當地民族旅游的中心,這里匯聚了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和墨西哥的旅游者,還有當地說拉地諾語的中間商,以及土著瑪雅族群,形成了旅游者、被旅游者 (土著人本身構成一種旅游景觀)、中間商 (旅游者和被旅游者的媒介以及提供服務設施)三種群體的工作分化。[24]埃文斯 (Evans)在《旅游與跨文化交流》中通過對波爾多·瓦拉塔旅游勝地社區適應性策略的考察,指出能懂兩種語言的文化經紀人的存在、季節性和常住性游客的存在加速了當地的文化變遷、強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認同。[25]伍德 (Wood)在《東南亞的民族旅游、政府與文化變遷》中指出,政府作為旅游開發的規劃者,文化意義上的商人,向旅游者進行文化展演的仲裁者,新政治形式的舞臺,其作用是矛盾和復雜的。一方面,旅游引起了政府對地方文化越來越多的干預,另一方面,又為地方文化群體提供了一種向政府表述自己不滿的新手段。[26]
4、民族藝術品的轉化與復興
通過對過去的或衰落的民族藝術品和歌舞的發展,旅游會使民族地區一些傳統藝術得到再生并重新流行。旅游最為顯著的影響是通過開發那些被認為是垂死的或消失的藝術品和表演等強化一個族群內部的認同。[27]不過,民族藝術品在向旅游藝術品的轉變過程中會出現形式、內容、規模上的巨大變化,有可能導致傳統藝術品內涵的喪失、技藝的下降。格拉本 (Graburn)在《旅游藝術品的發展》中指出,帶有民族文化內涵的旅游藝術品是一種介于物質符號、外界需求和民族抗爭與重塑的變動關系中的實體,它是連接變化中的旅游、民族與藝術的橋梁。[28]圖布斯 (Toops)考察了中國新疆旅游發展過程中手工藝品的發展情況,作者認為國際旅游引起手工藝品分化成了旅游手工藝品和民族手工藝品兩種類型,而市場與資源的兩元性又引起了手工藝品功能和形式的兩元性。當新疆的烏魯木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旅游工藝品生產基地時,吐魯番工藝品生產基地的重要性逐漸減弱。旅游在促進了喀什葛爾和庫車工藝品生產的同時,也降低了古爾加工藝品的影響。[29]博因頓 (Boynton)探討了旅游對傳統阿們派被子樣式的影響。作者認為傳統的阿們派被子,不管在設計還是工藝上,都具有很高的價值。自從旅游者涌入阿們派社區以后,他們對阿們派被子的需求導致了用于銷售和用于家庭的被子之間做工的明顯差別。[30]斯韋 (Swain)研究了土著民族藝術品生產的性別問題,作者認為性別問題不能通過發展理論來解釋,因為發展理論認為婦女生產者不是經濟利益的權利受益者,就是國際旅游縮影下全球資本浪潮統治中的受剝削者。作者通過對土著族群民族商品化數據的對比分析,揭示出內部(家庭、社區)因素賦予了女人商品生產的權利,而性別、階層、民族等層面的外部 (市場、政府)因素則限制了土著女人和男人的角色選擇。作者還指出,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文化復興的普遍話題已經主導了“第四世界”藝術品生產的性別話語權力。[31]納什 (Nash)在《旅游、工藝品與密克羅尼西亞的族群認同》中考察了旅游對密克羅尼西亞工藝品的影響,作者指出旅游使日常世俗的工藝品和熟練技師生產的價值較高的藝術品之間存在差異,作者認為對當地工藝品生產體系變化方式的考察為了解民族認同變化提供了重要視角。[32]馬克威克 (Markwick)在《旅游與馬耳他島的手工藝品開發》中指出,用傳統技藝手工編織的馬耳他絲帶需要耗費一個熟練工人幾個小時的時間,但所得的經濟回報卻相當低。盡管這樣,這些工藝品傳統技藝的復興卻在文化傳統和馬耳它人認同中扮演著重要作用。[33]
二、中國文獻的旅游與文化認同研究
在中國,地方民族在面臨現代化、全球化不斷深入滲透的現實面前,也在努力地尋找同現代性融合的可能,努力地進行著自身文化的現代轉型。旅游在這樣一個建構過程起著重要作用,它帶來了地方文化的復興,地方性的文化以及民眾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建構著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中國學者關于旅游開發與族群文化認同的研究重點關注的是在旅游開發下的文化認同與現代化的關系。具體可分為族群身份與文化認同、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復興等兩個方面。
1、族群身份與文化認同
1999年,“人類學:旅游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昆明召開,從此揭開了中國學者從人類學角度考察民族旅游的新趨向。在這次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專門討論了旅游與族群認同的關系。香港中文大學的白蓮在《旅游與歷史記憶:關于滿族身份再認同運動的個案研究》中指出,中國的旅游業發展正在幫助滿族這樣的“邊緣族群”重新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澳門大學與葡萄牙阿維若大學的蔡利平等三位學者在《關于民族旅游的文化遺產保護與解讀》中對澳門“土生葡人”這個特殊族群進行了考察,作者指出隨著澳門回歸日期的日趨接近,該族群的身份認同問題也逐漸凸現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旅游便為其提供了一種對內相互凝聚,對外擴大影響的途徑,因為通過對“土生葡人”文化特色的展示,族群成員獲得了同一性方面的強化。而旅游者在欣賞這種特色時,無形中也承認和接受了“土生葡人”在文化“異質性”上的正常地位。[34]徐新建通過“穿青人”、“銀水寨”和“藏羌村”的個案分析,指出民族旅游中“旅游民族”的出現強化了中國社會“多元一體”結構中的族群身份及其文化分野。[35]楊慧在《民族旅游與民族認同、傳統文化復興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開發中的“族群”及其應用泛化的檢討》中指出,云南各少數民族在旅游開發的特定場景中,族群意識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認同被強化,甚至比以往更強烈,并在與民族旅游發展的互動中不斷傳承、延續、發展。云南民族旅游推動著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構,為族群文化的復制、再造和再生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場景和舞臺。[36]周星通過對黔東南苗族村寨的觀光產業與少數民族文化展示的調查和研究,指出在文化旅游過程中,旅游者與當地的族群形成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族群關系。雖然地方展示給游客的文化部分是一種表層性的東西,但它依然在地方民族的文化認同上有著重要價值。[37]
在旅游過程中,民族接待地的居民自覺不自覺地與各種各樣的國內外游客打交道,而在日益頻繁的接觸中又往往會喚起他們對自身歸屬的認識,進而引起他們對自身身份表述的強烈關注。[38]因此可以說,旅游為邊緣族群宣稱自身族性提供了空間、機遇和資源,他們可能利用旅游提供經濟、社會和文化空間去宣稱它們獨特的族性。云南省寧蒗縣落水村的摩梭人在旅游開發中就表現出了對于自我意識和自我表述的強烈關注,他們作為納西族象征性的族群意識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認同得以強化,并在與民族旅游發展的互動中得以傳承、延續、發展。[39]艾米莉 (Emily)和曹 (Chao)等人在《霸權、中介與重現過去:中國納西族東巴文化的復興》中指出,納西族利用政府主導型旅游復活了在文化大革命間受到壓制的東巴文化。通過政治和經濟上的扶持,作為旅游產品包裝的東巴文化促進了納西傳統文化的再現。[40]香港人類學學者陳水木在《中國西南貴州“革”人認同的協調與再現》中,對貴州被識別為苗族分支的“革”人的族群認同進行了調查研究。他指出,盡管國家的民族識別對該族群的民族身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隨著民俗旅游業在當地的發展,為了在民族文化旅游中獨樹一幟,該族群開始質疑原來的苗族身份,要求將本族群重新劃為單一的民族。由此,陳水木提出,應該注意到原來的國家影響力與旅游產業的發展和多元化的社會轉型相結合對傳統的認同形式所產生的影響。[41]
2、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復興
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地方的“土著文化”必然會受到旅游者所帶來的現代化與全球化文化的影響,從而引起地方文化的變遷。但地方的“土著”并不是只能對現代性的文化做出消極的反映。在與外來文化發生接觸的過程中,地方會基于自身文化理念,在本土宇宙觀的支配下將外來文化納入到他們自己的體系中去,借以完成新時期的文化轉型,從而建構起他們新的文化認同。海力波以廣西的黑衣壯族群為例,探討了梭坡縣“文寨”的黑衣壯居民在近年來的旅游與文化開發過程中所進行的文化——政治實踐活動。他從文化表征的維度考察了黑衣壯族群成員在旅游開發的過程中對本族群文化加以改造、發明、展示的具體活動,揭示出了黑衣壯族群成員對自身文化形象和族群身份的想象。舞臺化的存在方式使文化擁有者黑衣壯居民重新反思、建構自己的文化,從而為自己確定新的文化身份和認同標準。[42]王良范以黔東南苗族為例探討了現代轉型下的文化認同問題。作者指出,現今黔東南的許多苗寨都把搞旅游作為一種掙錢的副業來操作,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恢復傳統的手工藝,將其商業化。傳統上那些只是供族群內部使用的東西,銀器、木梳、刺繡、蠟染、樂器,甚至工具等等,都成了同外部交換流通的旅游商品。在面臨現代化、全球化不斷深入滲透的現實面前,黔東南苗人也在努力地尋找同現代性融合的可能,也在接觸和接受現代性文化時努力地進行著自身文化的現代轉型。在這個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地方性的文化以及人民也在重新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43]
麻國慶通過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田野調查指出,文化認同雖然在現實的族群認同中起到重要的影響,但是,全球化的趨勢使得“文化傳統”的界定與內涵越來越難以把握,越來越具有流動性和再生產性,因此,應該更多的重視大眾文化與文化生產和少數民族族群認同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認為,在旅游等大眾文化事項的影響下,傳統文化往往成為了通過“有意識的創造”生產出來的大眾消費產品。在這一過程中,少數民族族群認同也會與更大規模的文化消費、地方社區的復興和開發戰略等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44]
族群認同是在族群互動過程中產生,群體間差異和群體互動是族群認同的基礎條件,民族旅游恰好為族群文化差異和族群互動提供了舞臺。[45]通過具有民族歷史價值和人文旅游景觀的再現和重組,一方面,少數民族展示了自身文化智慧和創造力,重新喚醒了本民族成員的歷史記憶,增強了內聚力。另一方面,處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獲得對它族文化的新認知,使這些長期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邊緣群體”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46]民族旅游引起的文化復興、族群認同,經歷了一個從變遷到重構的揚棄過程,伴隨旅游而來的文化商品化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在初期引起地方民族的迷茫,導致傳統失落,當地居民的認同感弱化,如民歌這種農業文明的文化現象與都市大眾文化結合,演變成為一種主要是表演性的民歌演藝活動時,民歌的文化認同功能被大大削弱了。[47]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文化調適之后,少數民族會在吸納外來文化基礎上推動著傳統文化的復興,形成民族文化的再造和創新。地方在這樣的再造與創新中強化了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48]
三、結語及進一步探討
文化認同在現代社會中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既有來自主流社會的建構,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認知。林特辛格 (Litzinger)指出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在社會話語和文化表述中往往被置于他者的邊緣化地位,主流話語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化與歷史的表述來建構國家的合法化,少數民族成員也在這一過程中被接納為國家的主人公,并得以反思本民族的歷史文化。[49]懷特 (White)以麗江納西族的族群認同為例指出,納西族精英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改造和重新解釋實際上是在官方話語的引導下進行的,但改造的成果被用來對納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使其更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最終達到維護和強化納西族在當地的族群社會中所占有的文化、政治、經濟優勢地位的目的。[50]懷特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當代中國民族傳統文化改造、展示其中隱含的話語轉型與博弈過程。這種方式啟示我們在對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的研究中,不能局限在哪一種話語對其文化的言說最具有真實性這一問題上,而是更為關注不同的話語在塑造少數民族及其文化過程中是如何產生、傳播、被接受、被否定、被改造的“博弈”過程,把注意力投放到不同的表述話語對民族的族群認同、自我的建構和生活意義的表述所起到的影響這一問題上。
在旅游發展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場景中,頻繁的人員流動和文化之間的交往接觸引起地方民族對我者和他者的文化判別。“我們是誰?來自何處?到何處去?”成為了地方族群界定自我身份的思量問題,進而形成對本民族的文化進行認同的實踐問題。在外來文化價值的影響下,是積極認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還是放棄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這是涉及到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大事。
那么,旅游發展引起的民族文化認同主要在哪些方面體現出來呢?筆者認為民族文化認同指的是由旅游發展引起的各種族群文化現象和活動,包括地方的傳統建筑、飲食服飾、傳統工藝等物質文化,還包括傳統儀式、節慶歌舞等具有表演性的行為層面的文化。涉及到人們如何通過對傳統文化有用性的經驗判斷來傳承發展民族文化,旅游者、精英與大眾在族群文化認同上如何實踐,旅游者和地方民眾在空間中的文化交換如何導致文化認同,本民族的成員在旅游中的文化認同的自覺或不自覺行為如何體現等等一系列問題。
[1]Hall,D.R.Stalinism and tourism:A study of Albania and North Kore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sh,1990,17(1):36-54.
[2]Light,D.Dradula tourism in Romania: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tat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sh,2007,34(3):746-765.
[3]Light,D.gazing on communism:heritage tourism and post-communist identities in Germany,Hungary and Romania.Tourism geographies,2000,2(2):157-176.
[4]MacCannell,D.Reconstructed ethnicity:tour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ird world communiti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4,11 (3):374-391.
[5]Van.Den.Berghe,P.L.&Ochoa,J.F.Tourism and nativistic ideology in Cuzco,Peru.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1): 1-26.
[6]Eastman,C.M.Tourism in Kenya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Swahili.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22(1):172-185.
[7]Esman,M,R.Tourism as ethnic preservation The Cajuns of Louisian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4,11(3):451-467.
[8]Adams,V.Tourism and Sherpas,Nepal:reconstruction of reciprocit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19(2):234-249.
[9]瓦倫.L.史密斯.愛斯基摩人的旅游業:微觀模式與邊緣人.瓦倫.L.史密斯.東道主與游客:旅游人類學研究(第二版).張曉萍等譯.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62-89.
[10]麥基恩.走向旅游業的理論分析:巴厘島經濟的雙重性和內在文化變化.瓦倫.L.史密斯.東道主與游客:旅游人類學研究(第二版).張曉萍等譯.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128-148.
[11]Cuillier,D&Ross,S,D..Gambling with identity:Self-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 on Official Tribal Websites.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es.2007.18:197-219.
[12]Medina,L,K.Commoditizing culture:Tourism and Maya identit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sh.2003.30(2):353-368.
[13]Grunewald,R.D.A.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4):1004-1021.
[14]Karen,De,Bres;James,Davis.Celebrating group and place identity:A case study of a new regional festival.Tourism geographies.2001.3(3):326-337.
[15]Jamal,A.Retail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the interplay of retailing,ethnic identity and consumption.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2003,10:1-11.
[16]Jamison,D.Tourism and ethnic:the brotherhood coconu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4):944-967.
[17]Gamper,J.A.Tourism in Austria a cas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on ethnic relation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1,8(3): 432-446.
[18]彭兆榮.旅游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62-263.
[19]Smith,V.L.Tourism and culture change:A symposiu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6.3(4):122-126.
[20]杰西卡·安德森·特納.楊麗慧譯.旅游景點的文化表演之研究.人文講壇.2004(1):6-11,17.
[21]Connell,J.Island dreaming:the contemplation of Polynesian Paradise.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03,29(4):554-581.[22]Grunewald,R.D.A.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4):1004-1021.
[23]Joseph,C.A.&Kavoori,A.P.Mediated resistanced:Tourism and the Host communit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4): 998-1009.
[24]Van.Den.Berghe,P.L.Tourism and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2.19(2):234-249.
[25]Evans,N.H.Tourism and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6.3(4):189-198.
[26]Wood,R.E.Ethnic tourism,the state,and cultur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4,11(3):353-374.
[27]Jamison,D.Tourism and ethnic:the brotherhood coconu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4):944-967.
[28]Graburn,N.H.H.The evolution of tourist ar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4.11(3):393-419.
[29]Toops,S.Xinjiang’s handicraft industry.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3.20(1):88-106.
[30]Boynton,L.L.The effect of tourism on Amish quilting design.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6.13(3):451-465.
[31]Swain,M.B.Women producers of ethnic art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3.20(1):32-51.
[32]Nason,J.D.Tourism,handicrafts,and ethnic identity in Micronesi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4.11(3):421-449.
[33]Marion C.Markwick.Tou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dicraft product in the Maltese islands.Tourism geographies.2001.3(1): 29-51.
[34]徐新建.人類學眼光:旅游與中國社會——以一次旅游與人類學國際研討會為個案的評述和分析.旅游學刊.2000(2):62-69.
[35]徐新建.開發中國:“民族旅游”與“旅游民族”形成與影響——以“穿青人”、“銀水寨”、“藏羌寨”為案例的評述.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21(7):1-9.
[36][39]楊慧.民族旅游與民族認同、傳統文化復興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開發中的“族群”及其應用泛化的檢討.思想戰線.2003.29(1):41-44,79.
[37][44]麻國慶.全球化:文化生產與文化認同——族群、地方社會與跨國文化圈.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37 (4):152-161.
[38]張波.論旅游對接待地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云南麗江為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1(4):68-71.
[40]Chao,Emily.Hegemony,Agency,and Re-presenting the Past:the Invention of Dongba Culture among the Naxi of SouthWest China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Melissa Brown.ed.1996.pp 208-239.
[41]Cheuang,Siu-Woo: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uizhou,In Brown,Mslissa J.eds.: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240-273.
[42]海力波.“做”黑衣壯:認同歷史與文化表征.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43]王良范.文化復興與文化認同——黔東南苗族文化的變遷與現代轉型.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7(1):103-107.
[45]白楊.旅游視野下的壯族族群認同.百色學院學報,2006,19(5):23-25.
[46]黃福東.旅游人類學與中國現實的有關理論淺述.廣西民族研究,2005,79(1):48-57.
[47]王杰.民歌與當代大眾文化——全球化語境中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及其重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8(6):64-68.
[48]曹慧中.民族認同與民族旅游.民族論壇,2007(4):18-19.
[49]Litzinger,R.A.Contend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In Harrell,S.eds.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117-139.
[50]White,S.D.State Discourses,Minority Policies,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he Lijiang Naxi People’s Autonomous Country,In Safran,W.eds.Nationalism and ethnoregional identities in China.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1998.9-27.
〔責任編輯:邵志忠〕
Review on The Ethnic Tourism With Cultural Identity
Wu Qifu
F59,G03
A
1004-454X(2011)01-0191-008
*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多元文化研究中心課題“中心與邊緣互動下的民族文化認同研究——以羌族旅游開發為例”項目 (編號:DYWH1012)。
【作 者】吳其付,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博士。四川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