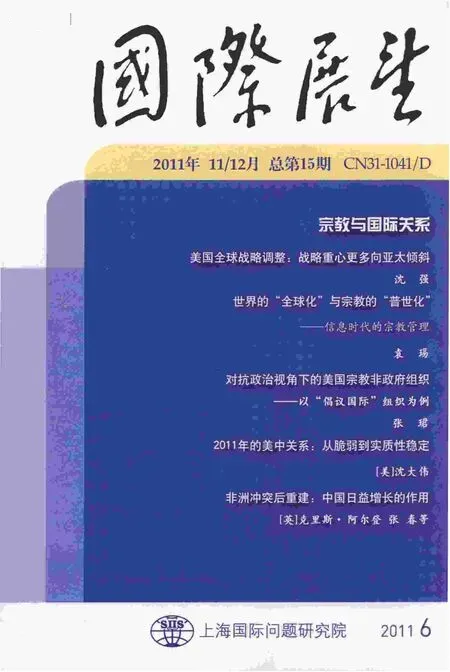非洲沖突后重建:中國日益增長的作用
克里斯?阿爾登 張春 貝爾納多?馬里亞尼 丹尼爾?拉吉
非洲沖突后重建:中國日益增長的作用
克里斯?阿爾登 張春 貝爾納多?馬里亞尼 丹尼爾?拉吉
隨著中非關系的快速發展,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正從促進向著保護的方向發展,這與非洲安全面臨的挑戰和國際體系轉型的壓力一道,呼吁著中國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已通過派遣維和部隊、提供沖突后重建投資及其他支持活動,為非洲沖突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盡管如此,由于多重不確定性的存在,中國未來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作用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 非洲 沖突后重建 作用
冷戰結束以來,中非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更多地反映了當代經濟全球化的重大歷史趨勢,放棄了既往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深化的貿易和投資關系是這一變化的重要動因。盡管經濟合作是且將繼續是中非關系的優先考慮,但中國正日益參與到非洲大陸的沖突與不安全因素的應對中,①Saferworld,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Saferworld: London,2010).特別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沖突后重建事務中。這一介入正日漸積極且某種程度上比過去更為靈活。
既有文獻往往認為,沖突后重建是指從國家失敗或國家崩潰中恢復過來。它們認為,沖突后重建和國家締造的障礙涉及諸多相互聯系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通過對失敗國家、國際組織參與的性質、安全、良治及基礎設施投資等問題的專門性界定,可能顯現出一幅有關沖突后重建和國家締造的清晰圖景。②有關沖突后重建的界定,可參見 Pierre Englebert and Denis M. Tull,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 Flawed Ideas about Fail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No. 4 (Spring 2008), pp. 106-139; S. Barakat and S. Zcyk, “The Evolution of Post-war Recove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6 (2009); S. Barakat ed., After the Conflict: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London: I.B. Tauris, 2005)等。本文的作者們并不嘗試采取這一略顯寬泛的方法,而是采取一種更為狹義的沖突后重建界定,即一國從長期沖突中恢復過來,實現穩定、和平與經濟發展。隨著國際體系轉型背景下的中國崛起和中非關系發展,中國正面臨著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的重大壓力和挑戰。
一、中國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的動因
20世紀末以來,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逐漸從先前主要關注發達國家轉向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非洲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地區,其標志是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的建立。③Kerry Brown and Zhang Chun, “China in Africa – Preparing for the Next Forum for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Chatham House Briefing Note, June 2009, pp. 5-6.此后,中國全面重返非洲并在諸多新領域發揮其影響力,沖突后重建便是其中之一。目前,中國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作用遠比過去更為重大,其動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非洲與國際體系的變化,也包括中國在非洲的國家利益的拓展。
首先,非洲所面臨的安全挑戰正從沖突和內戰轉向沖突后重建。
今天的非洲遠比十年前更為和平。應當承認的是,在克服沖突與不安全的雙重挑戰方面,非洲確已取得重大成就。盡管仍有不少沖突在繼續,但非洲的安全挑戰已從20世紀最后十年的戰爭與沖突,轉向進入21世紀后的沖突后重建。
隨著冷戰結束,非洲得以從兩極體系的主導中解放出來。這既解放了政府力量,也解放了非政府或者說叛軍力量,結果是使沖突成為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主要特征。如同一位著名非洲研究學者所總結的,“由于受稅入減少及對其權力的武裝挑戰的擴散而導致的非洲國家管轄能力下降,使得這類(沖突)地區的數量和規模得以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創造了一種新的無國家的國際關系”。①Christopher Clapham,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2.
1999年,非洲53個國家中有16個陷入了武裝沖突,大多數都不符合經典的國家間戰爭的界定。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非洲便飽受由相互聯系的戰爭形成的毀滅群的破壞。這樣的毀滅群有三個,分別是西部非洲——在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幾內亞和科特迪瓦都有戰爭或沖突;大非洲之角——在乍得、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索馬里和蘇丹有戰爭或沖突;大湖地區——盧旺達、布隆迪、扎伊爾/剛果(金)及烏干達陷入戰亂。這些沖突的絕大多數死傷者是婦女和兒童,且更多是由于戰亂導致的疾病和營養不良致死的。②Paul D. Williams, “Africa’s Challenges, America’s Choice,” in Robert R. Tomes, Angela Sapp Mancini, james T. Kirkhope eds., Crossroads Africa: Perspectives on U.S.-China-Africa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D.C.: Council for Emerging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2009), p. 37.
進入 21世紀后,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非洲結束了大多數戰爭和沖突。大多數先前飽受戰爭困擾的國家現在都將目光轉向國家重建,即本文所討論的沖突后重建。但這一任務仍困難重重。武裝沖突仍在少數國家繼續,其中最為著名的包括索馬里、剛果(金)和蘇丹,長期的、周期性的沖突導致了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后果和巨大的經濟代價。在其他國家,沖突后百廢待舉的環境使各種不安全因素隨時可能死灰復燃,而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亞等國的動蕩又為北非地區穩定帶來新的壓力。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地方性和社區性的暴力和低烈度的動亂及政治性暴力的頻率都非常之高,使人不得不為之警惕。
其次,中國在非洲的國家利益正從促進轉變為保護。
隨著中國在非洲利益的拓展,非洲的和平與安全對中國來說也日益重要。可以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已經從幾年前的利益拓展,逐漸向著利益保護的方向發展。
能源安全便是典型。2009年,非洲對中國的石油出口占到了中非貿易總額的60%。①并非只是中國這樣。2008年,石油占到美國從非洲進口總額的80%,美國是非洲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參見Standard Bank, “China and the US in Africa: Measur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Beijing’s Commercial Advance,” Standard Bank Economic Strategy Paper, 2011; Standard Bank, “Oil Price to Remain at Two-and-a-half-year Peak,”Standard Bank Press Release, 21st February 2011。如同其他國家在非洲的石油公司所面臨的情況一樣,中國在非洲的石油設施和石油工人也日益成為多個國家的非政府武裝的攻擊目標,如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和蘇丹。盡管大多數非洲石油出口國的沖突并不會導致全球石油市場的重大波動,但利比亞的沖突的確有這樣的效果。在卡扎菲下臺之前,中國從利比亞的石油進口占其石油總進口的3%。②The Economist, “Relying on Libya,” The Economist Daily Chart, 25th February 2011,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2/libyan_oil.因此,利比亞的動蕩相當明確地表明,中國追求能源安全的全球戰略使其不得不直接面對當地的不安全因素。
在能源安全之外,非洲的和平與安全也影響到中國其他方面的國家利益。利比亞動蕩發生后,在利工作的3.5萬名中國人不得不通過陸路和海路撤離,這類大規模行動將構成中國的又一新型挑戰。③AFP, “China Says 36,000 Evacuated from Libya,” Agence-France Presse, 2nd March 2011.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中國公民也經常遭遇暴力,如被索馬里海域的海盜所劫持。為數量日益增長的中國公民提供海外保護,正日益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關切。
盡管資源的穩定輸入相當重要,其他經貿利益也同樣重要。例如,中國在利比亞有75家公司承擔著價值188億美元的合同,占到2009年中國全球項目承擔總額的4.6%。①“Premature for Chinese Firms to Go Back to Libya,” China Daily, 30th August 2011;“Chinese Investments Face Low Risk from Libyan Rebels,” China Daily, 4th September 2011.有人預測,中非貿易到2015年將在201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達到 3000億美元,對非投資也將再增長 70%達到500億美元。②“China’s Investment to Africa to Increase to $50 billion by 2015, Bank Says,” Bloomberg News, 22nd February 2011.日益深化的經濟關系不只是意味著獲得非洲的自然資源,還意味著非洲日益增長的消費市場——這里擁有甚至比印度還要多的中產階級。③Standard Bank, “China and the US in Africa: Measuring Washington’s Response to Beijing’s Commercial Advance,” Standard Bank Economic Strategy Paper, 2011, p 5.但如同其他地方一樣,非洲超過10億的市場潛力,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其未來穩定與否。
第三,“安全—發展關聯”(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的新近發展。
冷戰時期,安全與發展完全是分裂的,被制度化為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的目標和手段的“政策領域”。甚至可以認為,冷戰實現了對發展與安全的一種宏觀上的地理分工,即發展指涉南北方關系,而安全指涉東西方關系。④See Geir Lundestad,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根據這一地理分工,世界政治被制度化為兩個不同的領域,它們的關切和政策手段也差異巨大,導致了一種概念上和政治上的分工,即一方面是所謂“發展研究”,⑤Frederick Cooper and Randall Packard e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ssays on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Knowled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而另一方面則是“安全研究”,⑥Pinar Bilgin and Adam. D. Morton, “Historicisinng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ailed States’:Beyo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No. 1 (2002), pp. 55-80.它們有著各自政策領域的不同機構。
自冷戰結束以來,這一局面已然發生重大變化。世界上最窮地區長期持續的沖突既使發展努力大為受挫,也激發了一種整合安全與發展的渴望。現在,安全與發展關切已經日益相互聯系。各國政府和各國際機構都聲稱,在介入沖突后局勢及與失敗國家或潛在的失敗國家的關系中,它們更為重視整合安全與發展計劃的必要性。就其行為體、機構及政策倡議而言,先前相互隔絕的兩個政策領域正日益相互交叉。如同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在21世紀,所有國家和國際機制必須促進更大的自由——通過確保免于匱乏、免于恐懼和有尊嚴的生活。在一個日益相互聯系的世界,發展、安全和人權領域的進步必須齊頭并進。因此,沒有發展,我們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我們就無法享有發展;不尊重人權和法治,我們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發展”。①“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New York, N.Y., United States: United Nations, 21 March 2005,http://www.un.org/largerfreedom/contents.htm.這樣,“安全—發展關聯”概念便被作為一種對非西方國家的單個國家或國際性干預的邏輯一致的方法而受到歡迎。
需要指出的是,新近的趨勢卻是更多強調安全,而非發展。全球化時代的安全因2001年“9·11”事件而有了新的含義。傳統的安全觀念在這一時期得以全面評估和演變。在整個安全光譜上,新的國際標準正不斷確立,特別是如邊境控制——移民和關稅及海上和空中安全等。基于這一邏輯,安全以一種特殊方式被融入發展話語,用安南在2001年《預防武裝沖突報告》中的話來說,是創造了“專門聚焦于沖突預防的新一代發展工程”。②“Prevention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 A/55/98 5-S/2001/574, 7 June 2001, http://www.reliefweb.int/library/documents/2001/un-conflprev-07jun.htm.
二、中國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的成就
盡管有多種評估沖突后重建努力的方法,但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2002年《沖突后重建框架》(Post Conflict Reconstruction Framework)報告提出的標準仍是最為重要的。該報告界定了“從暴力沖突停止到回歸正常”之間采取行動的三個階段,也即沖突后重建努力的三個階段:起步階段(initial response phase)始于廣泛的暴力結束之際,其特征是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服務,通過穩定行動和軍事干涉提供基本安全,其中包括部署維和人員;在轉型或過渡階段(transformation or transition phase),合法的地方能力產生并得到支持,其關注重點是重啟經濟發展,包括物質上的重建,確保有效的治理和管轄,并為提供諸如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社會福利奠定基礎;最終階段即鞏固可持續發展階段(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phase),鞏固先前的恢復性努力以預防沖突再次爆發。在這一階段,軍事行為體特別是國際維和人員逐漸退出社會和政治舞臺,社會重歸“正常”。①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Task Framework Report (Washington, D.C.: CSIS, May 2002), http://csis.org/images/stories/pcr/framework.pdf.
根據這一標準,中國目前在非洲的沖突后重建努力主要屬于前兩個階段,大致可分為3類。
第一,中國向幾乎所有聯合國涉非洲的維和行動派出了維和人員。
自2000年起,中國向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提供的維和人員增長了近20倍。②Bates Gill &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build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No. 25, 2009.中國維和部隊主要部署在非洲,幫助解決非洲大陸最為持久的和平與安全挑戰。中國向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剛果(金)、科特迪瓦、布隆迪、蘇丹、西撒哈拉、埃塞俄比亞及厄立特里亞等地派駐了維和人員。根據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目前中國在非洲參與了所有7個維和行動,派出1500多名維和人員,是5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表一)。
迄今為止,中國并沒有派出任何作戰部隊參加維和行動,中國派出的維和人員要么是軍事觀察員,要么是民事警察,要么是占據維和人員絕大多數的支持性力量,如工兵部隊、醫療隊等。例如,中國派駐剛果(金)參加聯剛特派團的維和人員位居中國派駐非洲維和行動的第三位,包括16位軍事觀察員和218名維和士兵。在維和士兵中,175名為工兵部隊,其余 43名為醫療隊員。工兵部隊主要承擔如修路,修建直升機坪,建設倉儲設施等。中國不僅增加了對維和行動的人員支持,而且逐漸參與到維和行動的領導與決策中。
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中國對部署更為強大和更具野心的維和行動的支持力度正在上升。中國目前的立場與上世紀 70年代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中國甚至拒絕就維和行動的表決投票。盡管如此,中國對派出維和部隊仍堅持當事國同意的前提。考慮到有的政府已經喪失合法性,并可能無法代表沖突各方,這一立場將繼續與其他國家的立場相沖突。盡管中國可能懷疑傳統上主導這類干預的西方國家的方法,但其參與維和行動的潛在貢獻仍是巨大的。
第二,中國正積極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國家的經濟重建。
非洲在滿足中國經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追求資源安全的過程中,中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些國家的內部沖突。在類似尼日利亞等資源所有權存在高度爭議的地方,中國參與開采資源使其也成為沖突的一方,至少在那些覺得未能從資源收益中獲益的人看來是如此。出售到中國的資源收入有時被用于購買武器以繼續沖突,如在蘇丹。這樣,在反對派武裝看來,中國與政府當局有著密切聯系。更為寬泛地,資源收入使得非洲的新家長制政權得以繼續掌權并中飽私囊,導致國家陷入不安全的怪圈。當然,這一情形并非只有中國才面對。大量的西方和亞洲國家的公司也都在同樣不穩定的國家的資源部門運作,如同中國一樣,也深深地陷入當地內部沖突并為這些政權提供了財富。①See Saferworld,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n Peace and Security (Saferworld: London,2010), Chap. 10.
在長期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同時,中國也迅速成為非洲更加重要的發展伙伴。②中國還向非洲提供了數量日增的人道主義援助,包括那些正陷入沖突中的地區。例如,2011年8月,中國宣布將向索馬里提供價值70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人們總傾向于認為,發展援助無論如何都是好的,不管它是如何提供的,也不管它被提供給了誰。當然,發展援助在執行得好時無疑會產生積極效果,解決沖突根源并為持久和平作出貢獻。但有時,善意的發展項目可能惡化甚至誘發對稀缺資源的沖突和競爭。例如,在水資源稀缺地區,幫助修建大壩便可能導致沖突。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接觸為非洲的沖突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通過基礎設施援建項目。發展與沖突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一項研究,在1990年至2005年間,武裝沖突導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付出了總計約3000億美元的代價,這大致相當于同一時期非洲所得到的援助總量。①IANSA, Oxfam & Saferworld, Africa’s Missing Billions: International Arms Flows and the Cost of Armed Conflict (London: Oxfam Great Britain, 2007).通過與非洲的貿易、投資和發展合作,中國正為非洲的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要否定其積極意義是很難的,特別是在基礎設施被破壞、缺乏投資和就業機會的剛走出沖突的國家,中國的建設性作用更加明顯。
中國對沖突后國家穩定的強調,可從其對安哥拉和蘇丹這樣產油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援建中看到。在安哥拉,自2004年底起,中國金融機構提供了高達 45億美元的信貸以支持該國公路、鐵路和住房等的重建和擴建。②Ana Cristina Alves, “The Oil Factor in Sino-Angolan Relations at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SAIIA Occasional Paper 55, February 2010, p. 12.在蘇丹,來自中國的貸款和投資也為石油工業及蘇丹成為石油出口國作出了重大貢獻,盡管石油業的發展本身在蘇丹南北內戰時期就已奠定基礎,且石油業的成功與達爾富爾沖突之間也存在關聯,使得中國的石油利益暴露在攻擊之下。③“Sudan Oil Minister Says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Fruitful,” Sudan Tribune, July 16, 2007,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22865.在這兩個案例中,增長的雙邊貿易、向其他工業部門的溢出、零售貿易增長及當地就業機會創造等都是中國日益參與其經濟的后果。中國的貢獻在其他不那么富有爭議的地方更易顯現。例如,中國對利比里亞飽受戰亂之苦的經濟的資助和投資據說在2010年達到了90億美元,盡管有20億美元涉及一項陷于停滯的礦產資源投資。④“China’s Investment Reaches $9.9 Billion,” The Informer (Monrovia), 26 April 2010.
第三,中國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安全支持。
中國正試圖將自身標榜為國際社會值得信賴的成員,而非洲則是中國塑造新興大國形象的重要舞臺。通過為非洲應對和平與安全挑戰的努力作出貢獻,中國期望被非洲和整個國際社會看做是承擔了部分大國責任,或至少被認為是在負責地行動。例如,中國官員和學者便往往這樣解釋中國對國際反海盜努力的貢獻。①Zhao Lei, “China’s International Peaceful Involvement Strategy and Anti-Piracy Effor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a-Africa Civil Society Forum on Peace and Development, Beijing,2-4 June 2010.又如,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中國幫助推動蘇丹政府、非盟和聯合國在2007年達成混合部隊進駐的共識。從2006年中起,中國政府便開始勸說蘇丹總統巴希爾改變立場。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和2007年2月訪問蘇丹時,胡錦濤都向巴希爾總統表達了中國對達爾富爾危機的關切,并希望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與非盟混合部隊的安排。②Gareth Evans and Donald Steinberg, “China and Darfur: ‘Signs of Transition’,” Guardian Unlimited, June 11, 2007, http://www.crisisgroup.org/home/index.cfm?id=4891&l=1.蘇丹政府于2007年中同意接受混合部隊。實現這一結果并不容易,中國的努力也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中國隨后向維和部隊貢獻了315名工兵部隊。
中國可能發揮更積極作用的一個潛在領域,是與非洲的地區和次地區和平架構的關系。隨著非盟和次地區組織通過非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非洲常備軍等機制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非洲的多邊政治圖景在過去十年里發生了許多變化。盡管仍面臨能力不足、資源有限及有時政治意愿不充分等問題,但地區和次地區性機制的作用和影響力仍在緩慢上升。中國正逐漸與這些機制接觸,并為其維和行動提供了一定的財政支持。例如,中國曾向非盟在蘇丹的維和行動提供了180萬美元資助,向非盟索馬里和西非地區的和平基金等也提供了一定的資助。
三、中國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的未來發展
中國未來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角色,不僅受中國自身的政策影響,還受非洲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具體而言,以下五個因素將重大影響中國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可能角色。
第一,投資重點:“硬”基礎設施抑或“軟”基礎設施?
中國已與多個非洲國家就沖突后重建簽署了以資源換基礎設施投資的合同,如蘇丹、安哥拉、剛果(金)和阿爾及利亞。其基本方式是通過兩份相互聯系的投資合同實現以自然資源換取國家基礎設施援建,包括一份資源(礦產或石油)合同和一份基礎設施合同。兩份投資合同的關系是開采自然資源,出口這些資源到中國,然后用資源出口收入資助這些受戰亂破壞的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非洲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幾乎全都屬于“硬”基礎設施,即公路、鐵路、橋梁、住房等。一國諸如公路、用水、電力及學校等基本基礎設施的建設,對于發展該國經濟來說至關重要。①Hafizullah Emadi, “Nation-building in Afghanistan,” The Gale Group, Contemporary Review Ltd, 2003, pp. 6-9.如果沒有基礎設施的支撐,該國及其公民便無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并將依賴于外國的財政和專家援助。
但世界銀行更為強調沖突后重建的社會層次“軟”基礎設施的投資。根據世界銀行的觀點,沖突后重建有兩個總體目標:促進敵對結束后向可持續的和平轉變,支持經濟和社會發展。在修復物質性的基礎設施之外,需要聚焦于向關鍵性生產部門、良治、重建關鍵性社會框架及正常化金融借貸安排等領域的投資。應當指出的是,世界銀行認為,沖突后重建“并不僅指物質性基礎設施的重建,也不必然意味著……沖突前存在的社會—經濟框架體系的重建”。②World bank,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8), p. 14.
進而,中國未來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作用面臨一個根本性挑戰,即是否需要轉向“軟”基礎設施的投資。如果轉型,則中國可能不僅會喪失傳統優勢——即在西方所不愿投資的“硬”基礎設施領域幫助非洲,還可能與發達國家陷入新的競爭。如果不轉型,則發達國家將利用某些“軟”國際法或“軟”國際規則批評甚至迫使中國改變目前的做法。而中國走中間道路——即同時投資于“硬”和“軟”基礎設施——的可能性、潛在收益與成本等又有多大?
第二,參與行為體:政府抑或非政府行為體?
到目前為止,中國參與非洲沖突后重建仍主要是政府性參與,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支持的公司或組織的參與。相對而言,私人或非政府行為體在這一領域難覓蹤影。但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都強調在沖突后重建的公私伙伴關系。如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說,“解決全球挑戰需要集體性和協調性的努力,涉及所有行為體。通過伙伴關系與聯盟,匯集比較優勢,我們能增加成功的機會”。
應當承認,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社會,都沒有準備好讓中國的公民社會參與到非洲的沖突后重建中去。中國會否允許更多的非政府組織和私有部門行為體參與到其在非洲的沖突后重建努力?考慮到中國公民社會的薄弱基礎,這些非政府組織和私有部門行為體的資源從何而來?最為重要的,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和私有部門行為體在參與國際關系后會產生什么樣的國際影響?
第三,參與方式:雙邊抑或多邊?
除派遣維和人員外,中國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參與絕大多數是雙邊性質的。眾所周知,中國外交始終堅持一項核心原則,即不干涉他國內政。很大程度上,這一原則阻止了中國在非洲沖突后重建努力中與國際多邊努力的合作。許多西方學者和決策者認為,中國對不干涉內政和尊重主權的解釋影響到治理模式及仍在持續的沖突,有時這種影響并非始終是積極的。
但近年來,中國在解釋不干涉內政原則時已經表現得更為靈活,在解決內部沖突時更愿意發揮積極的外交角色。如前所述,中國最終對喀土穆施加了重大外交壓力并迫使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與非盟混合部隊的部署。最新的例子可從有關利比亞的兩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看出。2011年 2月26日,中國投票支持安理會第1970號決議,允許對利比亞實施武器禁運,凍結利比亞資產,提交國際刑事法庭調查人道主義罪行,并明確提及保護的責任(R2P)——中國曾兩度表態支持這一聯合國原則。中國如此明確地支持制裁另一國對待其人民的方法,代表著中國政策的重大先例。3月17日,中國在安理會第1973號決議表決時卻投了棄權票,該決議授權成員國建立禁飛區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護遭受國家威脅的平民。對有的人來說,中國的確沒有否決第1973號決議,這標志著中國態度的進步。盡管中國過去只行使過6次否決權,但其中有2次是分別針對津巴布韋和緬甸的類似決議的。但中國隨后與其他國家一道,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羅斯,強烈譴責西方國家使用大量武力并呼吁停戰。很明顯,中國仍對應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人道主義干涉和使用武力懷疑態度。這一猶豫態度明顯體現在與利比亞過渡政府的關系處理上。盡管遵循不干涉內政原則,中國在北約采取武力后迅速與過渡政府建立了聯系。但與此同時,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承認過渡政府的步伐又是相對緩慢的。
這樣,要理解中國未來在非洲沖突后重建中的作用,必須關注中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的演變。事實上,這是一把雙刃劍。中國政策立場的逐漸演變可能對所有的利益攸關方來說都更好,無論是雙邊的還是多邊的。
第四,參與程度:深度介入抑或退出戰略?
中國仍有巨大的潛力,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到非洲的沖突后重建中。事實上,不少人都在呼吁中國更大程度的參與。例如,就與地區組織的合作而言,盡管中國可能仍難以提供其他大國那樣規模的財政支持,但與非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及次地區組織的相關機構就安全事務的制度化對話,將使中國找到其他提供支持的方法。向非洲常備軍提供維和部隊訓練可能是其中之一。又如,中國將成為非洲各國政府的另一個發展援助來源,但促進沖突后國家和脆弱國家的發展的努力可能無果而終,如果安全挑戰持續動搖任何已取得的成就的話。因此,如果要使發展扎下跟和持續的話,應對安全問題具有根本重要性。
同樣與中非經貿關系相關的是,中國應當將沖突敏感原則置于發展援助的核心,無論是小型的援助項目還是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工程。就最低目標而言,確保援助不會影響沖突預防和和平締造是重要的。這要求對所有發展項目的背景及其可能影響仔細分析。在必要的地方,這可能還需要設法避免發展項目成為誘導沖突的要素。為分析當地局勢并形成風險消除的手段,中國應與當地的社區發生聯系,而非僅僅關注非洲各國首都的統治精英。
這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沖突后重建努力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既非常復雜,又不可能在短期內見效。而且,期望一個深受暴力影響的社會在沒有持久的外部支持的情況下實現西方式民主治理、高度安全和經濟復蘇,可能是不現實的。①R. Picciotto and R. Weaving ed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vesting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6).進而,這些支持重建的努力將在何時終結?換句話說,中國何時才會從這一進程中退出,是在對象國能實現其穩定與和平還是經濟繁榮的時候?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中國維和人員何時真正撤走且中國投資不再支持沖突后重建而是轉向支持當地可持續發展,意味著經濟考慮的重大變化。與退出戰略相聯系的挑戰相當復雜,且并非中國所獨自面臨,整個國際社會都面臨這一問題。
最后,貢獻:物質性抑或理論性?
沖突后重建是一個涉及多元行為體、議程和使命的復雜過程。其寬泛的目標包括改革、重建和復蘇,都不可能在真空中發生,而是在其自身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特性導致的足以影響重建過程的諸多挑戰不斷變幻的環境中發生的。通過派遣維和人員、提供重建投資及其他支持行動,中國已經為非洲沖突后重建作出了重大的物質性貢獻。
但中國參與非洲的沖突后重建有何理論性貢獻?換句話說,中國參與沖突后重建的區別性特征是什么?作者以為,至少需要指出兩點。
一方面,中國是如何平衡不干涉內政與國際責任的。以發展援助為例,中國與西方國家對于援助的最佳發放方式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因此,很多人呼吁二者之間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對話與合作,以便研究這些差異,實現共同目標,并克服共同面臨的失敗。在當今的多極世界中,對于更多國家合作以應對集體性責任的需求相當緊迫。但在此之前,必須識別出不同方法的比較優勢。就不干涉內政與國際責任或主權與外部支持的平衡而言,作者認為,非洲各國政府、領導人及公民社會是解決沖突與不安全的首要責任人,外部行為體只能發揮次等的支持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是如何平衡“安全—發展關聯”的。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強調安全第一,但基于自身改革開放 30余年的經歷,中國更多強調發展第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因“文化大革命”而極端不穩定,正是發展第一的方法拯救了中國,消除了重大的不安全與動蕩因素,成長為今天的全球性大國。即便在許多西方學者、觀察家和決策者認為促進發展的努力在安全挑戰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將可能是無用功,中國仍堅持發展第一的方法,相信通過發展能實現安全。與此同時,中國也更加關注這一關聯,牢記安南有關“沒有發展,我們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我們就無法享有發展”的言論,同時也高度警惕西方安全第一方法背后的民主化前提。
克里斯?阿爾登(Chris Alden),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高級講師,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中非項目主任;張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貝爾納多?馬里亞尼(Bernardo Mariani),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中國項目主管;丹尼爾?拉吉(Daniel Large),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講師,皇家非洲學會亞非中心副主任
No. 1 (2002), pp. 5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