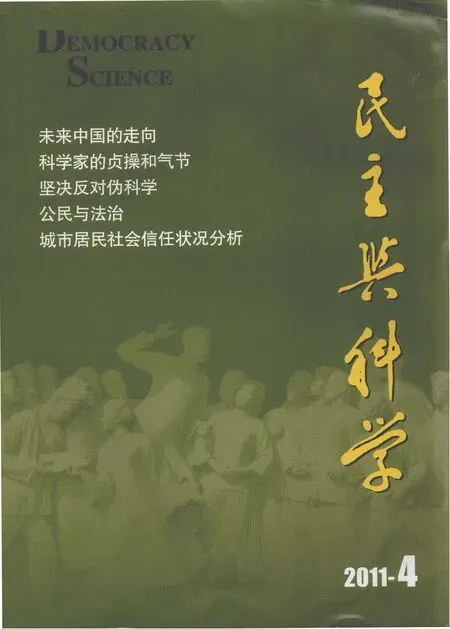“打倒知識”及其他
——讀史札記三則
■李 喬
“打倒知識”及其他
——讀史札記三則
■李 喬
“打倒知識!”
打倒知識,乃至打倒知識分子,是近現代革命史中痛苦而荒唐的一頁。這是極“左”革命派的行為。新見幾條典型史料,頗珍貴,錄之如下。
其一,“打倒知識”和“打倒知識分子”的口號。李銳同志發表在《炎黃春秋》的一篇文章,披露北伐軍曾提出過一個口號:“打倒知識!”讀后頗為驚詫。北伐就北伐吧,對象是軍閥,干嘛要打倒知識?難道知識與軍閥同樣壞嗎?北伐軍當然會有自己的解釋,但怎么解釋,北伐革命也不能這么搞呀。
讀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記:
讀今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黨史信息報》,有一篇標題為《打倒知識分子的標語》的報導。內稱,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毛澤東在瑞金的葉坪村一個住戶門口,看見貼著一張綠紙標語,上面寫著“打倒知識分子”。接著記者寫道:“原來葉坪村農民非常憤恨本村一位經常幫助地主欺壓群眾,教過幾年私塾的先生,由此對知識分子產生了惡感,視他們為被打倒的對象。這標語是鄉蘇維埃政府安排文書老謝寫的。”案:上面雖也舉出一種原因,但這問題似應作進一步探討。如:為什么農民一方面尊重字紙,一方面又討厭知識分子?為什么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多歧視知識分子?等等。
毛澤東對這條標語有何評論,不詳。這條標語,是我見到的最明確地提出打倒知識分子這一主張的材料。因為一個讀過書的人的惡行,便上升到要打倒整個讀書人階層(知識分子)的高度,這種抽象能力恐怕不會是貼著綠紙標語的那戶農家所能想得出來的。“這標語是鄉蘇維埃政府安排文書老謝寫的”——根子在此,這是當時黨的“左”的思想的產物。王元化先生提出要進一步探討農民對知識分子態度,此問題提得深刻。我黨對知識分子曾有的“左”的認識和政策,便與黨員的成分多是農民出身有關啊!
其二,按識字多少“肅反”。這是張國燾“肅反”中的發明。羅學蓬《張國燾川北蘇區“肅反”紀實》一文披露:“(為執行張國燾“肅反”方針)更為荒唐的是,有的保衛干部竟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繭巴、皮膚黑白來判斷好人壞人,連上衣口袋別鋼筆的人也不幸成了肅反對象。”(《同舟共進》2010年12期)識字成了原罪,別鋼筆便是罪證,有知識即有罪。張國燾完全不拿知識分子當自己人,而是懷疑之,歧視之,甚至干脆當敵人看。
對張國燾這樣對待知識分子,徐向前在《歷史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中也有披露:“肅反對象主要是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行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天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在這個排列中,“知識”與“白軍”和“地富”是同等看待的。所謂“從白軍過來的”、“地富出身的”,若是硬性地說,還多少算與“反動陣營”有一點兒瓜葛——盡管這樣審查也不對,太“左”;但當知識分子當學生有何辜呢?何況這些知識分子都是舍家舍命來投奔紅軍的。但就是因為他們讀過幾天書,有點兒知識,就成了被懷疑為反革命的疑點,甚至成了罪孽,便要“重則殺頭,輕則清洗”。徐向前對這種搞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張國燾便讓人又暗地調查徐向前。
其三,殺有知識的人。這是一條紅色高棉的史料。劉軍《越南柬埔寨兩國見聞》一文寫道:紅色高棉認為工商業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溫床,知識和財富是導致不平等的原因,所以,不惜毀滅城市和工商業,在肉體上消滅知識分子和資產者。在柬華人中有知識、有財產的人比例較高,所以受迫害更為嚴重。城里人被趕到鄉下時曾填過登記表,紅色高棉的人便按登記表談話,晚上趕著牛車到村里,接有知識或過去富裕的人去談話,一去不回。(刊于《百年潮》2010年12期)這是一段看似平淡而實則驚心動魄的記述。在紅色高棉的眼里,有知識必反動,知識越多越反動,故必鏟除之而后快。最可憐的是在柬埔寨的華人,他們知識多,財富多,所以紅色高棉對他們的殺心尤重。
其四,仇恨書籍,目讀書人為“妖”。這是太平天國所為。據《賊情匯纂》載:太平軍“凡擄人,每視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又據《平定粵匪紀略附記》載:太平軍“見書籍,恨如仇讎,目為妖書,必殘殺(持書人)而后快”。(轉引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手上無重繭者,多為讀書人,在太平軍眼里,他們都是妖孽,那些書籍,都是妖書。批林批孔時,曾盛贊洪秀全砸學塾里的孔夫子牌位。天王的部下仇恨書籍,目讀書人為“妖”,顯然與天王保持了高度一致。
張國燾的“肅反”,以識字多少、手上有無繭巴、皮膚黑白、口袋是否別鋼筆來判斷好人壞人,這與太平天國的識“妖”標準何其相似。“四人幫”的陰謀電影《決裂》,把手上的老繭作為錄取大學生的標準,這又與太平天國和張國燾何其相似。
用領袖的話糾正一種頑固心理
右,是反動的,左傾或“左”是革命的,而且越“左”越革命,“左”是與反動二字永不沾邊的——這是一種相當頑固的社會心理。這也是寧“左”勿右思想產生的一大原因。但實際上,“左”就一定不反動嗎?非也。還是看看革命領袖是怎么說的。
毛澤東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林蘊暉《國史札記·史論篇·毛澤東首創新民主主義》第6頁)這里沒提“左”字,但實際上否定的就是“左”,那種“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不就是“左”嗎?毛明確地說,這是反動的。
張聞天在1948年7月東北局召開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聯席會議上說:“今天鞏固農民的這種私有財產權,應該說具有進步的意義,破壞這種私有財產權,才是反動的思想。在今天的條件下,就要實行共產主義,實質上是倒退的,破壞性的,是反動的。”(同上,第11頁,引自《張聞天文集》第4卷)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就要破壞私有財產權,就要實行共產主義,無疑是“左”的。這種“左”,張聞天明確地說,“是反動的思想”,“是反動的”。
劉少奇在1951年5月在政協全國委員會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說:現在傷害私人工業家和小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會起破壞作用,這是反動的,就是所謂“左”的錯誤。因為它破壞生產積極性,妨礙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說過:空想的社會主義是反動的,錯誤的。我們曾經反對過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下過這樣一個結論,說它的性質是反動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所以現在過早采取社會主義步驟,過早的國有化,集體化,是違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是違背進步的。(同上,第33頁)在這段話里,劉少奇明確地將“左”與反動并提,與違背進步并提。違背進步也就是反動。總括劉少奇的結論,就是:在當時,傷害私人工業家和小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就是反動的,搞農業社會主義就是反動的。這個結論,完全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所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是反動的,也把“左”的主張與“反動”掛了鉤。“空想的社會主義”就是“左”的主張。
“社會主義”一詞,在《共產黨宣言》時代是一個左翼名詞,但并非誰用這個名詞誰就一定是左翼,是革命的。《共產黨宣言》在談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時,批判了一種“反動的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三種。這一批判,將左翼名詞掩蓋下的反動事實揭露了出來。
上引革命領袖們的話所依據的都是歷史唯物主義,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不可妨礙和破壞生產力發展等原理。其實,說妨礙和破壞生產力之舉是反動的,是很好理解的,反動,就是反社會進步而動,妨礙和破壞生產力發展,不就是地道的反社會進步嗎?
革命領袖們的話提醒我們:絕不是越“左”越革命,“左”也可以是反動的。
當然,革命領袖在這里所論述的“反動”,主要是從理論意義的層面上說的,與所謂政治上的反動是有區別的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絕不應當用領袖的話去亂套,認為倘若誰認識上一旦違反了唯物史觀就成了反動分子。這是應當辨析清楚的。
落實《張魯傳》,路人白吃飯
一些史書這樣記載: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社員吃飯不要錢,許多食堂被吃垮了。這個記載基本準確,但也有一點不夠精確:來公共食堂吃飯的人,不僅僅有社員,還有不少過路人。人民日報老記者林晰在《親歷“大躍進”歲月》一文中曾披露了他所見到的一些公共食堂的情況:“由于高級領導人提倡‘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干活’,還為了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曾經大吃大喝過幾天,加上過路人‘吃飯不要錢’,使得食堂很快就無以為繼了。”(《書屋》2010年第12期)在公社食堂里大吃,是社員倒也罷了,過路人也來大吃,食堂哪能不垮掉呢?
眾所周知,社員吃飯不要錢,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的,但過路人吃飯不要錢,根據的是什么呢?有人說也是按毛主席指示辦的。究竟情況怎樣呢?
毛澤東為給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立論,曾從中國歷史上找根據。他找來了《三國志·張魯傳》,并根據其中一些記載寫了大段批示。《張魯傳》有這樣一段記載:張魯五斗米道“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這是說,張魯在大路上建了許多不花錢白住的公共旅社,旅社里又放上不要錢的米肉供過路人食用,而且管飽,但不許貪婪浪費。毛在批語里推測說,張魯這樣做似乎是為了招來關中區域的流民。又說,這表現了五斗米道的經濟綱領。毛的批語里有一句話極重要:“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毛看來,在義舍中置義米肉,不就是古代的公共食堂嗎?人民公社為何不可以沿著張魯的路子辦自己的公共食堂呢?
在讀毛的批語時,我們應當注意到,毛推薦《張魯傳》,實際上只是說了張魯開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先河,而并沒有說天下的行路人都可以到人民公社的食堂里隨便吃,他強調的實際主要是張魯的“義”,即吃住“不要錢”這一經濟思想,而不是任誰都可以到公社食堂來白吃。我家所在的西堂子胡同街道,受公社大辦食堂的影響,也辦過一個公共食堂,大人領我去吃過,但要付錢的。過路人隨便吃,是《張魯傳》里說的,并不是毛說的,毛只是翻譯了一下《張魯傳》,只是說張魯的做法是公社食堂的“先河”。但是,許多公社干部并不這樣想,他們一看到毛的批語,不管是毛本人的話,還是毛引用的材料,都一字一句地落實。于是,不僅落實了毛的社員吃飯不要錢的指示,連同張魯的“行路者量腹取足”也落實了。這實際也就是在落實五斗米道的經濟綱領了。但也很難怪公社干部們這樣做,試讀一下毛的批語,他把張魯的義舍義米肉與“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之類混在一起說,公社干部哪里分得清呢?
公社干部如此盲目搬用毛的批語,反映出他們對毛的個人崇拜之強烈。由此可以看到,早在“大躍進”年代,對毛的個人崇拜就已經具有堅實、廣泛的社會基礎了。這是后來的極端的個人崇拜的前奏。
對《錯誤就是錯誤》一文的補記
筆者寫完《錯誤就是錯誤》一文后(刊于《民主與科學》2011年第二期),讀到2008年4月23日《報刊文摘》轉載的一篇文章《封建劣根性的東西要改正——趙樸初的傳統文化觀》(原刊《民主》雜志同年第3期,作者梁紅星、沈鐵筠),該文介紹的趙樸初先生的一個觀點,正與本文的觀點相同。趙樸初先生的話當然更有分量和參考價值。為讓更多的讀者了解趙先生的觀點,茲移錄文中相關文字如下:“趙樸初認為,無論是做事,還是做人,反求諸己十分重要。他講到,一個團體,一個政黨,一個國家,遇到事情,應先查查自己,不要先去怪別人。正確與錯誤是矛盾的統一,錯誤就是錯誤,有錯就要改正,不應該用‘失誤’這個詞來掩蓋錯誤,掩蓋錯誤就是錯上加錯,應該學習并努力做到反求諸己。”這是明達之論、諍友之論,說得多么正確和深刻!“錯誤”與“失誤”二詞,詞義不同,顯而易見。趙樸初先生是大知識分子,故一望某些宣傳品以“失誤”二字替換“錯誤”,便自然深覺不妥,故有如上議論。
(作者單位:北京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