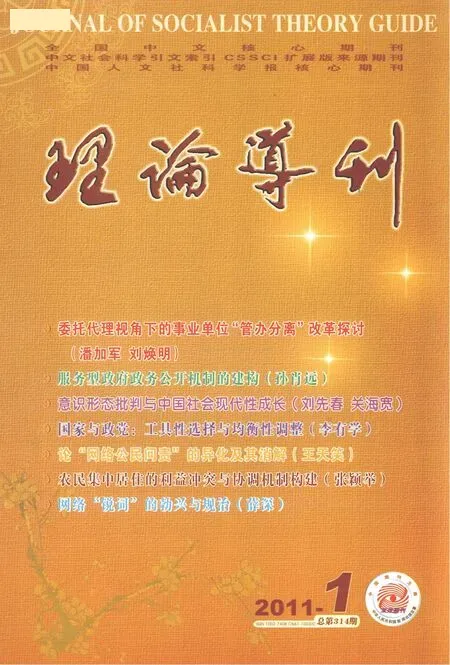論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
——一個(gè)基于行政生態(tài)的框架性考量
唐慶鵬,康麗麗
(南京師范大學(xué)泰州學(xué)院,江蘇泰州225300)
論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
——一個(gè)基于行政生態(tài)的框架性考量
唐慶鵬,康麗麗
(南京師范大學(xué)泰州學(xué)院,江蘇泰州225300)
整體性治理是一種新型的行政觀和行政方法論的統(tǒng)一,其實(shí)質(zhì)是為應(yīng)對(duì)外部行政生態(tài)的新發(fā)展,并基于對(duì)傳統(tǒng)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深刻反思,對(duì)政府內(nèi)部治理資源配置優(yōu)化的制度性再調(diào)整。要實(shí)現(xiàn)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必須對(duì)我國(guó)的現(xiàn)實(shí)行政生態(tài)有清晰的認(rèn)識(shí)。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態(tài)——理念——權(quán)力——職能機(jī)構(gòu)——手段”的改革路徑,逐步推進(jìn)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
整體性治理;行政生態(tài);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
“任何改革的嘗試都意味著人們對(duì)變革的期望,每一個(gè)新的模式本身就說(shuō)明了人們對(duì)政府部門存在的問(wèn)題的根源有一個(gè)清晰的認(rèn)識(shí)。”[1]自上世紀(jì)末興起的全球范圍的政府再造,正是對(duì)新時(shí)代變革及其所帶來(lái)的一系列政府治理問(wèn)題的回應(yīng)。整體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又稱整體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是上世紀(jì)90年代末由佩里·希克斯最早公開(kāi)表述論證,其后在一些新公共管理改革腹地國(guó)家,如英國(guó)、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開(kāi)始得到重視并在實(shí)踐中予以推廣,成為繼新公共管理改革后西方主要國(guó)家第二輪政府改革運(yùn)動(dòng)的主題。近年來(lái),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整體性治理的研究正逐漸興起。學(xué)者們做了大量富有啟發(fā)性的研究,但總體上看,學(xué)者們更多的傾向于把整體性治理視為從內(nèi)部技術(shù)的角度對(duì)政府的再造,即研究偏重于內(nèi)部取向。我們認(rèn)為對(duì)于整體性治理的研究不僅要從內(nèi)部取向進(jìn)行探索,更應(yīng)該關(guān)注外部取向的研究。因而,本文嘗試從行政生態(tài)的角度重新定位和闡釋整體性治理理論,并結(jié)合我國(guó)現(xiàn)階段行政生態(tài)探索推進(jìn)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路徑。
一、整體性治理模式的研究緣起及其范式價(jià)值的再解讀
整體性治理是如何興起的?最為直接的原因是公共事務(wù)發(fā)展的需要。從行政生態(tài)學(xué)來(lái)看,公共事務(wù)產(chǎn)生和發(fā)展?fàn)顩r取決于行政生態(tài)環(huán)境。行政生態(tài)是指圍繞政府系統(tǒng)的、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和作用于行政管理活動(dòng)的各種因素或條件的總和。[2]行政生態(tài)向行政系統(tǒng)提出不同形式的需要,構(gòu)成行政系統(tǒng)的資源、信息輸入,外部環(huán)境對(duì)行政系統(tǒng)提出的需求累計(jì)到一定程度則發(fā)展為公共需求或公共問(wèn)題;行政系統(tǒng)經(jīng)過(guò)組織內(nèi)部資源,輸出或生產(chǎn)決策計(jì)劃、法規(guī)措施等行政產(chǎn)品,以滿足和解決行政環(huán)境引致的公共需要和公共問(wèn)題。可見(jiàn),這種對(duì)內(nèi)組織治理資源以回應(yīng)公共需要和解決公共問(wèn)題的流程便構(gòu)成了整個(gè)政府公共事務(wù)管理過(guò)程。而政府治理模式的發(fā)展,也可視為是適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的需要而對(duì)內(nèi)部治理資源的再配置。
因而,政府的治理模式必然要根據(jù)環(huán)境的變化而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形成一種平衡關(guān)系。理論上,以理性官僚制為代表的傳統(tǒng)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是迄今被廣泛認(rèn)可的兩大基本政府治理模式。作為西方工業(yè)社會(huì)產(chǎn)物的官僚制,提倡理性化的思維,以嚴(yán)格等級(jí)制為組織基礎(chǔ),以采取指令式等非人格化的方式對(duì)政府內(nèi)部治理資源的配置為基本特征。20世紀(jì)下半葉以來(lái),社會(huì)生活秩序的深刻變遷,使得傳統(tǒng)的官僚制行政模式的現(xiàn)實(shí)合理性受到了廣泛的質(zhì)疑:“工業(yè)時(shí)代發(fā)展起來(lái)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guī)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tǒng),已不能有效運(yùn)轉(zhuǎn)。”[3]繼官僚制之后,新公共管理模式正是通過(guò)在公共部門中引入市場(chǎng)機(jī)制和私營(yíng)企業(yè)的組織模式與管理方法,重新優(yōu)化配置政府內(nèi)部治理資源,提高了公共部門的服務(wù)質(zhì)量,從而滿足公眾多樣化、個(gè)性化的需求。但新公共管理模式本身的治理資源分散化問(wèn)題凸顯,進(jìn)而衍生出諸如新的公共責(zé)任問(wèn)題、服務(wù)供給的分割化問(wèn)題、公共部門結(jié)構(gòu)性分化問(wèn)題等。正是基于對(duì)政府治理兩種主流模式的深刻反思,為適應(yīng)愈加復(fù)雜化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整體性治理的倡導(dǎo)者們呼喚政府治理整體主義的復(fù)興。
作為一種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整體性治理的發(fā)生有著內(nèi)在而深刻的邏輯機(jī)理,它是對(duì)政府內(nèi)部治理資源配置優(yōu)化的制度性再調(diào)整,是一種新型的政府治理觀和政府治理方法論的統(tǒng)一:首先,整體性治理提出了一種新型的治理觀。整體性治理強(qiáng)調(diào)服務(wù)對(duì)象、治理目標(biāo)以及社會(huì)問(wèn)題的完整性和有機(jī)關(guān)聯(lián)性,認(rèn)為政府的存在應(yīng)該為社會(huì)提供無(wú)縫隙服務(wù),實(shí)現(xiàn)公共服務(wù)的公平和正義。整體性治理回應(yīng)時(shí)代發(fā)展的需要,超越了傳統(tǒng)的強(qiáng)調(diào)威權(quán)統(tǒng)治的官僚制治理觀和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效率、效益”的新公共管理治理觀。其次,整體性治理強(qiáng)調(diào)整體主義的方法及信息技術(shù)手段再造政府治理。整體性治理的治理方法論不同于官僚制的行政命令——服從式的治理方式,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所推崇的市場(chǎng)契約、碎片化治理方式,而是轉(zhuǎn)而追尋政府治理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是“著眼于政府內(nèi)部機(jī)構(gòu)和部門的整體性運(yùn)作,主張管理從分散走向集中,從部分走向整體,從破碎走向整合”。[4]的整體主義方法應(yīng)用。同時(shí)十分重視政府治理手段的現(xiàn)代化、科學(xué)化、電子化,重視政府治理效率的提升。
二、整體性治理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與我國(guó)行政生態(tài)
政府治理的改革與發(fā)展必須基于現(xiàn)實(shí)行政生態(tài)的考量。整體性治理興起于西方國(guó)家,那么在我國(guó)推動(dòng)整體性治理是否同樣為現(xiàn)實(shí)之必要,又有哪些因素影響和制約整體性治理的制度創(chuàng)新?我們認(rèn)為當(dāng)前我國(guó)行政生態(tài)最大的特點(diǎn)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全面轉(zhuǎn)型。處于轉(zhuǎn)型期的行政生態(tài)主要表現(xiàn)為:政治秩序健康穩(wěn)定但政治系統(tǒng)不完善;經(jīng)濟(jì)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不成熟;社會(huì)在進(jìn)步但還不成熟;文化價(jià)值觀多元存在但缺乏明確主導(dǎo);科技進(jìn)步但應(yīng)用有限。隨著行政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斷變遷,我國(guó)傳統(tǒng)的公共管理模式與行政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沖突日益明顯,實(shí)然和應(yīng)然之間的張力成為我國(guó)推進(jìn)整體性治理制度創(chuàng)新的基本動(dòng)因和現(xiàn)實(shí)要求。
1.經(jīng)濟(jì)生態(tài)要求政府與市場(chǎng)的深度整合。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機(jī)制和生產(chǎn)發(fā)展水平是影響行政最主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因素。我國(guó)正在推進(jìn)中國(guó)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進(jìn)程。據(jù)有關(guān)學(xué)者研究測(cè)試,歐、美、日等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化程度為80%~90%,而我國(guó)市場(chǎng)化的總體程度在60%左右。[5]伴隨我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深入發(fā)展,一方面強(qiáng)化了政府與市場(chǎng)的橫向聯(lián)系,需要政府進(jìn)一步調(diào)整和完善與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另一方面也對(duì)政府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市場(chǎng)的本質(zhì)是社會(huì)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和發(fā)展要求政府具有較高的協(xié)調(diào)整合能力。其次,市場(chǎng)本身對(duì)效率的追求也要求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服務(wù),而政府可利用資源是有限的,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對(duì)有限的資源加以整合以有效回應(yīng)。最后,隨著我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當(dāng)前諸多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管理權(quán)力和服務(wù)功能正在向以行業(yè)協(xié)會(huì)為代表的社會(huì)和市場(chǎng)中介組織及其它非政府組織轉(zhuǎn)移,這就要求政府在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提供服務(wù)過(guò)程中,加強(qiáng)與市場(chǎng)中介組織的協(xié)調(diào)。
2.政治法治生態(tài)要求政府權(quán)力機(jī)制的再調(diào)整。建國(guó)以來(lái),我國(guó)逐步建立起了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即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多黨合作、政治協(xié)商制和人民代表大會(huì)制。這樣的制度架構(gòu)決定了我國(guó)的政治與行政不可機(jī)械割裂,所有行政行為都必須在政治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釋。但是,相對(duì)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改革的程度和廣度,我國(guó)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發(fā)展相對(duì)滯后。首先,權(quán)力機(jī)制有待進(jìn)一步完善。由于長(zhǎng)期以來(lái),我們把黨的領(lǐng)導(dǎo)變成了黨管一切,把黨的執(zhí)政變成了黨的直接行政,因而存在著黨政不分的現(xiàn)象;中央與地方權(quán)力分配并不均衡,地方之間職能界限不清,各自為政、以鄰為壑現(xiàn)象屢禁不止。其次,社會(huì)主義民主最本質(zhì)的內(nèi)涵是人民當(dāng)家作主,但受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不健全、傳統(tǒng)政治文化等因素限制,我國(guó)公民參政議政的水平和程度還有待進(jìn)一步提高。再次,政治生活的法治化程度不高,人治還一定程度存在,在相當(dāng)程度上成為政府治理制度創(chuàng)新的掣肘。
3.社會(huì)生態(tài)要求政府與社會(huì)有機(jī)鏈接。總體上看,中國(guó)社會(huì)正在遠(yuǎn)離傳統(tǒng)社會(huì)而向現(xiàn)代社會(huì)快速邁進(jìn),社會(huì)環(huán)境和諧穩(wěn)定,為政府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礎(chǔ)和條件。但由于我國(guó)社會(huì)正處于轉(zhuǎn)型時(shí)期,新的社會(huì)變遷也對(duì)政府治理提出新的挑戰(zhàn):(1)社會(huì)的階層分化日趨明顯。根據(jù)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的研究,我國(guó)目前存在著十大階層,每一個(gè)階層內(nèi)部都存在著復(fù)雜的亞階層,多樣性的擴(kuò)展意味著復(fù)雜性的增強(qiáng),因此,正確協(xié)調(diào)處理社會(huì)階層之間的利益關(guān)系,是政府在新世紀(jì)面臨的一項(xiàng)重大任務(wù);(2)“第三部門”逐漸興起但還不成熟。這些社會(huì)組織的逐步興起壯大,一定程度上有效分擔(dān)了政府治理職能,但同時(shí)我國(guó)第三部門發(fā)展還遠(yuǎn)未達(dá)到政府治理的需要。在西方政府治理改革的前沿國(guó)家,如德國(guó)每萬(wàn)人中社會(huì)組織已經(jīng)發(fā)展到120個(gè),法國(guó)110個(gè),而我國(guó)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最快最多的上海、青島等城市,每萬(wàn)人中才發(fā)展到6.5個(gè)和6.1個(gè)。[6]此外,我國(guó)相當(dāng)多的第三部門與政府部門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承擔(dān)著許多政府行政性事務(wù),缺乏獨(dú)立自治性,難以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服務(wù)、溝通和監(jiān)督的作用。(3)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不斷增加。整體性政府理念的興起部分地是由于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來(lái)臨。大多數(shù)國(guó)家政府相信組織間交流的協(xié)同工作能力是有效應(yīng)對(duì)災(zāi)難事故的重要因素。近年來(lái),我國(guó)自然災(zāi)害、生產(chǎn)事故、食品安全、生態(tài)環(huán)境、群體性事件等危機(jī)事件頻發(fā),“這一系列讓人無(wú)法喘息的亂象都可以一言以蔽之:我們已經(jīng)進(jìn)入了高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7]要求我們同樣要加強(qiáng)協(xié)同工作能力建設(shè)。
4.文化技術(shù)生態(tài)要求政府治理理念與技術(shù)的優(yōu)化。當(dāng)前我國(guó)外部行政文化生態(tài)呈現(xiàn)多元化特點(diǎn)。首先,我國(guó)公民具有較強(qiáng)的政治認(rèn)同感、政治信任感和良好的政治寬容精神,政府治理的資源動(dòng)員及調(diào)控組合較為容易,也使政府治理創(chuàng)新能夠在一種較為平和的氣氛中進(jìn)行;其次,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huì)的發(fā)展,社會(huì)日益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社會(huì)公眾主體的自我意識(shí)蘇醒,民主法治意識(shí)也逐漸增強(qiáng);再次,從整體上看,我國(guó)公民對(duì)自己的公民角色的認(rèn)知程度、政治能力感、效益感相對(duì)較弱,致使政府治理在實(shí)踐中屢屢遭到來(lái)自文化觀念的阻礙;最后,文化的多元發(fā)展同時(shí)也帶來(lái)一些不利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價(jià)值觀念異化。在部分官員中,公益觀念、服務(wù)宗旨在不同程度上被權(quán)力腐敗、官本位思想所淡化,公共權(quán)力部門化、部門權(quán)力利益化、部門利益?zhèn)€人化的現(xiàn)象比較突出,并造成很大危害。
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網(wǎng)絡(luò)與信息技術(shù)在塑造一個(gè)全新的社會(huì)形態(tài)——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與信息時(shí)代的同時(shí),對(duì)政府改革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并為之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技術(shù)支撐。登力維認(rèn)為,“信息系統(tǒng)幾十年來(lái)一直是形成公共行政變革的重要因素,政府信息技術(shù)成了當(dāng)代公共服務(wù)系統(tǒng)理性和現(xiàn)代化變革的中心。”[8]近年來(lái),我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迅速,2008年以來(lái)的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有三個(gè)量的突破,即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總量、寬帶用戶總量及國(guó)家頂級(jí)域名“cn”的數(shù)量均躍居世界第一,這顯示出我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不斷擴(kuò)大的社會(huì)影響力。伴隨著電子郵件和其他溝通技術(shù)的發(fā)展,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將跨越組織界限之間的伙伴溝通和合作變得更好、更快,也更廉價(jià)。與外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的欣欣向榮相比,我國(guó)政府信息化、網(wǎng)絡(luò)化程度較低。由于政府的信息資源長(zhǎng)期以來(lái)處于初級(jí)、簡(jiǎn)陋的管理狀態(tài),以及政府網(wǎng)上辦公在系統(tǒng)安全方面存在著諸多威脅與挑戰(zhàn),使政府的工作效率并沒(méi)有隨社會(huì)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得到應(yīng)有的提高。
三、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進(jìn)路建議
面對(duì)轉(zhuǎn)型期我國(guó)行政生態(tài)的特殊性,整體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創(chuàng)新需采取審慎態(tài)度。就整體性治理的制度創(chuàng)新路徑而言,我們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態(tài)——理念——權(quán)力——職能機(jī)構(gòu)——手段”的改革路徑來(lái)逐步推進(jìn)。
1.以整體服務(wù)為導(dǎo)向,轉(zhuǎn)變政府治理理念。整體性治理取向的政府再造要求遵從公民的整體需求,構(gòu)建服務(wù)型政府,因而推進(jìn)整體性治理必須從政府治理理念實(shí)現(xiàn)轉(zhuǎn)變:首先,以整體性思維審視政府治理存在的問(wèn)題。我們不能繼續(xù)秉持單一的行政思維看待政府治理存在的問(wèn)題,政府作為社會(huì)系統(tǒng)中的一個(gè)子系統(tǒng),許多問(wèn)題,表面上看在行政管理層面,但問(wèn)題的核心可能牽扯到諸如政治體制等外部生態(tài)的影響。其次,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取向從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會(huì)本位、公民本位轉(zhuǎn)變,注重公民需求的整體回應(yīng),增強(qiáng)服務(wù)型政府的公共服務(wù)能力。再次,在注重對(duì)正義、公平、責(zé)任性等民主價(jià)值的強(qiáng)調(diào)和對(duì)公民權(quán)利、人民主權(quán)和公共利益等多元價(jià)值的追求以充分體現(xiàn)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同時(shí),肯定對(duì)效率價(jià)值的追求,綜合平衡公平與效率的關(guān)系,做到“既注重效率,又注重公平”。
2.以憲政為前提,規(guī)范政府權(quán)力關(guān)系。整體性治理在權(quán)力運(yùn)作上不同于官僚制的集中權(quán)力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單位分權(quán),而是強(qiáng)調(diào)擴(kuò)大授權(quán),即并非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而是在分權(quán)基礎(chǔ)上的整合。但擴(kuò)大授權(quán)的前提是權(quán)力運(yùn)行環(huán)境是民主自由,否則將倒行逆施并有導(dǎo)致威權(quán)主義泛濫乃至打擊民眾的自由度的危險(xiǎn)。我國(guó)目前政治體制改革嚴(yán)重滯后于經(jīng)濟(jì)和行政體制改革,這就增大了今后政府權(quán)力調(diào)整的風(fēng)險(xiǎn)性。因而,政府機(jī)構(gòu)改革應(yīng)在憲政秩序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也只有在憲法的保障下進(jìn)行機(jī)構(gòu)改革,才能保障政府機(jī)構(gòu)的改革取得成功。[9]首先,整體性治理的制度創(chuàng)新并非可以隨心所欲地進(jìn)行,必須遵循憲法的規(guī)定和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基本原則。其次,進(jìn)一步完善公民權(quán)利保障機(jī)制,包括拓寬公民利益訴求渠道、創(chuàng)新公民參政議政機(jī)制等。再次,規(guī)范政府權(quán)力制約機(jī)制,包括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的制度化再調(diào)整,以形成建立健全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和運(yùn)行機(jī)制。最后,明確權(quán)力權(quán)利格局,形成黨委領(lǐng)導(dǎo)、人大監(jiān)督、政府負(fù)責(zé)、社會(huì)協(xié)同、公民參與的良性權(quán)力—權(quán)利格局。
3.以市場(chǎng)與社會(huì)為立足點(diǎn),梳理政府職能關(guān)系。加強(qiáng)政府職能的內(nèi)部整合,首先要立足市場(chǎng),整合政府與市場(chǎng)職能關(guān)系。整體性治理就是要準(zhǔn)確處理好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和政府調(diào)節(jié)的關(guān)系,其中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通過(guò)政策法規(guī)進(jìn)行必要的規(guī)制和有效的調(diào)控。整體性治理的政府應(yīng)更加側(cè)重以宏觀的角度對(duì)國(guó)家事務(wù)進(jìn)行管理,減少和避免政府部門對(duì)微觀經(jīng)濟(jì)的干預(yù)活動(dòng)。其次,培育公民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政府管理與社會(huì)自我管理的無(wú)縫隙銜接。整個(gè)社會(huì)管理是由政府職能和社會(huì)自我管理職能所組成的嚴(yán)密而完整的系統(tǒng),雙方圍繞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決定的職能范圍此消彼長(zhǎng)相互作用,各自發(fā)揮著應(yīng)有功能。[6]再次,在明確政府職能邊界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理順政府內(nèi)部各職能部門的關(guān)系,建立一種“組織規(guī)模大、職能范圍廣”的大部門體制,對(duì)相同或相近的政府職能進(jìn)行整合、歸并,綜合設(shè)置政府機(jī)構(gòu),健全部門間協(xié)調(diào)配合機(jī)制,從根本上解決機(jī)構(gòu)重疊、職責(zé)交叉、權(quán)限沖突、政出多門等問(wèn)題,最終建構(gòu)一種體現(xiàn)“整體政府”要求的權(quán)責(zé)一致、分工明確的組織架構(gòu)。
4.以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為手段,優(yōu)化政府治理水平。整體性治理改革是回應(yīng)現(xiàn)代信息社會(huì)的需要,是對(duì)政府治理有效性的追求,因而必須以先進(jìn)的科學(xué)技術(shù)為支撐。現(xiàn)今,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正好為政府間的合作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臺(tái),因而我們有可能也有條件推進(jìn)政府治理信息化建設(shè),建構(gòu)以網(wǎng)絡(luò)為基礎(chǔ)的整體政府。具體包括以下幾個(gè)方面:首先,加大投入,加強(qiáng)政府信息化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規(guī)范政府網(wǎng)絡(luò)管理體系。其次,以信息技術(shù)為手段,將不同的網(wǎng)絡(luò)支撐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基礎(chǔ)設(shè)施和人力資源進(jìn)行整合,簡(jiǎn)化基礎(chǔ)性的網(wǎng)絡(luò)程序,重新設(shè)計(jì)整體性的公務(wù)支撐功能和事務(wù)處理系統(tǒng),使政府治理程序簡(jiǎn)單化、業(yè)務(wù)流程統(tǒng)一透明化、政府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化,實(shí)行“輕松的、快捷的資源共享的”[10]在線治理模式和“一站式”即時(shí)服務(wù),提高政府治理和服務(wù)的效率。再次,發(fā)展電子民主,廣開(kāi)公共利益在線表達(dá)渠道,采取包括在線公共論壇、在線選舉、在線民意調(diào)查、政府官員線上交流等方式,整合政府與公民間的電子化互動(dòng)回應(yīng)機(jī)制,以求為公民提供優(yōu)質(zhì)的多元化服務(wù)。
[1]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lái)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21.
[2]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dǎo)論[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198.
[3]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12.
[4]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J].中國(guó)行政管理,2008,(10).
[5]咸臺(tái)零.中國(guó)政黨政府與市場(chǎng)[M].北京: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出版社,2002:81.
[6]許淑萍.論政府大部制改革與社會(huì)組織發(fā)展[J].學(xué)術(shù)交流, 2010,(1).
[7]張海波,童星.高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的公共政策[J].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6).
[8]Patrick Dunleavy.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the Digital Era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6 ,(3).
[9]才讓塔.論我國(guó)國(guó)家機(jī)構(gòu)改革的憲法思考[J].國(guó)家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1).
[10]拉塞爾·M·林登.無(wú)縫隙政府:公共部門再造指南[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201.
D035
A
1002-7408(2011)01-0010-03
唐慶鵬(1983-),男,安徽樅陽(yáng)人,南京師范大學(xué)泰州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康麗麗(1983-),女,江蘇如東人,南京師范大學(xué)泰州學(xué)院講師,研究方向:行政改革、公共政策。
[責(zé)任編輯:孫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