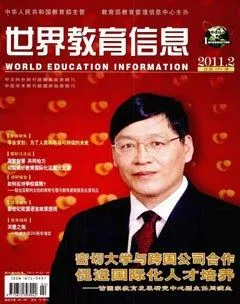洪堡之殤
2010年無疑是全球高等教育值得紀念的年度——柏林大學走過整整兩個世紀。為此,該校于2009年10月啟動了長達15個月的校慶,林林總總活動共計150余項,轟轟烈烈綿延至2010年年底。
恢弘的校慶徐徐落下帷幕之際,恰是回眸2010年慶典與盤點200年軌跡之時。
“折戟”校慶
柏林大學,學界公認為開現代大學制度之濫觴,不僅新大陸美利堅的高校競相效仿乃至復制,不僅1948年分裂之后的柏林大學,其本體于第二年眾望所歸地改稱為洪堡大學,甚而21世紀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仍言必稱洪堡,于是便有“洪堡神話”一說。
200年來,這所受全球頂禮膜拜的學府,其腳步邁得并非飄逸灑脫,甚至有些懵懵懂懂踉踉蹌蹌。值大慶之際,試圖跨越式一躍,卻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于對何去何從而渾渾噩噩。
這跨越式一躍便是題為“洪堡模式:科研世界中的大學未來”的國際學術會議,2010年10月7日~9日在該校召開,充當200周年校慶活動的收官之作。原定在會議落幕之日以《洪堡備忘錄2010》為校慶畫上圓滿甚或點睛之筆,卻因分歧而遙遙無期。
《洪堡備忘錄2010》草案由七大準則組成:①基于科研的教學與從教學獲取靈感的科研作為大學之核心;②以大學自治來保障科研自由;③研究型大學的卓越取決于所有學科的合力;④教學與科研之外,知識的交流與傳播被視作大學第三項核心使命;⑤研究型大學必須使創新型的科研項目不為功利所役;⑥大學應該作為保存與呵護記憶的場所,否則學術無以進步;⑦為跨學科事業,大學應該與校外機構展開合作。草案最后說道:“我們相信,這七個準則為思考明日之大學提供了堅實基礎。這并非意味著對所珍愛的傳統之生存加以保護,但作為對沿著洪堡所薦并被證實為相當成功的道路鍥而不舍地重塑大學的一種貢獻。”
“太保守”、“太謹慎”、“來自象牙塔”,甚至對德國高等教育存有“危險性”,沸沸揚揚,莫衷一是,感性超乎理性。質疑可歸納為如下幾點:大學有無必要涵納所有學科;“研究型大學”的表述是不是一種親美傾向;大學與社會的關系是否僅為單行道;可否把終身學習列為第八條;該備忘錄是為洪堡大學還是為全球所有大學而撰寫。
《洪堡備忘錄2010》的難產,其“禍根”或許在百年前便已播種。
百年“禍種”
1910年10月11日,柏林大學建校百年大慶翌日,以威廉二世皇帝命名的威廉皇帝學術促進會在柏林大學新大禮堂轟然誕生,1911年1月11日舉行首次實質性會議,科研實力主體尤其是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精英從大學大規模撤離,匯聚到促進會旗下的學術機構,設備先進人力雄厚,純科研攻堅無教學義務。該協會首任會長阿道夫·馮·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所倡導的“作為自主的社會系統的學術”公然與大學分庭抗禮。
歷史的吊詭在于,威廉皇帝學術促進會是以普魯士王家科學院的補充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1700年7月11日,選帝侯腓特烈三世決意設立普魯士王家科學院,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泛學科的科學院,并在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設計的方案上簽字。而恰恰這家普魯士王家科學院因1812年1月24日新章程的頒布而名存實亡,其旗下的科研機構逐漸并入新創立的柏林大學。此事件背后的推手正是洪堡兄弟,人文學者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與其弟、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便成全柏林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相統一。可見,威廉皇帝學術促進會的成立,對于柏林大學而言,無疑釜底抽薪。自此以后,柏林大學與洪堡理念從同床異夢走向分道揚鑣,1949年改名為洪堡大學也無力回天。
如果說,威廉皇帝學術促進會以柏林大學百年校慶為機緣冒然在柏林大學新大禮堂高調“稱霸”,那么,恰恰在1910年,《費希特、施萊爾馬赫、斯特芬斯論大學之本質》一書出版,作為百年校慶獻禮,洪堡的篇目卻缺位。把對柏林大學建立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3篇論著結集出版并配以長篇引論的是日后成為德國20世紀教育學巨擘的愛德華·施普朗格(Eduard Spranger)。詭異的是,就在之前1年,施普朗格在柏林大學以500多頁著作《威廉·馮·洪堡與人文理念》獲取教授資格。
難道洪堡本該游離于柏林大學之外?
十頁“遺言”
施普朗格鐘情于費希特、施萊爾馬赫兩位先賢,并非空穴來風。18世紀末19世紀初,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與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已是教育改革的弄潮兒,呼風喚雨,名噪一時。在其改革理念的影響下,1809年2月,威廉·馮·洪堡出任普魯士內務部文化與公共教學司司長,這位普魯士執掌教育政策的最高長官設計了一所“典范大學”(Universitas Litterarum),通過教學與科研相統一使大學生能夠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