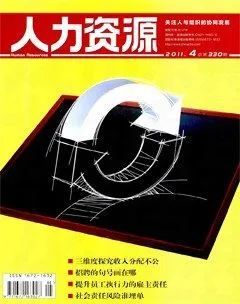走出養老金并軌預期的誤區
“兩會”期間,關于廢除退休雙軌制的呼聲不斷高漲,政府有關部門亦表示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的問題確實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然而有跡象表明,相當一部分人對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的期望值過高,存在著種種誤區。如果不消除這些誤區,不僅不利于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的推進,反而會制造新的阻力,使得并軌的制度設計“出師未捷身先死”。
重在規則公正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負責人楊宜勇的一段話在網上流傳,“從基本養老保險的角度講,任何勞動者都應該是平等的,以后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應該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基本方向。”這段話無疑是在一定語境下講的,而且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識才能予以正確地把握;然而從其產生的實際效果來看,并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反而吊足了人們的“胃口”,似乎當前所要解決的并軌問題就是全民性養老金的一次拉平。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誤解:第一,所謂“任何勞動者都應該是平等的”,容易導致并軌范圍的擴大化。因為農民毫無疑問屬于勞動者的范疇,而我們目前所說的并軌,主要是指企業、事業單位和公務員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如果把農民包括進來,就超出了基本養老保險費的征繳范圍。第二,所謂“基本養老保險應該是一樣的”,容易導致并軌方式的一刀切。因為無論在“企業軌”,還是在“事業和公務員軌”內部,都存在著若干級差。如果純粹不考慮繳費年度、職稱、職務、技能、貢獻等現實差別,所謂基本養老保險的“一樣”就成了絕對平均主義,而其本意是在同等條件下的“一樣”。第三,所謂“基本養老保險應該是一樣的”說法,還容易導致并軌時間的急于求成。誠如楊宜勇所言,他所說的“一樣”是一個“方向”,并不是一紙通知就可以實行的現實操作,設立一個過渡期是必不可少的。
也許將養老金一次拉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平均主義在實踐中行不通。因為現行的基本養老金支付的前提是繳費,而且它是特指企業的社會基本養老金:即使將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并過來,那也不是指全民的基本養老金。事實上,我國農村的養老問題已經由新農保制度的建立,開創出了一條逐步提高的途徑。如果將新農保制度和并軌問題扯在一起,就會抑制農民繳費參保的積極性。而且容易使社會基本養老金混同于公民甚至自然人養老金,即不管是否繳費或者還有其他什么情況,到了一定年齡就理應拿到“一樣”的養老金。結果會讓中央財政不堪這種高福利訴求的重負,因為目前即使是狹義的企業社會基本養老金,也存在著相當大的缺口,延遲退休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揮之不去。
其實,我們不應當低估基層群眾的覺悟,他們不會簡單的“仇富”,也不會指望在一夜之間與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享受同等的養老待遇,只要彼此的差異是通過正當的途徑實現的就可以了,這就是規則公正,而當前我們所討論的并軌的積極意義正在于此。但是規則公正不等于平均主義,追求或者允諾平均反而有違公正。在市場機制存在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鼓勵增加養老收入的多元化。即使企業、事業單位、公務員系列養老體制成功并軌,在基本養老金之外,企業年金、個人賬戶之間的受益程度會依然不同。同時還有商業養老保險的合法存在,每個公民都有在商業養老保險方面的投保自由。另外,在逐步提高全民養老統籌水平的過程中,我們也應當客觀看待所謂的“碎片化”;作為一種過渡措施,計劃生育夫婦養老保險、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村干部養老保險、老年津貼制度、農村五保戶制度、優撫制度和城市孤寡老人福利制度等所做出的努力,我們都應當給予必要的尊重。
重在綜合平衡
上市公司華遠地產的年報披露,任志強的“象征性”年薪是758萬元。經國資委考核,實際能落實的大約為70多萬元,照章納稅和繳納全額社保后,他拿到手的年薪在40多萬元。而即將退休的他,按照目前北京市企業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水平每月2268元計,一年的養老金不到3萬元。有媒體將這稱之為悲劇性的收入滑坡:然而與每月只能拿到55元養老金的農民相比,他依然“高高在上”。這就告訴我們,基本養老金并軌如果只是在退休后才產生約束力,依然難以讓人產生公平感。
基本養老金并軌如果只是在退休后才產生約束力,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誤區,忽視了養老金相對于工資的“替代”性質。衡量養老金福利水平的高低除了其覆蓋面大小的區別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是工資替代率。上述任志強的養老金,與他退休前的工資相比,其工資替代率相當低,不到10%。如果基本養老金的并軌不顧工資替代率,在人們退休后一律拉平,反過來不利于其在職期間獎勤罰懶。而且在職期間工資水平較低者對工資水平較高的人仍然會有意見,認為他原本就不該拿那么多。從社會分配的角度看,人們在職期間的工資屬于第一次分配,養老金屬于第二次分配。如果在第二次分配時強求一致以示公平,那么人們的公平訴求必然會追溯到第一次分配;如果對此采取回避的態度,就是一種舍本逐末。
事實上,養老金的不公與工薪收入的不公之間,是一種流與源的關系。如果后者的懸殊過大,前者的公平約束力就會相形見絀。與基本養老金的并軌相比,當前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擴大的勢頭是一個更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據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的統計,以2010年為例,20%最低收入人群與20%最高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差已經突破了2位數,達到11倍,而且這一幅度有可能還會擴大。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劉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指出,當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萬倍,因此他呼吁在“十二五”期間,要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專家們關于基尼系數屢屢超過國際警戒線的統計告訴我們,如果對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擴大的勢頭不加以遏制,就會加大并軌的阻力,“越往后拖,解決起來難度越大”。
顯然,如果想使并軌的公平約束力在人們退休后產生作用,那么在人們退休之前的第一次分配中體現社會公正更為重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同樣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要體現規則公正,重在綜合平衡。在當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身份之間實際存在著的分配鴻溝中強調綜合平衡,也存在著一個如何“并軌”的問題。如果稱之為對計劃經濟的理性回歸,并無不可,盡管這需要進一步的解釋。比如在提高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方面既要給政策,又要破體制。因為不同的地區、行業和不同的企事業單位,在資源占有的地位上有差別、效益有優劣,盡管有增長工資的鼓勵政策,但位于相對劣勢的地區、行業和企事業單位沒有相應的實力,不僅不能保證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實際收入反而會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時候就有必要打破體制界限,適當地提高工資發放的統籌層次,確保同工同酬。
重在選擇權的賦予
在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的努力中,弱勢群體過高的期望值固然需要正確的引導;然而對于并軌之前薪酬和養老金較高的群體而言,改革的推進對他們也不能過于遷就,否則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目標的實現將遙遙無期。有消息表明,不少公務員擔心養老金并軌,擔心自己的退休金將削減一半。對于掌握立法資源的公務員來說,這種擔心很容易形成網友所說的并軌中“最大的阻力”。
在解決收入分配懸殊過大的過程中,基本養老保險的并軌無疑需要適當控制收入水平較高層面的增長幅度。如果一定要經過收入水平較高層面中關鍵群體的同意,將會使基本養老保險的并軌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那不僅是與虎謀皮,還往往如同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很難做得到。如果像高薪養廉那樣對公務員網開一面,勢必會造成同一收入層面其他群體的攀比,比如“事業單位養老改革懸空”。在事業單位養老改革中,相關文件明確提出,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待遇應當向企業職工“看齊”。這無疑是符合并軌方向的,但是在試點中卻遭到不少事業單位的強烈抵制。他們試圖“把公務員同拉下水”,要求同公務員一起改,致使五個省市的試點工作遲遲未能展開。
由此可以看出,為了基本養老保險并軌的順利推進,公務員參加社會保險的改革優先提上日程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牽好這個“牛鼻子”,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僵局再現不僅難以避免,已經出現的僵局也難以突破。當然,公務員參加社會保險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提供一個過渡期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必須強調以公共利益為重,而不能看少數強勢者的臉色行事。公務員應當是人民的公仆,“仆人”沒有理由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主人的利益之上。這并不是對公務員應有權利的剝奪,可以提供一組選擇,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對于原有的公務員,除了“老人老辦法”的過渡,還可以提供提前若干年退休、轉到他們認為對自己更有利的“體制”中去等備選方案。對于新錄用的公務員,可以提供不同的方式,在他們參加選拔時就明確告知,使他們在選擇進入公務員隊伍時有一個合理的預期。
選擇權的賦予是個必須系統思考的問題,需要打破地區、行業壁壘,突破資源壟斷、身份界限,統籌兼顧。當務之急是改變那種試圖從更大的系統中孤立出來,規避在更大的范圍內承擔更多責任,在“減員”后“增效”的思維慣性。實踐告訴我們,以舉國之力在一個領域中異軍突起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協調升級,在分配領域也是一樣。系統科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不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大,如若不顧“環境”的反饋,不僅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從深圳等地公務員系統養老改革的試點經驗來看,在化解并軌“阻力”的時候,拿出一個更有權威的頂層設計勢在必行。這又需要從分配領域的頂層設計做起,由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去統籌協調。毫無疑問,只有在不同地區、行業、體制之間能夠相對同步地共享改革成果,彼此之間的職業選擇和合理流動才具有現實意義,基本養老保險的并軌方能水到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