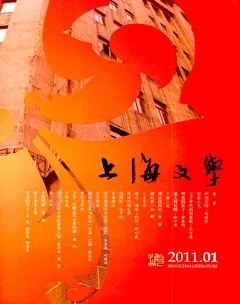文學(xué)\\大概念與日常紋理
文學(xué)研究通常區(qū)分為文學(xué)理論、文學(xué)史、文學(xué)批評三個類別。文學(xué)批評,很大一部分即是一部文本或者一個作家文學(xué)寫作的具體分析。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注意到一個意味深長的跡象:文學(xué)批評——也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個作家的分析——愈來愈少。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批評家對于作品與作家懷有濃厚的興趣,他們津津樂道自己的解讀體會,仿佛身臨其境,穿梭在作家編織出來的故事之間;然而,現(xiàn)在的文學(xué)批評已經(jīng)大為蕭條,作品或者作家很少光顧批評家的宏偉思想了。許多批評家放棄了所謂的“細讀”,轉(zhuǎn)向了宏大的理論企圖——文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史。相對地說,這些年文學(xué)理論觀點與文學(xué)史知識的產(chǎn)量的確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文化研究”風(fēng)行之后,這種狀況有增無減。我想事先表明的是,我很喜歡“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再一頭扎在深奧但有些霉味的經(jīng)典里面,而是直接面對生氣勃勃的當(dāng)代文化。大眾文化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對象,各種文化生產(chǎn)機制也是“文化研究”的考察對象,甚至整個世界都被當(dāng)成一個巨大的文本給予分析。所以,“文化研究”制造了許多有趣的話題,也啟用了許多有趣的分析方法,意識形態(tài)分析即是其中的一種。“文化研究”可以選擇各種文本作為個案,但是,這種分析已經(jīng)與傳統(tǒng)的批評趣味相距甚遠,批評家很少談?wù)撟髌分腥宋锏男は穸嗝瓷鷦樱骷胰绾渭毮伒伢w驗人物的內(nèi)心經(jīng)驗,舞會上幾個人物之間的對話隱含了哪些機鋒,一條街道或者一片風(fēng)景的再現(xiàn)栩栩如生,如此等等。“文化研究”更熱衷于利用作品的各種片斷重構(gòu)自己的話語場域,然后引申出某種特殊的話題,例如一部武俠小說之中的兵器譜,另一部歷史小說內(nèi)部的服裝體系,某種修辭或者某個詞匯的使用如何說明民族交往之間的不平等,故事內(nèi)部的人物關(guān)系如何折射出性別歧視,等等。總之,現(xiàn)在的許多批評家不耐煩地擺脫了作品內(nèi)部故事情節(jié)的具體糾纏,迅速地構(gòu)建起他們自己的理論樓閣。
當(dāng)然,文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史領(lǐng)域的興旺昌盛令人稱許。但是,文學(xué)批評的大幅度萎縮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問題?我曾經(jīng)將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大學(xué)的學(xué)術(shù)體制。許多人的心目中,學(xué)術(shù)是一些“硬知識”,是史料,是一個個理論命題,瑣碎地解讀一部作品似乎沒有什么分量。教授們習(xí)慣的“學(xué)問”來自引經(jīng)據(jù)典。現(xiàn)在看來,這種狀況背后可能還隱藏了另一些原因。尤其是與幾位作家交談之后,這種想法更明朗了。
應(yīng)該承認,不少作家正在逐漸喪失對于批評家的敬意。公平地說,多數(shù)作家很難在學(xué)術(shù)的意義上判斷眾多理論命題或者文學(xué)史研究的價值。他們肚子里常常嘀咕的一句話是——許多批評家越來越不懂“文學(xué)”了。如果僅僅把文學(xué)包裹在一大堆概念術(shù)語之中,肯定無法洞悉文學(xué)的精髓。作家——當(dāng)然,特別是小說作家——通常是人情練達,世事洞明,既了解大院落里面的勾心斗角,也明白江湖之上的三教九流。許多作家都擁有一副看穿世故的火眼金睛,活像一個個巫師或者巫婆。譬如張愛玲這種作家,從客廳、廚房到弄堂、店鋪,日常生活之中的哪些小伎倆、鬼把戲逃得出她的眼光?所以,這些作品里面隱藏了豐富的皺折,并不是空降一兩個概念——諸如什么什么“主義”——就能處理得了。如果迂腐地按照某種理論設(shè)計按圖索驥,那些作品就會像蠟人一樣缺少生命的氣息。
批評家因為某一個特殊的主題——例如“尋根”、“苦難”、“孤獨”——褒獎某一些作品的時候,作家或許會不屑地嗤之以鼻。他們對于這些主題沒有異議,然而,他們認為許多批評家只會貼標(biāo)簽,分辨不出“藝術(shù)”上的優(yōu)劣。質(zhì)量上乘的作品通常血肉豐滿,有時作家會使用“紋理”這個詞。如同一篇論文的論證質(zhì)量取決于作者思想的縝密程度,許多杰作往往紋理細密。這些作品的質(zhì)地堅實厚重,人們甚至很難用一句話簡單地概括這些杰作的主題。相反,一些貌似尖銳的作品內(nèi)涵單調(diào)。批評家之所以很容易給這些作品安上各種名目,恰恰因為它們簡單。嚴格分析起來,許多作品架構(gòu)單薄,邏輯脆弱,生硬之處與人為的扭曲比比皆是。批評家賦予這些作品的聲譽往往言過其實。他們認為,工藝認真的作家已經(jīng)所剩無幾,批評家的褒獎又再度鼓勵了粗制濫造的風(fēng)氣——因為不懂行。
我對于作家諸如此類的抱怨并不陌生。批評家活動于自己的領(lǐng)域,各種結(jié)論的價值必須放置于理論的背景之下給予衡量。作家是一批生產(chǎn)者,他們的評語可能陷于操作主義,常常受到實踐之際具體情境的影響因而缺少高瞻遠矚的氣度。然而,近來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變。我再度意識到,理論的傲慢無疑是一種危害。盡管我不能完全認可作家的抱怨,但是,我還是試圖認真地考慮一下——批評家是否真的忽略了什么?
這時,一些新的認識開始出現(xiàn)。
一些著名的經(jīng)典作家或者經(jīng)典作品的確顯現(xiàn)了這個特征:紋理細密。例如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尤利西斯》的密集程度可能是許多人難以接受的,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質(zhì)地同樣極其細膩。我們可以挑出“斯萬的愛情”這個片斷再讀一遍。斯萬如何逐漸地戀上了奧黛特?這個過程沒有多少戲劇性起伏的情節(jié),但是,密集的心理細節(jié)絲絲入扣地完成了一個不動聲色的內(nèi)心轉(zhuǎn)移。許多時候,人生是由眾多的細節(jié)鋪陳出來的。日常生活的許多細節(jié)決定人生這樣而不是那樣選擇。一個人的生活感覺通常會落實到細節(jié)層面上。是否愛一個人,這間臥室是否舒適,幾個朋友是否默契,同僚之間的氣氛是否融洽,這些問題未必訴諸大幅度的動作情節(jié),而是更多體現(xiàn)于各個生活細節(jié)。作家通常知道,虛構(gòu)一個精彩的情節(jié)遠比虛構(gòu)精彩的細節(jié)容易。敘述比描寫容易。人們可以在電視節(jié)目單、影碟的封面或者新版圖書廣告之中讀到各種情節(jié)介紹。可是,如果沒有相應(yīng)的細節(jié)積累,這些情節(jié)介紹只能是一個梗概。五百個作家寫得出這種梗概,只有一個作家才能提供足夠的細節(jié)完成作品。離奇的情節(jié)可以上天入地,海闊天空,堅實的細節(jié)才能讓這些情節(jié)返回人間。如果這些情節(jié)的離奇程度超過了細節(jié)的負擔(dān)能力,說服力就會急劇下降。一個人屢屢輕易地穿越槍林彈雨,不費吹灰之力擒獲敵國的總統(tǒng)——構(gòu)思這種情節(jié)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哪些細節(jié)才能使這種故事顯得可信?
大約已經(jīng)有十幾年的時間,金庸小說的聲名大噪。如果有權(quán)利自由選擇,多數(shù)人寧可閱讀《鹿鼎記》而不愿意問津《紅樓夢》。但是,我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里表示,前者的價值遠不如后者。
……
這時,我很愿意再度提到金庸,提到他的收山之作《鹿鼎記》。這部小說的離奇、有趣傾倒了許多人。出身于妓院的韋小寶吉人天相。盡管沒有任何武功,他的油嘴滑舌持續(xù)地化險為夷,并且在愛情領(lǐng)域充當(dāng)了一個最大的贏家。一個又一個美女絡(luò)繹不絕地投懷送抱,韋小寶揮揮手慷慨地照單全收。小說的結(jié)局是,韋小寶攜帶七個美貌的太太和一大筆財富享受他的逍遙人生。如此之多的人強烈主張,金庸業(yè)已當(dāng)之無愧地進入經(jīng)典之列,以至于我不得不抬出另一部經(jīng)典作為參照——《紅樓夢》。賈寶玉生活于鐘鳴鼎食之家,大觀園的眾多姐妹造就了一個溫柔之鄉(xiāng)。無論是黛玉、寶釵還是賈母、鳳姐、襲人、晴雯,賈寶玉是所有人溺愛、疼愛或者憐愛的對象。然而,就是在如此甜蜜的網(wǎng)絡(luò)之中,賈寶玉的人生危機開始了。生活的難題如此之重,賈寶玉不得不斬斷塵緣,出家是他了結(jié)一切的最后形式。顯然,曹雪芹并未被榮華富貴迷惑,他在各色人等密不透風(fēng)的內(nèi)心生活中剝離出尖銳的不可承受之痛。如果說,這種悲劇性的幻滅感是《紅樓夢》的深刻,那么,金庸給出的生活理解簡單極了:生活就是如此地輕松快樂,即使在刀光劍影、兵荒馬亂的年頭,金錢或者美人仍然會在運氣的驅(qū)使下不可阻擋地降臨。《鹿鼎記》時常不知不覺地拐向了喜劇——這并非偶然。
上面這一段論述中,我對于《鹿鼎記》的非議是——過于簡單的生活理解。現(xiàn)在,我愿意繼續(xù)補充的是,過于簡單的生活描寫只能帶來過于簡單的理解。金庸的許多小說相當(dāng)粗糙,只有骨架而沒有細節(jié)。一個人獨自在古墓之中練功十年,這種情節(jié)很容易設(shè)想;可是,如果要寫出如何解決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這就是極大的考驗。《鹿鼎記》之中的所有奇跡之所以能輕松地實現(xiàn),因為武俠小說之中的江湖沒有日常生活的重量。一日三餐,油鹽柴米,衣食住行,量入為出——我們之中多數(shù)人的豪俠氣概就是被這些瑣事拖垮了。如果沒有日常生活的負累,誰說我們就不能當(dāng)一個武俠?就是因為甩不下這些生活細節(jié),我們無法踏入那個自由自在、快意恩仇的江湖。所以,《鹿鼎記》僅僅能充當(dāng)一個成人童話。《紅樓夢》之中賈寶玉的遭遇一樣奇特:一個從花團錦簇之中成長起來的公子哥兒,最終毅然地辭別榮華富貴,落發(fā)出家。然而,《紅樓夢》的高超之處在于,無數(shù)細節(jié)堆積成的日常生活逐漸顯露出不可動搖的邏輯——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結(jié)局。我們無法將賈寶玉的后半生想像為一個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盜,或者成為一個大腹便便的官員。許多經(jīng)典作品的故事情節(jié)是全部細節(jié)堆出來的,這些細節(jié)聚沙成塔地凝聚成無法更改的可能性。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肯定要自殺的,包法利夫人也肯定是要吞砒霜的。相對地說,偵探小說或者武俠小說常常以固定情節(jié)征集細節(jié),情節(jié)是主導(dǎo)。這些情節(jié)僅僅是一個建筑設(shè)計圖。如果沒有相應(yīng)的建筑材料,這些建筑物不會真正矗立在地平線上。如果浮皮潦草地使用不合格的材料,這些建筑物即使建起來,最終還是要倒塌。
一部小說如何處理疏與密,這是一個技術(shù)性很強的問題。沒有理由認為,紋理越密越好。萊辛的《拉奧孔》在比較詩與畫時指出,詩人進行大密度的羅列很可能事倍功半。人們讀到最后一句的時候,肯定已經(jīng)忘了第一句。疏與密的選擇是很重要的。疏可跑馬,密不透風(fēng),“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阿霞已經(jīng)從一個小丫頭長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一句話寫出了二十年,可以“疏”成這樣;另一部小說的開始就是某一個主人公早晨醒來,可是幾十頁翻過去了,主人公還沒有從床上起來——也可以“密”成這樣。
那么,選擇的依據(jù)是什么呢?
觀察一個對象的時候,將對象分解為十個單位、一百個單位、一千個單位,觀察的細致程度遠不相同。這就是分辨率問題。分解的單位愈多,分辨率愈高,觀察到的圖像愈是精密。一個作家不喜歡這一類的敘述:“他高興地走了”;“她憤怒地說”,如此等等。“高興”或者“憤怒”僅僅是一個粗糙的觀察單位,這些單位還可以分解為音容、笑貌、肌肉的抖動、呼吸的加劇、步態(tài)的變化,等等。
理論的意義上,分辨率的提高是無止境的。然而,一個恰如其分的分辨率取決于觀察的目的。考察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考察某一個王朝的崩潰,沒有必要研究一個閃爍的笑容或者一個羞怯的眼神;然而,如果考察一個戀愛事件,這些細節(jié)就必須納入視野。所以,我曾經(jīng)說過,歷史與人生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歷史學(xué)家關(guān)注的是各種宏大的景觀,諸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某種社會制度的確立,某一場戰(zhàn)爭的勝負,帝王將相理所當(dāng)然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公。相對地說,作家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在于描寫具體的人生,諸如一個人的服飾打扮,說話時的表情,內(nèi)心深處的波瀾,咖啡館里的交談,餐桌上的拌嘴,總之,一些有趣的細微末節(jié)。
我想,這里有必要稍微解釋一下。在我看來,所有過往的事情都可以通俗地叫做“歷史”。歷史學(xué)是一種處理歷史素材的方式,文學(xué)是另一種處理方式。古代的史官是一個重要的職位,負責(zé)記載國家及宮廷的各種重大事件。許多朝代不允許個人修史,因為涉及的是大事件、大人物。相對地說,文學(xué)——尤其是現(xiàn)代文學(xué)——考察的是歷史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近現(xiàn)代以來,日常生活的意義逐漸進入了作家的視野。羅蘭·巴特精辟地指出,藝術(shù)之中沒有雜音。換一句話說,文學(xué)作品不存在沒有意義的多余筆墨。多數(sh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瑣碎景象無助于說明歷史重大事件,但是,這不等于沒有意義。這時,衡量各種意義的范疇是人生。歷史大尺度里沒有意義的細節(jié),放置在幾十年的人生里面可能熠熠生輝。日常生活的最基本意義當(dāng)然就是維持個人身體的存活,許許多多細節(jié)就是為了維持生存。文學(xué)再現(xiàn)日常生活,也就是再現(xiàn)了生活的環(huán)境、氛圍。另一方面,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人生轉(zhuǎn)折的某種契機。一次列車的晚點可能制造了一對情侶的首次邂逅,一句不合時宜的回答可能破壞了一個小職員晉升的機會——當(dāng)文學(xué)以人生為觀察單位的時候,這些內(nèi)容的重要性極大地增加了。
我已經(jīng)多次說過,文學(xué)批評時常對于這種分工表示不滿。文學(xué)收集了那么多雞零狗碎的生活景象,這又有多少價值?——批評家對此信心不足。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將文學(xué)之中的各種日常生活景象納入歷史范疇。換言之,“人生”這個范疇被規(guī)定為“歷史”這個范疇之下的組成單位。這造就了批評之中“典型”這個概念的意義。“典型”概念的衡量之下,各種個別的人物、性格、行為、思想狀態(tài)無不通向一般,通向一批類似人物的共性。當(dāng)然,這僅僅是“典型”的初步涵義。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一般”和“共性”并非某種靜態(tài)的描述。一個“馬大哈”或者一個“嫉妒者”、一個“吝嗇鬼”,這種性格類型的總結(jié)沒有多少意義,重要的是表明這些性格在某種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的作用。他們是歷史的先行者,還是阻止歷史進步的反動派?這時,每一種性格之中就帶有豐富的歷史信息。這是對于“典型”的深刻理解。在我看來,盧卡奇的理論將這個問題表述得最為清晰。他認為歷史是一個總體,“典型”人物最為深刻地展現(xiàn)了歷史的內(nèi)在可能性。這時,從鞋子里掉進的一粒沙子到街道上馬車的樣式,從宮廷里的一次嬉鬧到邊陲之地的非法交易,文學(xué)之中的全部內(nèi)容都聯(lián)系起來了,并且共同從屬于一個稱之為“歷史”的至高意義。
“典型”的確顯現(xiàn)了概括世界的雄心,完成了一個理論的“格式塔”。可是,現(xiàn)今看來,這種理論“格式塔”似乎存在某些問題。這里,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xué)仍然是一個無形的主宰。黑格爾的想像中,先驗存在的絕對精神是一個神秘的本體,歷史的每一個階段無一不是這個絕對精神的不同顯現(xiàn)方式。相似的是,上述理論“格式塔”預(yù)設(shè)存在一個業(yè)已完成的歷史藍圖。這種歷史藍圖懸空地掛在人們的前方,所有的蕓蕓眾生無非是填空式執(zhí)行早就規(guī)定下的指令。只有這張歷史藍圖存在,我們才能識別“典型”,才能夠知道誰在扮演歷史的主角,誰又是無足輕重的配角。這種觀點無法想像,每一個人都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創(chuàng)造歷史,歷史不是先在的,歷史就在他們手中。每一個人的意愿、沖動、思想、行為都是歷史建構(gòu)的一部分,都將在歷史之中產(chǎn)生或強或弱的回響。那些強悍的、高歌猛進的英雄人物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眾多無聲無息的普通人也是歷史的組成部分。沒有后者,前者又有什么意義?歷史是所有人的共同產(chǎn)品,所以,歷史的完整圖像始終是未知的。某些時候,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可能被替換為“歷史規(guī)律”。即使如此,所謂的“歷史規(guī)律”亦非某種神秘的原則居高臨下地主宰每一個個體,如同某種生物的密碼不斷地復(fù)制人們的生命圖式。相反,作為一種文化動物,人類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不斷地突破固定的生命圖式。嚴格地說,人類創(chuàng)新能力制造的未知即是“歷史規(guī)律”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歷史規(guī)律”業(yè)已包含了不可重復(fù)的新型可能,這顯然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一個重要差異。總之,理論“格式塔”強調(diào)的是已經(jīng)完成的歷史——盡管是認識上的完成而不是實踐上的完成;相反,我傾向于認為,歷史始終處于生長之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未定之?dāng)?shù),始終給人們留下了開創(chuàng)和拓展的空間。
不過,相當(dāng)長的時間里,我們對于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xué)還是很習(xí)慣的——盡管我們口頭上不斷地說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我們還是習(xí)慣于想像,歷史有一張先驗的藍圖等待實現(xiàn),一批先知先覺的領(lǐng)袖人物率領(lǐng)無數(shù)庸眾向著宏偉的目標(biāo)進發(fā)。這是一幅有機的圖景。歷史已經(jīng)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必須在這一幅圖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么擁護這個宏偉的目標(biāo),要么反對這個宏偉的目標(biāo),沒有人可以自作主張地游離于這一幅圖景之外。文學(xué)所要描述的,就是這一幅圖景的縮微版。這時,所謂的“紋理細密”并沒有多少意義。多一個細節(jié)或者少一個層面均不影響歷史的認識。一切已經(jīng)事先規(guī)定,一個例證與二十個例證效果相同。反之,如果某些日常生活的景象逸出了預(yù)設(shè)的解釋軌跡,尷尬的理論局面將難以收拾。
我估計不少人覺得,這一幅圖景過于理想化了。歷史的藍圖、目標(biāo)、整體、領(lǐng)袖與大眾——構(gòu)成這一幅圖景的各種因素都出現(xiàn)了問題。從后現(xiàn)代主義到福山“歷史的終結(jié)”,各種理論正在從諸多方面質(zhì)疑這一幅圖景。但是,或許我們還是要承認,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常生活的確十分簡單、明朗。那時日常生活的層次很少,沒有各種發(fā)型和服裝款式,沒有那么多的汽車和樓房,沒有電視和互聯(lián)網(wǎng),只有幾本文學(xué)著作和幾部電影供全社會消費,借閱一本小說或者送一張電影票就有可能開始一場戀愛。那時人們的思想十分單純,“最高指示”回響在幾億人的腦子里,人們相信這就是世界的唯一出路而不再思考什么。當(dāng)然,那時的思考是一種危險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失控很可能破壞這種簡單、明朗的局面。所以,那時的知識分子是麻煩的源頭。他們因為多讀幾本書就不知天高地厚,貿(mào)然發(fā)表一些僭越的言論擾亂思想秩序。某些具有海外背景的知識分子還會不知趣地引用幾個英文單詞,這顯然是挾洋自重。這種情況下,那時的文學(xué)常常闖禍。一些作家讀了些俄羅斯作品或者中國古典名著,時不時就企圖把人物寫得復(fù)雜一些。如果英雄人物與反動人物的復(fù)雜性可能導(dǎo)致故事情節(jié)偏離航線,那么,能不能在“中間人物”身上試一試,展示冰山之一角?普通人是不是也可能產(chǎn)生猶豫,產(chǎn)生憐憫之心,或者,見了美女也會產(chǎn)生性的欲望?這種企圖當(dāng)然及時地遭到了嚴厲批駁。“小資產(chǎn)階級”以及“個人主義”的喝斥令人心驚肉跳,而污蔑“工農(nóng)兵”的罪名可以立即置人于死地。某些作家愿意花一些精力交流寫作技巧。這時,“形式主義”的聲討立即出面封堵這種興趣。批評家指出,“形式主義”的譜系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遠離勞動人民的火熱生活。事實上,研究文學(xué)形式還隱含了一種擔(dān)憂——擔(dān)憂無意地開啟“所羅門的瓶子”。那時整個社會的語言體系比現(xiàn)在簡單得多。從報紙到人們的內(nèi)心,人們的詞匯量以及表述方式遠不如現(xiàn)在豐富;如果表述強烈的情感,口號的數(shù)量遠遠勝過詩。這保證了社會成員的思想共同運行在一個狹窄的軌道上。如果眾多的詞匯、表述方式無形地打開了一扇扇門戶,將會增加思想出走的可能性。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生活變了,文學(xué)也變了。理論“格式塔”終于破裂。
上面那一段關(guān)于《紅樓夢》、金庸比較的文字引自不久之前我寫過的一篇文章《奇怪的逆反》。我想指出一個奇怪的事實:周圍的生活越來越復(fù)雜的時候,文學(xué)卻越來越簡單了。如今的大眾傳媒十分發(fā)達,各種消息紛至沓來,正在全面地覆蓋這個沸騰的社會。天文地理,奇聞軼事,還有哪些我們不知道的?如此之多的記者穿梭于大街小巷,這時,作家不得不重新想一想,文學(xué)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事實上,我正是在這些意義上重新考慮到作家的抱怨: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作品內(nèi)部的細密紋理,這是文學(xué)處理歷史、揭示生活奧秘的與眾不同的獨特視角。
我們的身邊,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生活的確出現(xiàn)了急劇的轉(zhuǎn)折。人們當(dāng)然可以從各個角度給予總結(jié)。我曾經(jīng)做出一個概括:從革命時期轉(zhuǎn)入后革命時期。后革命時期,生活的大幅度分化形成了眾多復(fù)雜的層次。許多人用“啟蒙”形容80年代的文化。這種啟蒙不僅帶來了個人的思想覺醒,同時,權(quán)利意識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望同時浮現(xiàn)。這時,人與人的關(guān)系圖譜迅速多元化。五六十年代社會成員的關(guān)系幾乎完全從屬于政治聯(lián)盟——階級。階級陣營是鑒定敵人和朋友、好人與壞人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然而,利益、欲望大面積介入之后,各色人等之間的種種聯(lián)盟時刻都在重組。與此相應(yīng)的是,社會的文化生活正在急速裂變。持續(xù)多時的革命話語開始松懈,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左右社會的價值判斷。另一方面,緊張的革命氣氛消退之后,一個充滿世俗氣息的日常生活被釋放出來了。五六十年代,所謂的日常生活多半仍然是另一種形式的工作和勞動。趙樹理小說中,一個女人回答為什么愛一個男人,答案就是:“因為他會勞動。”然而,現(xiàn)今日常生活的空間一下子膨脹了幾千倍。從繁瑣的生計、一地雞毛的家長里短、小人物的各種小算盤到富豪們的娛樂、消費、享受,這個空間擁有眾多的內(nèi)容。古往今來,我們每一天都必須沉浸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完整的范疇被文學(xué)意識到,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潛入這些生活,條分縷析,這種文學(xué)才不至于如同泡沫似的浮游在生活的表面。
我的另一個感覺是,歷史正在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插入我們的生活。革命話語松懈之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乘虛而入,許多學(xué)說打起了“國學(xué)”的旗號,例如儒家學(xué)說。如果僅僅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視為業(yè)已逝去的一個歷史文化遺跡,一種學(xué)術(shù)研究的對象,人們大致上不會產(chǎn)生多少異議。然而,如果力圖證明儒家文化將如何主宰當(dāng)下以及未來的日子,情況可能迅速地復(fù)雜起來。由于歷代儒生的解讀,理解儒家學(xué)說的最基本涵義并不困難。恰恰因此,另一個問題就迅速地尖銳起來:無論是仁、義、禮、智、信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簡明而良好的理念為什么一直實現(xiàn)不了?我們不是一個勤勞勇敢,而且充滿智慧的民族嗎?正面的闡述、倡導(dǎo)僅僅是一種通俗的學(xué)術(shù)解說,只有面對這個難題才是介入歷史。后革命時期出現(xiàn)的另一些問題也是如此。正如一些人已經(jīng)反復(fù)指出的那樣,許多跨國資本進入中國,一大批底層民眾正在遭受跨國企業(yè)的剝削。然而,如果表示義憤之余還企圖考察這種狀況的前因后果,那么,我們不得不追溯更為深刻的歷史原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曾經(jīng)對于跨國資本嚴辭拒絕——80年代之后為什么不得不改變當(dāng)初的選擇?當(dāng)時,還有哪些方案可供權(quán)衡、比較?經(jīng)濟數(shù)據(jù)之外,還有多少其他因素決定了這種選擇?只有全面地考慮這些問題,我們才不至于將革命時期與后革命時期截然分開——事實上,后一個歷史階段的許多主張恰恰是前一個歷史階段的必然產(chǎn)物,只不過二者之間是以顛倒的形式聯(lián)系起來。總之,在我看來,一個個歷史階段不是單純地疊加起來,而是隱藏了種種內(nèi)在的交織與回環(huán)。如果文學(xué)不愿意浮光掠影地收集一些表面印象,作家就必須深入歷史的內(nèi)部脈絡(luò)。
如何深入?我已經(jīng)提到文學(xué)處理歷史的方式——從日常生活進入,從一個個具體的人物、故事進入。歷史不僅存在于各種巨型景觀之中,同時存在于乘車的感覺、餐廳的氣氛、流行的服裝款式以及打招呼的用語等無數(shù)瑣碎的細節(jié)之中。這些瑣碎的細節(jié)不一定能夠有機地與重大歷史事件掛起鉤來,但是,它們往往能引起眾多社會成員的情感共鳴。換言之,這些細節(jié)的意義在社會成員相似的“感覺結(jié)構(gòu)”中得到了衡量。歷史不該理解為抽象的、沒有人物而只有事件和數(shù)據(jù)的記錄。文學(xué)可以表明,具體的個人以及圍繞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最終必然包含個人的解放,或者說必須抵達這個最終目標(biāo)。這大約是“以人為本”的一個部分,文學(xué)集中處理這個方面。所以,我在《壓抑和解放: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和符號》一文中說過:在我的心目中,文學(xué)——尤其是今天的文學(xué)——的首要意義仍然是圍繞壓迫與解放的宏大主題。但是,文學(xué)承擔(dān)的使命不僅是在傳統(tǒng)的意義上認識歷史。對于文學(xué)來說,壓迫和解放的主題考察必須延伸到個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具體、感性的經(jīng)驗。個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壓迫與解放的主題復(fù)雜多變,遠非政治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描述的那么清晰。所以,我更傾向于表述為:壓抑與解放的主題。壓抑也是一種壓迫,但是前者遠比后者隱蔽、曲折、微妙、范圍廣泛,焦點更多聚集于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區(qū)域。因此,解放同時包含了微觀的、小型的形式。這一切均是文學(xué)揭示的內(nèi)容。
后殖民理論進入文學(xué)研究之后,批評家犀利地分析了帝國主義對于弱小民族的壓迫和殖民,尤其是形式隱蔽的文化殖民。但是,這種分析許多時候以民族、國家為衡量單位,民族國家內(nèi)部時常被無意地視為同質(zhì)的共同體。情況當(dāng)然遠非如此,民族國家內(nèi)部同樣存在極其復(fù)雜的壓迫形式。而且,民族、國家內(nèi)部的階級、性別、文化群落之間的等級可能與民族國家外部的各種壓迫形式結(jié)合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體系。如果考察沒有延伸到個人,我們就無法完整地意識到這個龐大體系的威力。魯迅之所以比許多作家深刻,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他對于這個龐大體系的清醒認識。
文學(xué)對于個人和日常生活的興趣還隱含了一種認識:這個領(lǐng)域是總結(jié)歷史的一個重要資源。文學(xué)時常提供了各種未定的經(jīng)驗,即未經(jīng)其他學(xué)科概念固定命名的經(jīng)驗。之所以未定,因為每一個具體的個人在這些經(jīng)驗之中顯現(xiàn)出十分活躍的狀態(tài),單一的概念還無法鎖定。經(jīng)濟學(xué)對于個人的預(yù)設(shè)是,個人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這即“經(jīng)濟人”的基本涵義。然而,文學(xué)觀察到的個人遠為豐富。從理性、情感、道德到各種具體的言行,文學(xué)之中的個人并不是單向地參與歷史,而是在社會關(guān)系中形成一個多向的小小網(wǎng)結(jié)。沒有理由將所有的個人考察都歸為“原子式的個人”。某些現(xiàn)代主義作家的確出現(xiàn)過這種企圖:他們力圖深深地鉆入人物意識的內(nèi)核,并且證明個人與社會無關(guān)。但是,不等于所有涉及的個人考察都是這個主題。相反,許多復(fù)雜的個體經(jīng)驗恰恰說明,巨大的社會如何與個人互動,如何曲折地塑造個體意識,乃至壓縮在無意識之中。
盡管文學(xué)曾經(jīng)多次充當(dāng)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的文化先鋒,但是,文學(xué)提供的個人故事或者日常生活經(jīng)驗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如果說不是越來越遭受輕視的話。文學(xué)作品的細密紋理時常被棄置不顧,因為批評家運用的大概念對于如此微妙的意味產(chǎn)生不了反應(yīng)。這些大概念的常見作用往往將文學(xué)并入某一個現(xiàn)成的學(xué)科,成為一種現(xiàn)成的例證。現(xiàn)在,我們周圍存在眾多聲名顯赫的學(xué)科。各個學(xué)科的確立表明了一種知識分類方式,現(xiàn)今的知識分類方式得到了大學(xué)體制的有力支持。多數(shù)知識分子欣然接受這種分類方式,包括接受知識類別之間的等級差別。許多知識分子對于傳統(tǒng)的壓迫形式相當(dāng)敏感,例如從資本、企業(yè)、經(jīng)濟體制到物權(quán),相形之下,隱藏在知識內(nèi)部的壓迫并未得到足夠的注意,例如從教育環(huán)境、大學(xué)體制、學(xué)術(shù)資本到知識產(chǎn)權(quán)。許多時候,炫耀淵博、炫耀外語、炫耀名牌大學(xué)的資歷幾乎是他們的一個普遍特征。這至少是激進理論無法跨出學(xué)院圍墻的一個原因。如果說,對于多數(shù)知識分子來說,甩開大學(xué)體制的庇蔭幾乎不可能,那么,適當(dāng)?shù)仃P(guān)注文學(xué)肯定是有益的。文學(xué)的具體性始終是一個沖擊,文學(xué)閱讀多少有助于緩解理論帶來的思想硬化。這是我從作家的抱怨之中獲得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