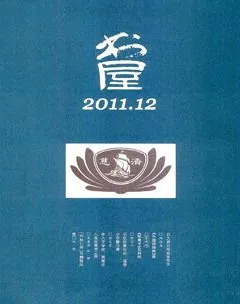陳序經的大學校長生涯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知識界圍繞“全盤西化”問題展開大論爭,嶺南大學青年教師陳序經(1903—1967年)持激進的全盤西化立場,一時間名聲大噪,世人對之詬病者多,公開贊同者少,而內心予以理解者似也不在少數。實則那場筆戰,只是陳序經亮相學術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西南聯大時期擔任法商學院院長,乃聯大院長中最年輕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談”的關于他寧肯不做院長也不肯按規定加入國民黨一事,顯露出這位學人的鮮明個性。他終其一生未加入任何黨派,即使1949年后他頗得賞識器重,即使友人力勸他加入民主黨派,他卻始終保持無黨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團體,大學時代為了回避加入基督教,毅然離開在學兩年的滬江大學而轉入復旦大學,后來他出掌具有教會背景的嶺南大學,竟成為該校創辦以來首位無教籍的校長。陳序經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優容雅量”,頗贏得高級知識分子的好感和信賴。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嶺南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暨南大學校長和南開大學副校長,被贊譽為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難得的大學校長”。亦因如此,為極左的政治氛圍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終于消失在“史無前例”的大劫難之中。
一
1948年8月,陳序經正式出任廣州嶺南大學校長(初為代理),時年四十五歲。此前,他任職天津南開大學已近十四年之久,擔任著國立南開的教務長、經濟研究所所長和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等要職。可以說,在何廉、方顯廷兩位教授相繼離開后,陳序經愈加成為張伯苓校長倚重的中堅力量。有分析說,張伯苓甚至考慮在自己(因出任考試院長)不得兼任校長的情況下由陳序經接任,這一推測也并非毫無根據。可是,張伯苓幾經權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陳序經返回嶺南就任校長一職,明顯與“南開本位”不符,可能而有力的解釋只能是:時局使然。盡管后人記述此事時,大多有意無意地淡化這個顯而易見的背景因素,但細加觀察則不難作出推論。國共兩黨武力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隱然成為“第二戰線”,辦學讀書均非其時。嶺南大學董事會的再三邀聘,終于促使陳序經在大變局到來前夕,結束他的南開生涯,返鄉辦學,竟在一個特殊時期使原本平平的嶺南大學驟然“靈光一現”,卻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陳序經,海南文昌人,當時籍屬廣東。早年跟隨父親到南洋經商,后返回內地上學,大學畢業后赴美留學,獲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學位,隨即短期游學歐洲,回國后最初任教的學校就是嶺南大學。陳序經治學領域寬泛,其中對于南洋各國歷史和華僑問題一直關注,他本人在東南亞華僑中也頗具聲譽。因此,嶺南大學董事會在前任校長李應林業已任職十年要求“休假”之后,物色到陳序經這樣一位與嶺大有淵源的本鄉留美學者,可謂恰得其人。嶺南大學成立于1888年,創辦人乃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牧師,在紐約設有“嶺南大學基金會”,屬于私人捐募性質,因而嶺南作為一所教會大學卻不歸屬任何固定教派。1927年依照國民政府有關規定,嶺南改由國人自辦,鐘榮光先生出任首位華人校長。歷史上該校為躲避戰禍,曾經自廣州遷澳門、香港等地,戰后再回到廣州康樂園。其時,已發展成為具有文、理、農、工、醫、商等學院的綜合性大學。陳序經接手的就是這樣一所建校較早、歷史繁復、亦中亦西、地處嶺表南端、出入國門順暢的私立高等學府。
仔細算來,陳序經擔任校長近四年時間,前十四個月尚在國民黨治下,1949年10月中旬廣州解放,至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被解散,后一階段的兩年半則已是新中國初期。在“改朝換代”過程中,為了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陳序經先后與國共雙方政要打交道,此類活動乃“事務性接觸”,并不涉及所謂歸屬之類。廣州作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最后一個政治中心,有段時間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蔣介石、何應欽或邀宴或要求來校園暫住,陳序經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但是為了營救被捕的嶺大農學院長李沛文,他不得不求助于朱家驊,終于奏效。中共進入廣東初期,執掌粵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學者杜國庠,陳序經對之尊敬有加,并與廣州市長朱光將軍以及楊東莼等領導人合作融洽。不過,當軍管會查出學校出納處違規存有金條,欲拘捕相關職員時,陳序經卻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納員,我是校長,要逮捕,就逮捕我。”肅反期間,校內地下室發現槍支,一時間風聲鶴唳,陳序經調查后行文陳情:槍支為以前學生軍訓時所用,多為一戰時舊物,已銹蝕為廢棄物云云,一場風波得以化解。
其實,美國基金會對嶺南大學提供的資金資助,往往換成金條以求保值,為了避開當時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學校用金條到香港兌換港幣以發放教職員的薪酬。這種“優越性”是否構成陳序經成功吸引一批北方學者戰亂之際來嶺南“棲身”的一個因素,如今恐怕已無從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陳校長的人望,他的誠懇與平易,他的積極主動,再配合嶺南大學的“硬件”設施,以及時人對于局勢的各自判斷,形成了眾賢匯集嶺表的難得一見之景觀。
二
當年嶺南大學的學生、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盧永根先生,在一篇紀念陳序經校長的文章中寫道:“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北平后揮師南下的時候,不少名教授和學者對黨的政策存在疑慮而紛紛南下,準備經香港轉往臺灣或外國。就在這個時候,陳校長毫不動搖地堅守崗位,以自身的行動和禮賢下士的風范,把一批來自北方的名教授羅致到嶺大,說服他們留下來,使他們成為廣州解放后的學科帶頭人。廣東省的多數一級教授就是這樣來的,在醫科領域尤為明顯。”
所謂北方的醫學專家,實際上主要來自北京協和醫學院,關鍵人物是著名的放射醫學專家謝志光教授。陳序經出任嶺大校長剛剛兩個月,就利用回天津辦事的機會,數次趕赴北平拜訪謝志光,懇切相邀,幾次相談后,謝欣然應允,并帶來一批協和的名醫,諸如秦光煜、陳國禎、陳耀真、毛文書、白恩施、許錦世、周壽愷、司徒展等教授。他們南下任教嶺大醫學院,謝志光出任院長,使得該機構盛極一時,雄踞海內。外科專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國撰文憶述:“嶺大醫學院開辦在各學院之后,自1948年聲譽驟然公認為全國當時最佳者。附屬教學之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在此之前,每月虧達五千元港幣,自謝院長上任后,雖醫藥診療費與從前一樣,每月收入盈余由數千元起,六個月內增至數萬元港幣,其他各學院經費皆不充足,全靠醫學院盈余補充,于是其他學院可能繼續添聘國內著名教授,嶺南大學竟成全國最完善大學之一”。辦好一所大學的醫學院,乃陳序經的夙愿,還在戰后南開復校時,他就主張創建醫學院,限于條件未能如愿,而今嶺大醫科的興盛,應是他辦學最得意之舉。
不僅如此,陳序經還聘請到陳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張純明、吳大業、陳永齡、容庚、梁方仲等多位各學科的著名學者來嶺南大學任教,大大提升了學校的師資水平。數學大家姜立夫長期擔任南開大學教授,與陳序經有同事之誼,他本來已經到了臺灣,但不適應那里的生活,陳序經遂邀他來嶺大,設立數學系,請他做系主任。陳序經與陳寅恪相識于1934年,兩人共同參加一個在南京舉行的會議,會后北返列車中相談甚歡,后來又在西南聯大共事,彼此相知漸深。陳寅恪與胡適同機飛離北平后,一路南來,事先與陳序經聯系,表示愿來嶺南大學“避風”,陳序經復電歡迎,隨即電匯一筆充足路費,寅恪先生如約抵穗,而其家人卻到了香港。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陳校長親自赴港勸說調解,終于將陳家接回康樂園妥為安置,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即在此度過。語言學家王力離開清華進入中山大學,不久接受陳序經校長的熱情相邀,也來到嶺大,擔任文學院長并在校務問題上多有建言和翊贊。
人們贊譽陳序經“不但是個學者,而且是個很有遠見、很有組織能力、很能團結人的教育家”。他的辦學能力突出表現在“識才”與“容才”這兩點上。凡遇稍有資歷的教師前來求職,他首先要了解該教師是長期從事學術工作,還是以謀官做官為主,對于后者,他認為必不能專心致志于教學,十之八九必婉謝。而對于所聘教師的學術經歷、治學特點及教育背景等,他幾乎爛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數家珍。識才不易,容才更難。居高位或具有權力資源之人,能夠真正做到“不忌才”實屬難得。陳序經對于教授學者們,不搞宗派,不分留學還是未留過學,只要有才學者,他都很敬重,亦即人們常言的兼容并蓄。曾在嶺南大學任教的法學家端木正評述道:“陳校長和知識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說過,他當教務長也好,當校長也好,從來不到教室去聽教授講課,不去檢查教學。他說,每位教授在我決定下聘書的時候,已經是相信他的教學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幾年書,還去檢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請他。”
三
像多數舊時大學一樣,嶺南大學的行政系統精干而富于實效。校長之下設教務長、總務長,分管教學事務和日常庶務,校長有秘書一名,負責文書和聯絡。各院系負責人均為專職教授。陳序經主政時,學校最高決策層通常為五人:校長、教務總務二長及文學院、理學院的院長。校長對董事會負責,掌有人事、財務的絕對支配權。陳序經勇于決斷,也善于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他常常用電話或登門訪問方式與相關教職員商討決策方案,簡捷而精準,效率很高。他聘用馮秉銓、任銳麟兩位嶺大資深教授分任教務長、總務長,前者乃哈佛博士、電子物理學家,口才好,善交際,教學方法高明,深受校內中外師生佩服;后者是三十年代即來嶺大任教的加拿大華僑、神學博士,曾經兼任廣東國際紅十字救災會工作,忠于職守,富有才干,社會活動能力強。此二人在陳校長短暫而光耀的嶺大辦學生涯中作用重大。
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嶺南大學理學院院長、美國教授富倫先生。嶺大成立之初,外國教師居多,以后逐年減少,至陳序經掌校時僅十余人,其中主要是美籍教師。在陳序經看來,富倫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實學者,他還是美國基金會在校內的代表。對于新校長的若干舉措,富倫不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間的友誼與日俱增。且看1949年6月,即陳序經履職將滿一年時,富倫向美國基金理事會提交的一份報告:
陳校長1948年8月1日就職。從那時起:1、在他的領導下學校平穩過渡,沒有發生任何不滿現象。2、他設法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去年沒有發生透支現象,而且還有點結余以便應付以后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3、他重新組織了醫學院,它的教職工隊伍絕對被視為在中國最有實力的。4、他還加強了其他學院,特別是文學院,吸引了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學者。5、他增進了校園的學術氣氛,在許多方面超過了戰前的水平。6、雖然他不是位基督徒,但他本人和學校的基督教目標及特點都得到廣東各教會機構前所未有的信任。7、他逐步加強了大學的中國人隊伍,同美國人一道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決策。8、他服從校董會的領導,校董會如今非常信任學校領導班子,而一年前卻不是這樣。9、在政治動蕩之際,他處事不驚,使得全體師生能面對變遷保持平靜,令人贊不絕口,而廣東一些人卻惶惶不可終日。
“富倫報告”透露出美方對于新任校長的滿意和贊賞程度,其中所列各項基本上是客觀信實的,特別對新校長處亂不驚的氣度與“一些人的惶惶不安”作了對比。內中“設法得到中國政府的資助”一節,顯然是指陳序經向當時的國民政府尋求辦學經費資助的努力,關于此事的細節,在已刊行的有關陳序經出版物中未見載述。國民政府對于私立大學曾有相當力度的資助,但在兵敗如山倒的局勢下,能有多大余力顧及“碩果僅存”的高等學府,實在是個疑問。不過,陳序經作為商人之子,當然具備一個大學校長“跑經費”的能力,意外地有所斬獲,也未可知。事實上,他在金融界頗有一些朋友,為了辦學而籌措資金,還是有人愿意設法相助或慷慨解囊的。據說,當年陳序經只身北上南開,得到張伯苓欣賞,最初是緣于協助解決了一筆迫在眉睫的經費難題。辦好一所大學,需要能力全面的校長,他無疑是一個能者。
1950年夏,朝鮮戰爭爆發,抗美援朝隨后開始,反美浪潮洶涌而至,嶺南大學的外籍教師紛紛離去。富倫是最后一批撤離的美國教授,離別康樂園之際,陳序經一人前來送別,向這位合作辦學的朋友表示一份個人之間的惜別之情。此時,嶺南大學前景暗淡,中央教育部已經召開了“全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真正的“社會變遷”才剛剛開始。
四
當初有些人動議,將嶺南大學遷往香港,遭校長陳序經否定。他的理由是,如此完善的一個大學遷移異地,談何容易!而內心則認為,國民黨腐敗失去江山,取而代之的共產黨應當有希望。抗戰時期陳序經在南京、重慶曾見到過周恩來,那是些與南開有關的偶然場合,他對這位中共領袖的印象并不差。江山易主之后,他擁護人民政府,與粵省主政者也建立起融洽關系。但是,他擔任嶺南大學校長的后半段,總的感覺是危機四伏,精神壓抑。除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壓力外,過去辦學的一些有效做法如今卻行不通了,他自述:“政府命令停止使用外幣,本校若是使用了是違背政府命令。校長是學校負責人,做了違法事情,坐牢或任何處分,校長是最先一個。假使不用外幣,教職員工的生活又必有了很多困難:有段時間人民幣從五百元兌換一港幣貶至五六千元兌換一港幣。私立學校校長在經濟上無辦法,就做不下去”。私立學校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本來生龍活虎的陳校長也愈加無可奈何。他甚至后悔自己離開南開而來嶺南的選擇,在一份“檢查”中他寫道:“我曾經將這個意思向杜(國庠)廳長說,他勸我勉為其難做下去”,“可是在精神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始終是感覺到痛苦”。
1952年春,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拉開帷幕,嶺南大學與其他十余所具有外國教會背景的大學一并被取消。嶺大取消校名后被并入中山大學,其原有的醫、農、工、法、經濟各學科被調整出去,只有文、理二科進入新的中山大學,而康樂園變為中大新址。對于如此“大動作”的學科調整,陳序經內心不無保留,但他配合此項工作的進行,并無外在的抵觸。就個人而言,他得到解脫,終于一身輕松了。從這時開始到1956年的四年間,陳序經沒有擔任任何實質性的行政職務,被安排到中山大學歷史系做一名研究教授。此時,他所從事的社會學、政治學以及“文化學”,通通當做“資產階級文化”學科已被取消了,研究歷史乃唯一選擇。好在他對古匈奴史、東南亞各國史、西南少數民族史等均有興趣和學術積累,默默耕耘成為他這四年間的主色調。
有統計顯示,自1952至1966年間,陳序經撰寫書稿約二百五十萬字,計有《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匈奴史稿》、《西雙版納歷史釋補》及《中西交通史稿》等。其中,東南亞古史的七種由香港《大公報》社分別印行數百冊,作為贈閱本內部發行(至于他這些著作的正式出版,已是其身后之事)。作為一項參照,從1928年到1952年,他的各類寫作字數總計也不過約三百萬字。在“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奮與毅力令人感慨唏噓不已。據其家人介紹,他養成了早睡而凌晨四時起來寫作的習慣,多年不輟,即使日間肩負繁雜公務亦是如此。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陳序經與陳寅恪、姜立夫等人被評為中山大學一級教授,多為“嶺大舊人”。當時校內曾有人質疑陳序經的學術造詣。客觀地講,陳先生治學領域寬泛,似乎不很符合人們認同的學術專精標準。他的博士論文屬政治學題目,任教高校則以社會學立身,在南開經濟研究所,他從事工業化社會調查課題,終非嚴格意義的經濟學家,在西南聯大自創“文化學”,著作刊行而爭議不斷。難能可貴的是,他即使兼任校長,也不廢自身學術追求。著名的明代經濟史家梁方仲先生站出來解疑:“我原以為陳序經只是校長之才,但最近讀到他撰寫的歷史,可以肯定地說,他在學術上的功底無可非議。”
海外報章對陳序經離開校長職位長期“賦閑”有過失實報道,一些朋友于是勸他出國另謀出路,國民黨人士也來信鼓動他“脫離鐵幕”。對此,陳序經平靜處之,他自信沒有加入過國民黨,平生教書辦學,從未涉足任何政治活動,共產黨不會難為自己,因而仍在康樂園安心作學術研究。問題在于,陳序經雖無“官職”,但威望與影響仍在,原嶺南大學的教授們樂于與他接近,聽取他的意見,甚至有一稍嫌夸張的說法:陳寅恪惟陳序經之言是聽。如此一來,已經實行黨委制的大學權力機制,感覺遇到了挑戰,必欲“糾正”之。1955年前后在任的那位學校書記,用一種暴君的姿態對待高校知識分子,以致連“有涵養”的陳序經私下抱怨:有的人不僅要用腳踩在你的身上,而且還要用腳踩在你的鼻子上!
五
1956年對于陳序經來說是個轉折點,先是評為一級教授,后被國務院任命為中山大學副校長,還做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廣東省政協常委。這一變化,與那段時間知識分子整體處境的改善有關。據傳,主政廣東的陶鑄某次進京匯報工作,周恩來總理特別提起廣東有一位能聘到一級教授、善于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教育家陳序經,應當向他學習知人善任的本領。后來,陶鑄與陳序經幾乎結為莫逆之交。還有一個背景不可忽略:東南亞華僑籌建新加坡南洋大學,在全球杰出的華人學者中物色校長人選,陳序經被選中的呼聲很高,反映出他在華僑社會的聲譽和影響。此事對中共高層不可能沒有觸動,陶鑄就曾專程詢問陳序經的態度,陳表示自己無意于此。
再次擔任校長(副職),陳序經意識到自己是十幾所被解散的私立(教會)大學校長中唯一被重新啟用者(輔仁之陳垣先生另當別論),但此刻履行職責的情形與以前主持嶺大時已明顯不同。上有黨委會,負責思想政治和干部人事,各位正副校長各有分工,職責范圍明確具體,只要各安其職即可,全不似私立校長獨自當家的勞頓與風險。陳序經分管基建、房管和衛生,幾年間增建了體育館(臨時會堂)、生物樓,還擴建了學校醫務室。他上任剛剛幾個月,“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就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界圍繞“全盤西化”、鄉村建設與工業化以及大學教育諸問題展開論爭,陳序經一向以“敢言”、“好辯”聞于世,頗有所謂“一士諤諤”之概。可是在1957年“鳴放”時,他卻顯得比較謹慎,發言很遲,那篇發言記錄稿《我的幾點意見》6月間發表在《南方日報》時,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事態轉折已非常接近了。他的發言溫和含蓄,但也不失鋒芒。其中談到:高校內泛政治化現象嚴重,學術與政治不分,許多黨員用搞政治運動的經驗,硬套到高等教育上;許多黨員做事往往不講法律和制度,一些干部與其說是違法亂紀,不如說是無法無紀。他在發言中也強調,高校如果不要黨的領導,是很難想象的,問題不在于要不要黨的領導,而在于如何領導。曾有報紙點名批評這個發言,而陳序經在“反右”運動中竟安然無事。
粵省政治區位特殊,從清代中后期的“十三洋行”,到現代的毗鄰港澳(臺),加之沿海僑鄉居多,流動性與開放性明顯。其主政者需要靈活應對,為官也就比較開明。當年陶鑄肯于善待陳寅恪、陳序經等人,顯示出他過人的眼界和氣魄。1958年,為適應華僑子弟的入學要求,新暨南大學在廣州成立,陶鑄以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身份而親自兼任該校校長。其間,他多次訪晤陳序經,探詢辦學方策。經過幾年草創,學校初具規模。1962年底,陶鑄執意卸去兼任的校長一職,堅請陳序經接任。這樣,年近花甲的陳序經便開始了一段暨大校長生涯。
自1963年至翌年上半年,作為暨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主要致力于兩件事:一是提高教學和學術水平,二是建設校園。他籌劃自外校調入一批骨干教師,幾經努力,僅小有所獲,社會組織形態已然變化,過往的成功經驗如今難以奏效。他秉持教育管理要有“優容雅量”的想法,親自登門造訪暨大每一位教授,親自接待返鄉來校探訪的僑生家長。他虛懷若谷平易近人,對教職員工從不擺校長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車遠道來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員必定招呼上車,以至校長的乘用車被稱作“小巴士”。他在任期間,暨南大學作為一個特例,成立了校董事會,廖承志為董事會主席,成員包括費彝民、王寬誠、何賢等海內外知名人士。陳序經的“親和力”不僅在校內大行其道,也不斷擴延到海外人士中,無論相識與不相識,人們愿意與他商談各類辦學事宜。在不長的時間里,學校增設外貿系、東南亞研究所,籌辦醫學院,增加圖書儀器,擴大海外學術交流,華僑子弟回祖國讀書的人數明顯增多。
陳序經辦暨南大學有聲有色,本來是與國與民的大好事,但在極左年代里,卻無意中犯了政治上的大忌。還在他上任暨大校長之初,上邊即有責難聲:“為什么找一個黨外人士做正校長?”
六
1964年6月,突然下達調令:陳序經轉任南開大學副校長,調離廣東。陳序經不明所以,也極不情愿重返南開,他求助于陶鑄,陶鑄坦言此次自己也是愛莫能助,反而勸他北上就職為宜。究竟是何原因促成了此項調動?陳序經與粵省高級知識分子由來已久的密切關系,他與海外人士的互信合作,在一些人看來,已事實上形成與黨爭奪知識分子、與黨抗衡,影響惡劣,有人甚至貶稱他是“土皇帝”。其實,此類“反映”在極左和封閉的政治環境里始終存在,當然構成一種推動因素。
同年9月,陳序經懷著無奈的心情回到闊別多年的天津南開大學。世事難測,轉了幾圈又回到了原點,舊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將舊人當新人,他的內心難免感到苦澀甚至是自嘲。當時南開已有六位副校級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衛生之類,實際上無事可做。遇見西南聯大老友、歷史系教授鄭天挺,鄭問他現在做些什么,他答說練習烹飪技術(自作伙食),可見其初返南開之境況。1965、1966兩年的寒假及春節,他都回廣州與家人共度(中山大學住房保留)。“文革”初起,陳序經作壁上觀,以為與己無涉。豈料嚴冬時節狂飆突起,他被揪出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美帝文化特務”、“黑線人物”等罪名洶涌而至。隨后被抄家,住房遭強占,夫妻二人被趕至僅幾平方米的一小屋內安身,還被責令不斷地寫交代材料。陳序經的身體一向強壯,但此時卻急轉直下,聽力、排尿均出現障礙,1967年2月16日終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年僅六十四歲。
長歌當哭,總在痛定思痛之后。像陳序經這樣的學者型大學校長,歷經1949年前后兩個時代,卻均能創下優異辦學實績,至為難得。如此才華橫溢的教育家,卻被狹隘的偏見、俗陋的嫉賢妒能所戕害,時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為甚。陳序經的學養、經驗和操守,真正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遭遇極左權勢的忌諱和打壓,難以盡展其才,則是需要痛切反思的一個歷史糾結。
(陳其津:《我的父親陳序經》,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編:《東方振興與西化之路——紀念陳序經誕辰一百周年論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此文為教育部社科項目06JA880040之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