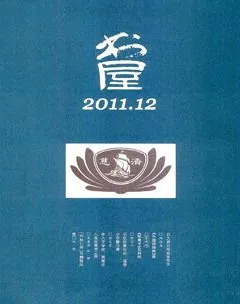愛如生樣柔弱
一
1928年浦江清在恩師王國維棄世周年之際著文《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憶及先師生前“素不主自殺”、“嘗譏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為意志薄弱,而社會之鋪張之者,可科以殺人之罪”——此處雖未指名道姓,明眼人卻一望便知,所謂“腦病蹈海之留學生為社會鋪張”,顯然當為1912年3月6日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發文《令陸軍部準建楊鄭二烈士專祠并附祀吳熊楊陳四烈士文》中的湘籍沉水自戕人士之楊毓麟、陳天華。
1911年8月5日湖南長沙人楊毓麟(1872-1911,字篤生,號叔壬,復號守仁)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沉,據說埋葬于ANFIELD公墓的楊氏墓碑上用英文給出的紀念銘刻并自戕理由乃是“因政治思想而死”(吳建華《蹈海烈士楊守仁》)。當年未及不惑的楊毓麟蹈海自殺的消息傳出令同志不勝訝異悲悼。黃興自稱“感情所觸,幾欲自裁”,痛失良友之情溢于言表;孫中山信函中也說“殊深悲悼。弟觀篤生君嘗具一種悲觀懇摯之氣,然不期出此等結果也”。
關于楊毓麟自殺原因,《孫中山全集》給出的一個解釋乃是:“楊聞廣州起義失敗并憤于日本瓜分跳海自殺。”與此類似,強調1911年4月27日黃花崗起義失敗對楊刺激至深、因之尋死的說法從當時到日后都非常流行。例如楊氏曾經主持的《民立報》當年8月25日特意登出《蹈海記者之痛史》,稱楊氏“精神痛苦,如火中燒”故而溺水。馮自由撰寫《革命逸史》也稱其因“神氣沮喪”而導致“舊病復發”。章士釗1963年3月18日寫于北京的《楊懷中別傳》間關提到這位與楊懷中關系最好的族孫,亦稱“守仁憤革命之失敗,自沉于海”。楊懷中即楊昌濟,楊開慧之父。
在偏愛湘人“精神”的錢基博先生解讀中,楊毓麟“發奮蹈海”一件直接后果就是讓當時同在英倫留學的湖南老鄉章士釗從“青桐”變成了“秋桐”,刺激之沉痛可想。
黃花崗之敗,志士駢首,而友人楊篤生同客英倫,聞之,發奮蹈海死。士釗所居黯然,感于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為“秋”焉。
章士釗少年因讀書所在之長沙東鄉老屋有稚桐一棵,皮青干直,日夕瞻對,油然愛生,又因諳習白居易詩之哲理高遠,所謂“自云手種時,一棵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故而自號“青桐子”。此際則因篤生之死改號“秋桐”,之后又之后,為回國操辦《甲寅》,論多違俗不為茍同之旨屢觸眾怒,再度改稱“孤桐”,獨立寒秋的況味一望無際,其所強調者,無非就是“吾行吾素,知罪惟人”、“天爵自修,人言何恤”,這是有使命感和擔當力的人才能知行的話。
錢基博先生著有《近百年湖南學風》,章士釗是他非常欣賞的人,與譚嗣同、蔡鍔合列一傳,三人或“明死生之故、變法不成乃殺身以殉所信”(譚),或“張軍國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聲大義”(蔡),或“權新舊之宜、與世相劘而叢詬以將莫齒”(章)——都屬不計后果之人,“下蠻干去”,這就是那一代湖南人,背后有“信”。與章士釗友好若此的楊毓麟,想來亦復如是。
不過,在篤生赴歐之前曾奔走效命的滬上,《民立報》編者根據1911年10月11日—12日所刊楊自書“絕命書三首”推斷,以為“先生蹈海之原因甚復雜,要為得神經病所致”,又代為訂正“留歐學界有謂其資盡投海”的流言,顯然此說也是當時流傳楊氏死亡原因一種。
《民立報》所刊書信三通的確均有提及健康問題,所謂“腦病復發”,然若細究語意,則另有深意大可玩味。如《致某某二君書》之一:
弟患急性腦炎,原因出于年長失學,好作繁思。感觸時事,腦病時發,貪食磷硫補品,日來毒發,腦炎狂熾,遍體沸熱不可耐。前禮拜往英格爾斯哥觀所謂博覽會者,以該地為一大制造口岸,會中機器館必×,可借研究觸發之×,乃徘徊其中,得益絕鮮,益感憤于科學根底之不可追補。在寓徹夜不成眠,欲得一手槍回國,因英語不佳,人地又生,不得,而行返 ( 北淀城)。后益郁悶不可制,于昨日買車票來利物浦,欲趁便船歸國,尋一二× ×死之。然海天萬里,非旦夕可達,而吾腦悶憤不可解,憤不樂生,恨而死之,決投海中自毖(文中“× ×”為脫字)。
此函楊毓麟還敦囑友人“國事大難,公等勉之,為將來自愛自經,講讀為賢哲所義。弟久欲解脫形神束縛,與他人無關,亦不計是非嘲笑也”——此一“不計”后果頗具湘人特色。
楊氏另一致某君書中同樣強調了“腦炎劇發,不可復耐,有生無樂,得死為佳”的狀況與心理,并另將存款一百一十鎊原為“歸國后為開一小小炸彈廠之起點者”,如今改變用途“濟黃× ×(按:原文缺字)兄之窮”。這位楊氏不肯明言的匿名同志,實即黃興,難怪黃對篤生之死那般心碎。
第三通遺書則為《致懷中叔祖書》,寫給當時同在英倫的楊昌濟(1909年與章士釗一起考入氵厄北淀大學就讀,參見楊毓麟1909年11月4日致母親書),“腦炎大發”、“狂亂熾勃不可自耐”、“迸亂不可制,憤而求死”的理由依然保留,楊毓麟死得似乎很平靜:“恩怨銷亡,萬事俱空,因緣頓盡,罵我由公等,不暇惜矣。”因為是寫給親屬的遺書,故該函多涉及身后家事處理,例如“旅費余三十鎊,寄歸與慈母,為最后之反哺”,甚至還將行李存放氵厄 北淀車站供楊昌濟以備取用,“以票呈長者,或可檢得一二英文書供用”。
其實,早在1909年6月20日楊毓麟致夫人儷鴻函中,就曾提及“請二哥買腦丸”,“但買到后,至今未曾服用過三分之一”,且說“倫敦天氣,入夏季以來,頗為清爽和煦。每日必往公園散步,身體甚屬相安,不以為苦”,當時病況似并不嚴重。該年11月4日前往氵厄 北淀修學前致妻函中甚至自稱“身體甚好”。盡管在楊昌濟的回憶中,篤生似乎身體先天就較文弱,“退然如不勝衣,乃能為景略雄談也”(氏著《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何況常年“奔走江湖,積年勞瘁,感憤時事,腦疾時發”,尤其執筆滬上鼓吹革命之時“報館事務異常繁瑣,精力大虧”。1908年赴英就讀后則“研習英文甚苦,腦疾愈甚”,“顧勤敏性成,不自制,明知用功過度于身體有傷,而苦學如故。嘗嘆少年精力徒費于國學一隅,于數學、英文未嘗致力,迨中年為之,其難乃十倍也。又嘗悔在日本時為感情所動,未能堅忍,至今日而科學根柢乃不得而追補也”。因此種種,楊毓麟似乎經常處在一種“憤甚”、“益憤悶不能自已”,“病乃日深”的境遇當中,他在私函中嘆息最多的就是“苦于無暇求學,至以為惱”、“甚矣求學之難矣”,且立志“耐勞勉學,從容漸進,不求速效”。那代人舍命“救國”、“以學救國”的愿望至少在情感真誠上是無可質疑的,假如我們還可以辨審他們措施是否得當。楊昌濟謂楊毓麟“每著一論,精神迸露,義氣凜然,讀者深為感發。君故工文辭,有遠識,其不可及處,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誠”,良有以也,著于1902年留日期間的《新湖南》無疑是此種文風的代表作,滔滔雄辯義氣慷慨,黃興在致孫中山信函中連連稱贊篤生“思想縝密”以“美材”譽之。
生死事大。1909年11月4日寫給母親的家書中楊毓麟還在內疚“慈親本年六秩大慶,未及歸國恭舉壽觴,惶恐無極。將來慈躬七秩大慶時,守仁準可潔膳馨饈,瞻依愛日也”——兩年之后,他的選擇卻令自己永遠無法完諾。
二
選擇主動赴死的人無論如何都是人類中的少數,而選擇在二十世紀初蹈海赴死的中國人中,著名的至少就有三位湖南人。我們不妨再趁此觀照一下另外兩位,陳天華(1975—1905)和姚宏業(1881—1906)。
1905年12月8日新化人陳天華在日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據說是為了抗議日本政府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1906年4月6日益陽人姚宏業在上海黃浦江投海自盡,是亦為“殉學”,殉“中國公學”的開辦問題,但同樣與日本取締留學生政策有關。姚氏早年就讀長沙明德學堂,1904年加入華興會,隨后東渡日本入宏文學院學習。1905冬取締留學生規則的頒布導致次年春姚宏業與王敬芳、張邦杰等人在上海籌辦中國公學以安置歸國學生。因經費等原因,中國公學開學后不久即遭困厄,姚宏業投江以殉,身后留有數千字遺書,道盡“為中國公學而死”的心思。
陳、姚二烈士可說是為了同一“意義”世界殞身,而后他們的安葬又引發了禹之謨、寧調元在岳麓山公葬烈士之舉,更間接引發了禹之謨的被逮與被殺。
禹之謨之死潛在原因即為他發動并主持了陳天華、姚宏業公葬儀式:二人之尸同時歸梓湖南后,禹之謨約諸同志,認為“今國家孱弱,兩烈士之所憤而死也,非葬岳麓山不足以驚國人”。據說屆時(1906年5月23日)湖南各校生徒分別從朱張渡、小西門兩處渡江,“皆白衣冠來”,“之謨短衣大冠,負長刀,部勒指揮。執紼者約以萬計,皆步伐無差”,“適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觀之,全山為之縞素”。此事日后在毛澤東的記憶中被稱為“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本會總記》,《湘江評論》第四期),而于風雨飄搖之清政府看來卻正是大忌,故有鉤織罪名逮禹入獄并最終絞殺之舉措。
刊登于1906年《洞庭波》上署名“湖南某君”的《挽陳、姚二烈士聯》,公認是禹之謨手筆,其中上聯透露出的奇異的“贖罪心理”引人矚目:“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義,應是湖南。烈士竟捐生,兩棺得贖湖南罪。”所謂“殺同胞”之湖南人,具體所指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同治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中興名臣”變臉為“湖南罪人”。盡管因為“洪、楊諸人崛起草野,其綱紀四方又未能秩然就緒”,于是曾、左諸公“慕撥亂之名誤反正之業”的“倒行逆施”稍有可原諒的余地,只是:
光復之際,三湘子弟建功獨多,未始非湔洗之一念有以激發之也。是故洪、曾睽而滿廷延,孫、黃合而漢起,湘之人才為輕重于天下者見矣。期間經營光復,屢起屢仆,百折不撓,飲刃不悔者,厥維湘人之特色。(佚名:《禹之謨傳》)
何止“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譚嗣同,禹之謨同樣選擇“吾輩作事,死,義也。列邦改政孰不流血?以吾為先導,可乎”,或者“余之軀殼,久已看空,何懼為?吾輩為國家、為社會死,義也。各國改革孰不流血?吾當為前驅”,至于“身雖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遺在世同胞書》),這日常“衣西裝,單衫革履,短發垂右”頭戴“拿破侖帽”的“晚清異類”,分明卻讓我們辨識出“三軍可奪其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的傳統儒家情懷。甚至在入獄之后他的持議依然就是:“大丈夫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禹之謨豈畏死者!若畏死則不至此地矣!滿廷方號預備立憲,余以興民權而遭此禍,不死幾個可慘之人,猶以為立憲可靠。”據說禹之謨常說一句口頭禪便是“舍命去干,決無不成之理”。
這里固然有性格原因。例如禹之謨也有“常思稍自斂戟”的時候,但“及臨事,則又飆舉奮發,置一切不顧”,乃至官中有事他的反應也是“往往出名爭執,詞意決裂”(曹孟其《禹之謨傳》),“暫藏豐城劍,待著羑里書”(靖州獄中自題)的愿望畢竟更多只是一種愿望。
然而這一時期渴望“赴死”的激烈情緒往往更成為一種“全民自覺”——更為準確地說,當是讀書識字尤其略通西學之人的“群體自覺”——這種“自覺”在湘籍志士身上又特別張大其辭。還是楊毓麟,在《新湖南》中他同樣以為“中興名臣”們“徇書生之小節而忘國民之大恥”:“西諺曰‘以血洗血’,此慘憺哀痛之言也。吾湖南負罪于天下也,以血購之,欲求所以揃雪前恥而開辟新世界者,亦當以血償之。”雖然“吾豈敢煽起殺機以菹醢我父老子弟之性命哉?吾抑豈忍汩溺世法,以任吾父老子弟之沉眠酣寢,席薪火以待焦灼哉”——這代人的激烈并非源于天性的忍苛或暴亂,“余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里有“世界潮流”的影響,“暗殺”風潮彌漫中外,楊毓麟專門在《神州日報》上輯有《記白人暗殺事件列表》,甚至我們的儒雅翰林、日后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概莫能外。禹之謨“靖州獄中自題”第二聯就是“師拿破侖,學瑪志尼”。1905年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行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同樣認為“寧犧牲一己肉體”、“樾請為諸君子著先鞭,更愿死后化一我而為千百我,前仆后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烈士吳樾意見書》,載《民報》第三號)。吳樾作為“中國炸彈第一聲”被稱為“(楊)守仁之密謀”。楊毓麟本人干脆就是第一個自學制造炸藥的革命黨人,并因此失去一只眼睛,他還一度曾是“北方暗殺團團長”:“研究爆發物十余種”(馮自由《新湖南作者楊篤生》)、“黨人能自造炸彈,自守仁始”(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但依然提醒讀者諸君不要因此以為這些“革命黨人”就是一群暴虐殘忍之徒:“夫破壞者,宇宙之悲谷也,吾不忍于湖南見之,吾亦何忍為湖南言之?雖然,是烏可以已哉!茍可以不至于暴動,即毒蛇鷙獸,亦決不至于暴動也”、“求文明者,非獨賞其價值,又須忍其痛苦”(楊毓麟《新湖南》“第五篇:破壞”)。他們何嘗不渴望“非暴力”生活?
三
1908年8月12日-1910年4月14日,身在英倫楊毓麟有十數通書信寄給母妻兒女及弟殿麟,所謂“性至孝,對其家恩義甚篤,然因國家多難,常懷舍身殉國之志,公而忘私,近十年來居家僅四日也”。持論激烈的楊毓麟此間寫給親人的信函,殷殷切切督責備至,“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
這研制炸彈第一“黨人”也會從國外購置新樣手帕(倫敦萬國博覽會紀念品、CrystalPalace紀念品)送給妻、女、母親,給兒子的禮物則是“美術郵票一二枚”。他向妻子索要“小照”,顧念她身體不佳,甚至在家書中開列具體方法要妻子遵囑“切實調理”(1909年10月24日致女克恭函),并海天萬里寄上“西洋藥水”(1909年12月14日致妻函)。他從倫敦寄給妻子明信片,所錄“己酉九月”(1909年10月)舊作三首,嚴肅節制卻深情內斂,自有一番特殊美感:
行吟自笑吾意狂,偃蹇相偕有孟光。
一事如君差不惡,斫頸衛足也無妨。
已辦要離共一邱,發春便買入吳舟。
香篝酒碗如相憶,黃浦江東碧澥頭。
篋劍崢嶸欲化龍,酒徒歌哭漫相從。
生平不作牛衣泣,應解兒夫意未慵。
不輕不狂卻有情有義。身處異域父親對兒女讀書之事籌劃細致理性,百年之后讀來如在紙面:
現在我雖流落江湖,然自己兒女,萬無令其叨擾外家之理,不獨于心不安,亦于事理不順。且令兒女依賴外家,絕非好氣象。凡人貴自立,不宜使依傍他人作生活。英國人教養小兒女,一切必令小兒女自己支持自己,自小習慣,自然養成獨立自治性質。此事不可姑息,以為兒女小,到學堂怕人欺。且在外家叨擾過久,大有竭忠盡歡之嫌;實屬無以酬答恩慈,此事于我心極為不安。茲特寄上英國金鎊十鎊,照現在鎊價,總可換百一十元以外(或百二十元外),請少奶從速將兩兒分別送入學堂。至八月節,如學校假期中不好住,可令兩兒暫寄居外家。如其可住,仍住學堂。以后總須入學校住宿讀書。以上系我決定如此,少奶務須依我此信行事,且不可仍令兒女叨擾外家。(1909年6月20日致夫人儷鴻書)
依照此后楊毓麟寫給兒女的信函判斷,其妻應該依從他的決定將兒女送入學堂,或者就是“懷中叔祖”所薦之“規矩甚為謹嚴,辦理亦得人”的周氏女塾(即周南女校前身)以及“功課亦好,管理亦為得法”的明德學堂。此可參見楊毓麟1910年4月10日致女函。
寫給女兒克恭信中,除囑咐女兒要特別留心算學、英文、體操等“西學”科目外,父親的囑托細膩到了瑣碎的程度,他甚至會將如何正確稱呼外公外婆祖父祖母叔舅諸親、如何預防傳染病的問題在信中一一向兒女交代清楚(分見1909年6月21日、1910年4月1日致兒函):
汝到學堂寄宿后,自己須要切實學好做人,切實用功求學,不可在學堂內與同學諸人終日閑談亂講,不可與同學諸人鬧意見。待同學諸姊妹宜格外客氣,彼此以求學用功相勉勵。見學堂監督教習,尤宜恭而有禮,恪守校訓,不可違抗。一切日用飲食起居,須有一定規則,按照一定鐘點。鐘點是人生在世一件必須謹守的事,人無一定做事鐘點,便是不能學好的憑證。(1909年6月20日致女函)
此函并以父親的威嚴為女兒定下“規矩”:“平日除與諸女同學往來及休息往來外家請安外,不準汝與男學生往來,亦不準汝妄向別的人家行走”——這并非只是一種“時代局限”,時隔百年之后,倒是倫理生活已經“開放搞活”到無邊無際的我們該多反思一番“男女有別”的意義與制約。
對兒子克念,除依然囑咐“切實用心讀書習算,極力學做好人”之外,更叮嚀“世上道理多,事情多,無論是何等絕頂天才,不過曉得十萬分之一,學得百萬分之一”,必須“細心研究,切實履行,時時刻刻以扎硬寨、打死仗方法對待之”,“須知世上聰明好漢多得很,聰明好漢多,切實成一個有用的人者卻不多。還是資質平常的人,切實用功,不成就用功有用人物不止,拼死去做,倒做得成一半”——此語深得湘人性格“吃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之精神真諦。尤當注意者,是楊毓麟此函除繼續吩咐兒子不可拋荒“算學、英語、體操等要緊功課”之外特別長篇大論對于“中學”尤其“經書”的態度:
近日無知少年醉心歐化,一言及《四書》、《五經》,便有吐棄不屑之意,殊為大謬。此輩只知有歐洲,卻忘記得自己是中國人。歐洲各國,現在中、小學校,每禮拜必須有數點鐘講解耶穌教《圣經》。……《五經》、《四書》為周秦以前政治、文化、歷史、道德、倫理之薈萃,于世界各國中流傳最古老之學說,實蔚然為一大宗者,而可弁髦土苴之乎?
此即我們的確見識了一個岳麓、城南、校經書院學子(并曾“中舉”)的知識背景與價值判斷。與此類似,《新湖南》中楊毓麟雖然對“鄉愿陋儒”不假辭色,對“新學小生”同樣嗤之以鼻。我們更再次窺見湖南作為“理學大省”在清末依然濃郁的修養與根基——《厚道還是霸道:楊昌濟與“湘中二楊”》一文中于此我已三致意焉。難怪楊毓麟寫給女兒信中更特意強調“辦事”之重要:
欲作國文好,必須熟讀古人名作,尤宜用心向事情上切實考求事理之是非、辦事之條理及說話之次第。知事理是非,知辦事條理,不知說話次第、亦算不得好文章。若并事理、是非、辦事條理之不知,只是放屁,不是作文。是非及條理不是在紙上讀來的,卻是讀書后再要用心對一切事情上研求的。汝必知此,乃可讀古文,乃可學作國文也。(1909年10月24日)
1910年4月1日致兒子克念函中,楊更嚴厲批評“中國各種小說”:
尤不可貪看無聊小說,耗損一生有用之精神,墮壞一生不可纖毫污損之道德。中國各種小說,皆于人生應有之知識,及應完具之道德,毫無裨益。而其引動人生不肖之思想及無恥之行為,則其力量大至不可思議,中國現在人心腐敗,達于極點,皆只是此種小說魔力之結果,吾兒萬萬不可自誤。
四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此語,的確“不可不猛省,不可不深思”。陳天華《絕命書》中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痛陳“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一切規則自矜,至于以報國為名而私德盡喪——這些話掩抑在清末民初的“主義”當中似乎很少被提及。然而,這些話與同為湖南人的“平江不肖生”《留東外史》中對留日學生種種不檢點生活的刻骨描畫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系?陳天華之死與楊毓麟之死是否只有“為政治而死”一種解釋?楊毓麟好友章士釗之后同樣激烈的“轉身”是否存在某種必然?
由大書特書《黃帝魂》鬧退學搞革命的“小憤青”到留英歸來一度職掌民國教育司,和彼時日益高漲的新文化運動意旨乖離,章士釗不肯曲學阿世以殉時風,一路走來罵名不斷——“政治信念全變”,完全否定了自己從前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開始公開抨擊代議制,要求廢棄舊國會與舊法統;鼓吹以農立國,反對工業化;鼓吹禮教復興,反對新文化運動。1924年11月章士釗出任段祺瑞政府司法總長,1925年4月起兼任教育總長,直至1926年4月段氏下野,章也隨之結束了為時一年半的從政生涯。這期間章所推行實施的一系列教育政策,無論出發點是好是壞,卻都遭到了全國上下特別青年學生的一致反對,“驅章運動”接連不息越鬧越大,其最著名者自然是1925年8月“女師大風潮”。
所謂“銳意復古,反對新潮”、“以武力解散女師大,侮辱婦女人格”,章總長是站在“支持校長(即被魯迅罵到狗血噴頭類乎虔婆的楊蔭榆女士)”的立場上的,于是“凡所措置,類屬乖異”,諸多名校恨不能一致抵制章氏命令,脫離教育部管轄。“女師大風潮”差不多已由教育問題轉化為政治風潮,成為當時北京知識分子最為關切的所在,章士釗本人亦陷入與全國教育界為敵之窘境。
遭受挫折若此,章士釗非但未放棄既定政策,態度更趨強硬。1925年8月底,在章氏主持下,段政府下達整飭學風令。10月底,教育部會議決議展開“讀經運動”,規定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讀《論語》等儒家經書。別看幾十年后當下中國果然已在踐履章總長決議大小頑童重新補課“三字經”,如此舉若在當時,卻只有更遭群起攻擊的份兒。吳稚暉宣稱“整頓學風宜也。顧章行嚴何人,足言整頓學風乎?足解散女師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魯迅指出章士釗并非真信讀經可以救國,不過以此欺人、便利其反動統治,其心可誅。11月28日北京工、學各界數萬人召開國民大會,以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號召,要求段祺瑞下野,懲處賣國賊。接下來示威學生即轉往章氏住宅:
一擁而入,遇物即毀,自門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由笥而揓,無鍵與不鍵,凡服用之屬無完者;先肆其力而搗之,次盡其量而攫之,卒掃聚所余,相與火之。
各界群眾又于次日搗毀一向同情章士釗言論的《晨報》館——真真是一個動輒“激烈”的時代——其源頭難道不該追溯晚清?不知曾經“激烈”的章總長此即是否曾有“作繭自斃、請君入甕”之嘆呢?
后世我人閱讀歷史的傷感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情緒狂熱持續激動之下的青年學子,似乎少有人愿意知道或愿意記得,這位讓他們必欲“驅之而后快”的“保守型”總長二十多年前(1903)同樣“愿從天假殺人柄,豕盡中朝舊輩流”,其激進奔放乃至“暴力”傾向何嘗在他們之下?他甚至發表過一篇《殺人主義》,要“借君頸血,購我文明”。
1903年4月,就讀于江南陸師學堂的章士釗,因校方拒絕學生改良堂規要求事,毅然決然率領三十多名同學退學至滬,“蟻附愛國學社,公言革命”。這批“小革命”中就有日后更以激烈著名的陳獨秀。1903年5月章士釗受聘為《蘇報》主筆,“當時宗旨,第一排滿,第二排康”,“鬧革命”鬧得沸反盈天——謂予不信的讀者敬請參閱章氏本人《黃帝魂》一文。甚至在《蘇報》館查封后,1903年8月章士釗在上海又創辦了有“《蘇報》第二”之稱的《國民日日報》,同時設立東大陸圖書譯印局,編印出版多種宣傳革命和反滿書籍、傳單。章士釗也曾是“暗殺團”骨干分子,其同事自然包括楊毓麟、蔡元培。
然而,不久以后,章士釗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據說這跟“萬福華刺殺案”后章士釗獄中反省有關,“才短力脆,躁妄致敵”,也算“血的教訓”了。從“學書學劍錯雜來”到“力脫黨籍為書生”(章著《草新湖南案成放歌》),他悟證了“黨人無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答吳稚暉先生》)。惟其如此,你才會明白,何以章士釗在東京能如此堅決拒絕加入“同盟會”,即使同盟會祭出“美人計”、讓“近代四公子”之一吳保初的女公子吳弱男前去勸誘都未成功,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撮合了章、吳締結婚姻。此后章士釗由“廢學救國”轉身一變而成“苦學救國”:赴日、赴歐……之間章士釗還經歷了一個對西方憲政體制從神往到批判的過程(即其二次革命前后為岑椿煊充任謀士之時)。總之這個湖南人每次“翻邊”都很徹底、也很固執。再之后的回歸,就是如上這個“保守主義精英”了。
這就是根性,也更是修養,章士釗跟他的盟兄章太炎類似,無論他們曾經一度多么激烈宣稱:“此輩學生,只須日習體操已足,凡考生洋奴所謂學問,了無用處,反而擾亂社會”——他們卻始終都會再度成為讀書人和“學問家”:他們深知“文化”不能“革命”。“文化”只有一脈相承、厚積薄發、春秋代序、生生不萎。
二十多之后,1925年章士釗回憶往事:“今試思之……(當年罷課學生)由此失學者過半,余亦未見別有所就。”看來,章氏對學生運動一直持有懷疑與反對的態度原本屬于痛定思痛。何況,在章士釗看來,“五四”以后“學風之壞,已臻極地,國學垂絕,士德全無”,教員“植黨構煽”,學生“荒學踰閑,恣為無忌”,以致“校紀日頹,學績不舉”,至使“道路以目,親者痛心”。客觀看來,這位老資格的“革命黨”如下忠告何嘗不佳:
時事之艱難,決非在校之學生所能普濟。故學生愛國運動,只宜處變而不能處常,若必據為典要,嘗試頻頻,恐將一面激起社會之反感,一面荒廢學業。
實際上,章士釗此種反思行為在他1905-1911年陸續留學日本和英國時候已經開始,由極端的革命論轉向平和的調和論:
十八年前,愚持極端之革命論,并主廢學以救國。后亡命往東京,漸變易其觀念,竟由廢學救國,反而為求學救國。己因與革命老友握別,留學英倫,而極端之革命思想,變化不少。(《新時代之青年》,1919年11月)
章士釗深心以為中國現在“倫紀凌夷”,士不悅學,學風囂張,再不及時加以整頓“邦基將淪無底”,故而才會采用較為強硬手段。至于女師大學生,也屬“閨門稚質,少不更事”,既然“幼弱可憐”,則“且類有家督保人,交相維護”——這種“家長”口吻,激怒當年大張旗鼓的“女新青年”倒也正常。
1923年著于德國柏林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章士釗有言,“人言黑白吾不問,唯詢報國究何如?由來功罪難此斷,刀筆英雄本水炭”,后世我人閱讀先賢著作,此意甚為關鍵,要不得將彼時人物因意見不同導致的筆墨官司一味當真,“報國”這一愿望往往對于敵對雙方乃至幾方都是真切的,至于具體意見合于實際或理想高蹈、急功近利或大而無當……則只能具體情境具體分析,皆以“因緣”現。同為“辛亥老人”的蘇淵雷先生曾將章士釗“搞學術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凱又討袁反袁、不加入同盟會又沖鋒在前”規約為真正的“獨立精神”,不因私誼負公仇,確是發人深思的見地。
五
楊毓麟之死后七年、王國維之死前九年,民國初年還有一個人的死曾經驚動了國人的心: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濟巨川先生自沉于京師積水潭——現在那個因“新三里屯”什剎海的煙柳繁華而著名的所在。
巨川身后遺書成扎,反復論證乃為“蓄志一死,殉義救俗”、“(吾之死)實痛乎繼清者不行仁政以及民,重負夫有清遜位之美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圣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于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效忠于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于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于世界。(《敬告世人書·戊午年第壹》)
當此之際,后世我人難道不該對“主義”二字另生一種理解與敬畏?何謂“專以世道為主義”(《敬告世人書·戊午年》)?和楊毓麟類似,梁濟對于“中西”優長并非沒有的見,早在1892年,三十三歲的梁濟即“留心時務,雅以西學為急”:“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1898年為次子煥鼎(即漱溟)開蒙,也是首選《地球韻語》以言世界大勢而非尋常四書五經督課童子,更諄諄以教子弟出洋為言。這與他二十年后(1918)主動赴死之前慨嘆“吾觀一般無骨之人,對于國俗所尊信斥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斷為中國必亡之真因,欲救此亡,當從心術根本上起。吾臨死匆忙,雖反覆言之,猶未盡萬分之一也”(《敬告世人書·戊午年第壹》)并無抵牾。厚道誠摯如巨川,晚清日記中對清朝政府“吾君吾相”之“并無真實憂勤之意”的怨懟之語在在皆是。
同樣作為父親,梁巨川選擇主動赴死之前明言“我非不知世間有生可以行樂,求死實為至苦也”(《再告世人書》),然“所欲有甚于生者”,“至于不惜死以求寤人,或真見有不可終日之勢”(《貽趙智庵書》),“做事不避迂拘,思喚起世道人心,去澆薄而就誠篤,不惜以性命貢獻于社會”(《別竹辭花記》),“國性不存,我生何用”:“故雖有極可喜之家庭,而不敢戀,不能不犧牲快樂以明志,所以動世人之省察也”。所謂“國性”即“天理民彝,為圣道所從出者,是吾國固有之性,皆立國之本也”,大約仁義廉恥、誠敬忠信等皆是,“較之空言世界大同政治高尚徒夸目的反召紛紜者,其功用不可同日而語”。他安靜地安排自己的死亡,自行“檢點裝殮衣物,安排客廳字畫,備吊者來觀,以求知我家先德”,他滿含慈愛認證兒女孝順有為、“我之家庭,真正雍雍熙熙之家庭也”,明己之自戕非出個人生活困頓,而是“發明正義”,他甚至細心安排好兒女各自歸家時間、便于他們料理自己后事:“余見彼面,彼收吾骨。”(《敬告世人書·甲寅上半年》、《留示兒女書》、《戊午遺筆》)
梁濟之死再九年之后,“奮身一躍”于頤和園昆明湖的王國維也是一位父親,身后留有八個兒女,其中四個尚未成年。觀堂譏諷乃至責備楊毓麟等人蹈海為“意志薄弱”之時,是否預料過自己居然在十六年后同樣選擇了自殺、甚至同樣選擇了自沉——魚藻軒前的池水較之大西洋里的海水,無疑淺陋且渾濁,然而據說從入水到撈出只有不到兩分鐘時間我們就失去了當年“清華四導師”的首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觀堂遺書之冷峻簡潔,更在以上諸公之上。對于身后妻子兒女的安置,也更顯冷靜、甚至冷漠:
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 父字。
觀堂“奮身一躍”真就如此清淡通脫?弟子浦江清謂恩師“抑余謂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為哲學上之解脫”、“當其奮身一躍于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此一剎那頃,先生或有勝利的微笑歟”難免為尊者諱的意味,讀來萬分牽強。實則浦氏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斷制,才會在文末搖擺出“奔逝而去者,昆明湖萬頃之洪波,而默然無以應我也”這樣坐臥不安的糾結。
因為陳寅恪蓋棺論定,“觀堂之死”似乎也早成為一樁毋庸置疑的定案:所謂“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其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遙想巨川先生“先自治,后自由,尤為要緊”(《貽趙智庵書》)之遺言,清末民初這番關于“自由”的思想認證與行為掙扎乃至生命搏擊,真真令人不禁人琴之痛。
小觀堂十歲卻先觀堂十六年而死的林覺民(1887—1911),“廣州起義”就義之時年方廿四,傳說最終決定將其處以極刑的兩廣總督張鳴歧亦因愛才浩嘆“(林)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當年“三月念六夜四鼓”林覺民留給后世一封情真意摯的《與妻書》:
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愿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卒不忍獨善其身。
這“家書”兼“情書”蕩氣回腸,生氣拂拂,至今讀來才明白據說能用英文演講、通曉日語、德語的“美少年”性情根本卻依然是鮮明的儒家“民胞物與”、“兼濟天下”、“推己及人”的根本立場。這封信的接收人、彼時身懷六甲的林妻陳意映哀傷于對丈夫的思念不久郁郁病亡。民國元年(1912)2月11日林父孝穎在福州白塔寺為子發喪。3月福州召開“黃花崗烈士追悼會”,老父感于同鄉林秀軍“晚風吹夢作秋涼,浴血何來痛國殤。肯為艱難雙束手,不勝哀怨九回腸”之挽詩,和以“趙佗臺迥北風涼,藁葬荒丘半幼殤。一死自酬他志愿,初聞直碎我肝腸。黃花吊客傾鉛淚,白發哀翁對影堂。東海明年櫻再放,君行應念舊同裳”,并親寫《挽子》一聯:“湯武非圣人,千古相傳謬論;彭殤同一視,而翁何愛殘年。”勉自豁達之外,暮年喪子的無限傷感又怎能輕松。
毫無疑問的是,清末民初這些出于不同“政治”而有類似“主義”自愿赴死的人們,其實都是一些正直、善良、嚴于律己、刻刻反省乃至對他人與社會充滿愛心的人。惟其如此他們才“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國人之道德心本薄弱,欲其辦事諸人耐勞耐苦,潔己奉公,顧全大局,為社會增幸福者,恐不多覲”、“吾輩丁斯時也,厭世主義未可形于言,并不可存諸心,尚有大責任在也”(禹之謨《與澤、蔚二弟書》),類似的痛切,楊毓麟系列著述例如《論道德》、《新湖南》都有反覆申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第七十六章)。“愛如生樣柔弱”,“愛”只有如此柔弱、只能如此柔弱:面對現世的堅硬,“愛”的具體踐履與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依然是個必須深謀遠慮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