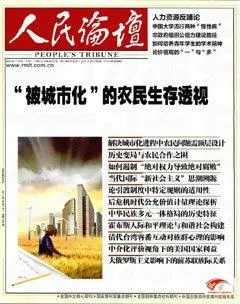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特征
【摘要】中華民族的形成特征是文化認同:神話認同是其形成的前提,身份認同是其形成的標志,國家認同是其形成的結果。中華民族的關系特征是互相依存,文化依存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經濟依存是其物質生活的基礎,政治依存是其共同命運的關鍵。中華民族的發展特征是融合統一,理論升華是先導,共同奮斗是動力,安定強盛是結果。
【關鍵詞】中華民族 多元一體 文化認同 互相依存 融合統一
幾千年來,中華各族人民在祖國大地上自強不息、團結拼搏,共同創造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建設了幅員遼闊的錦繡河山,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長期發展進程中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正確認識這一格局的歷史特征,對于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的形成特征是文化認同
神話認同是中華民族形成的前提。著名德國哲學家謝林認為:“一個民族,只有當它能從自己的神話上判斷自身為民族時,才成其為民族。”①創生神話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文化之根,只要找到了這條根,就等于找到了自己與文化母體相聯系的臍帶及其祖先譜系。因為有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便有了許多民族首領因卵而生的傳說。《晉書》中記載的北漢之主、匈奴人劉淵因卵而生的神話傳說便是其中一例。此類神話傳說不但經常發生在魏晉之前的北方民族統治者身上,而且直到宋元之際依然余波未息。《蒙古黃金史》中寫道,成吉思汗誕生時曾有玄鳥飛來,發出“成吉思”的叫聲,連續七日而不息,直到它足下的玄石自動裂開,出現了一方龍紋漢字玉印。這些神話傳說長期被史學界斥為“荒誕不經”,甚至是“封建迷信”。然而現代史學家們終于發現,民族創生神話本身體現了先民的文化認同和集體記憶,其本質上的真實與意義,為史料考證和考古發現不可替代。這種使民族共同體中不同民族成其為自身的內在精魂,正是其認祖歸宗的終極標尺。《史記》華夷諸族共為“炎黃子孫”的記述,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分離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據與前提。鮮卑自認為是黃帝之后,契丹自認為是炎帝之后,而匈奴則認定其先祖為夏后氏之苗裔。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的一體主要不是種族血緣的一體,而是文化的一體,所以炎黃五帝被稱為“人文始祖”。正如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陳寅恪先生所說,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則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凡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那種試圖僅僅通過血緣考證來說明民族屬性的努力,并不具有普遍意義,否則便難以達到“多元一體”與“炎黃子孫”這兩個命題之間的邏輯統一。
身份認同是中華民族形成的標志。范文瀾先生曾經指出:“漢族無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體。它的祖先多得很,不僅傳說中的黃帝族是它的祖先,而且所有融合進來的任何一個民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凡是現在兄弟民族的祖先或者是已經融化似乎失蹤的古代民族,都是漢族的伯叔祖先或者是祖先的一部分。”②中華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首先是自我認同。對于各民族成員來說,以炎黃為核心的五帝系統如同一座輝煌無比的金字塔,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是命運的歸屬,也是一種無尚的榮光。由于遠古先祖與圖騰神話的絕對權威性和強大吸引力,可以把現世的統治者與神圣的先祖聯系在一起,使文化關系得到血緣依附,在宗法制度的條件下為實現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提供了依據。在經久不衰的民族沖突、雜糅、融合過程中,一些分散孤立的民族單位被淹沒,許多新的民族實體也在誕生,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相連的民族統一體,彼此認同順理成章。所以,在清末民初的 “華夷之辯”以后,產生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多民族統一國家表達方式。
國家認同是中華民族形成的結果。各民族由文化認同而成為炎黃子孫,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當然一員,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享有了成為天下主人的資格,具有了統一天下的神圣權利與使命。這些民族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便不能容忍被稱為“胡虜”、“外夷”,也不甘心于僅有的一席之地。所以他們大多自稱“中國”,并且以舉起中原正統文化的旗幟統一中國為己任。這說明不僅是漢族,而且各民族之間早已達成明確共識——“中國”是一個諸族共有的政治共同體,其不可質疑的永續生命和至高無上的神圣性,超越于所有民族和具體王朝之上。元朝末代皇帝妥歡帖睦兒退居上都,曾把一首詩交給朱元璋派來的信使,詩中寫道:“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江山易手之際并無“亡國”之恨,反而表現出前朝君主對后起之秀的禪讓、嘉許態度。朱元璋也對大臣們說過,元“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之類的話,而且他從來不提明朝得江山于“異族”之手。所以,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形成的必然結果及其不可逆轉的發展主流。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而產生,中國走向統一的歷史大趨勢因此而不可逆轉。
中華民族的關系特征是互相依存
文化依存是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共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本質特征和活的靈魂。因為有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支撐,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才能對多民族統一國家實施有效治理。然而,如同漢民族本質上是中華各民族的融合體一樣,漢文化作為中華主體文化的突出代表,也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體。不能認為游牧民族都是原始的野蠻人,假定他們的生活狀態處在農業文明興起以前很低的水平上。事實上,牧業文明與農業文明具有根本不同的、不可簡單進行高下類比的發展道路。不同文化在傳播、撞擊、滲透與互補中實現生態上的凝聚與升華,這是中華民族文明不死、不可戰勝的秘密所在。
陳寅恪先生曾經說過,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注入于久遠而陳腐之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有歐洲騎士文學之盛況。中原漢地在歷史上無疑是中華文化的聚寶盆,正是不同文化的沖融和注入,才使它有機會源源不斷地吸收到新鮮血液,得以吐故納新,從而激發出萬古常新的活力。因為有了各民族色彩紛呈的文化交融,才有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繁榮。正是由于蒙古和西域等北方民歌與中原文學藝術的融匯,才有元曲和雜劇所鑄成的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又一座高峰。
經濟依存是中華民族物質生活的基礎。如果以甘肅天水為中心,北至大興安嶺,南至云南騰沖,可以將中國劃分為兩大部分。東南部是處于濕潤半濕潤地帶的農業經濟區,西北部主要是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帶的牧業經濟區。天然地理條件造成了農耕社會與游牧社會經濟的不同類型,從而確立了相互之間必然的依存關系。為了保障生存需要所進行的經濟掠奪和貿易往來,產生出超越長城的巨大力量。所謂掠邊入寇,你來我往,不過是由于彼此需求的引力作用,南北民族之間可謂是不打不成交,越打越緊密。由于北元的存在,明初南北關系極為緊張,朝貢互市無法進行,致使蒙古牧民連衣服都穿不上。俺答汗不得不采取戰爭手段來獲取中原的農工產品,以解燃眉之急,同時也走上了艱辛曲折的求貢之路。明廷亦有對草原物產的實際需求,且不愿再動兵戈,終于同意恢復互市。據有關史料記載,從此蒙漢人民交易不絕,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里,無烽火之警。俺答汗病逝后,蒙古右翼舉部痛悼,明廷亦賜祭優恤,這都說明他的作為符合民族依存的客觀要求和南北民眾的共同意愿。
政治依存是中華民族共同命運的關鍵。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盛世”,都以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為前提。12世紀中葉元朝的空前統一,不但結束了安史之亂后五百多年的血戰與紛爭,而且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如《元史·地理志》序所說:“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東,南越海表。”大都(今北京)的建造,確立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中心。由于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當時中國的海船制造技術和海洋航行技術領先于世界,海陸通道的開辟規模空前,貿易伙伴達到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元朝滅亡之后,中國南北長期處于紛爭狀態。也正是因為清朝的統一,才有了所謂的“康乾盛世”。因此,以摧毀三皇五帝系統及其華夏一元觀念為發端的“古史辨派”,又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的民族危亡關頭,發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吶喊。
中華民族的發展特征是融合統一
理論升華是中華民族融合統一的先導。從神話傳說到文字正史,從左丘明到司馬遷,中華諸族同為炎黃五帝后裔的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到了唐朝,“華夷一家”的思想主張進一步發揚光大。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唐初名將李靖亦言,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為生,故常習戰斗,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宋遼金元時期,作為歷史發展的必然反映,“漢族正統觀”在史學界失去統治地位,“中華統一正統觀”的集成性思想成果開始出現。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史論篇》中,以洋洋近千字對這一觀念作以闡述,提出了“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和“但居其功業之實而言之”的代表性觀點。據《大金吊伐錄》所載,遼天祚帝在給金朝的降表中還不忘作出“奄有大遼,權持正統”的聲明。郝經在《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中寫道:“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者,則中國之主也。”這是對當時形勢發展必然性的闡明,也為忽必烈入主中原提供了理論依據,即“有公天下之心,宜稱為漢。”這里所說的“漢”,也就是“中國”。清乾隆皇帝在御批通鑒時寫道:“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同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③他還說:“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④“中華統一正統觀”和“天下一體”國家觀念,既是民族融合的產物,也是推進國家統一歷史進程的思想先導。
共同奮斗是中華民族融合統一的動力。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史,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奮斗史,而不是哪一個民族的“侵略擴張史”,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偉大的史實。歷史在恩格斯所說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的作用下前進,各兄弟民族在相互爭奪、相互統一、相互交融過程中共同譜寫了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的光輝史詩。
歷史上中原民族或者說漢族的作用自不待言,其他民族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從南北朝到隋唐,是一個民族融合的高潮時期。令國人世代驕傲的大唐,實乃諸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杰作。建立唐朝的李氏集團本身并非中原民族,而且起兵之初的謀臣武將亦多為胡族。蒙古組成由諸多民族構成的武裝力量,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滿族同樣是依靠諸多民族的支持與合作,定中原,平“三藩”,撫蒙古,安青藏,重新統一南北,又經康、雍、乾三代帝王之努力,使多民族統一國家得以鞏固。
實現國家的統一歷史進程往往與民族斗爭相伴隨,許多民族都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但正如范文瀾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斗爭與融合》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在當時,作為敵對的民族或國家,經常殘酷地進行過斗爭,今天看來,卻是兄弟鬩墻,家里打架。”我們應當無比珍惜祖先流血犧牲共同創造的歷史成就,而沒有理由把這種犧牲作為制造民族隔閡的借口。有人曾把元朝和清朝的統一戰爭視為“侵略”,把這兩個王朝的統治視為異民族對中國的統治。日本侵華時曾編寫過所謂的《異民族統治中國史》,企圖借用此類說法和“歷史事跡”,宣揚其侵略和統治中國的“合理性”。歷史的教訓應當記取,不應當讓那些持有民族偏見的謬說混淆視聽。
安定強盛是中華民族融合統一的結果。中華文明以其獨有的連續性得以發展,首先要歸功于民族的融合與國家的統一。有了這條歷史線索的有力貫穿,它才未被內外因素的干擾和沖擊所中斷。而且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國家統一與民族融合,都會有力增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在唐朝,突厥、匈奴、鮮卑、高句麗、吐蕃和西域諸族人才都能為國家所用,而且外國人也可以在政府為官,形成了不同民族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交流的社會環境。他們在睦相處中取長補短,各盡所能,以堪稱輝煌的偉大成就,在短短百年的時間里鑄成一個當時世界上最為強盛的國家。同時中原與邊疆地區文化技術也得以廣泛交流傳播,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和進步,也豐富了中原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忽必烈及其元朝,留給后人的最大遺產恰恰是這個偉大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本身。正是這次中國歷史上最大范圍的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留下了最為遼闊的疆域可供子孫后代去耕耘,使中國這艘雄偉的東方之船,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顛撲不破。輝煌一時的羅馬帝國,以及曾經與唐朝一度并峙的阿拉伯帝國,在分裂以后就不見有統一的國家再生。而在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的古代歷史進程中,盡管數千年間分裂的陣痛反復發作,但每次分裂的結果總是迎來更大規模的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最后由清朝劃上了不可改寫的句號。那時鞏固國家統一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推動,更重要的是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基于共同命運的必然選擇。
列寧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是要使各民族融合。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決定了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而且鞏固國家統一和加強民族團結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各民族同胞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民族已經成為“國族”,民族之間的關系實質上也是民族與國家的關系。祖國的每一寸土地,都屬于各族人民,而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國家與民族有如父母與兒女,民族之間早已是兄弟。在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珍惜愛護我們賴以生存發展的民族大家庭,珍惜愛護我們統一強盛的社會主義祖國,及其不可分裂、不可玷污、不可侵犯的神圣,應當成為中華各族兒女不可顛覆的精神信仰和超越一切個體、局部利益的價值追求。(作者單位:求是雜志社)
注釋
①麥克斯·繆勒:《宗教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1頁。
②《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③《國朝宮史續編》,卷八九。
④《清高宗實錄》,卷一一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