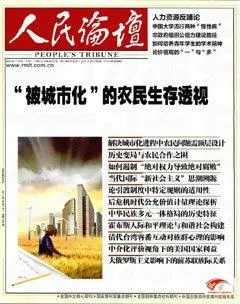中世紀歐洲城市與大學自治傳統關聯
【摘要】中世紀歐洲城市不僅是大學的誕生地,更是大學自治傳統的發源地。中世紀城市給大學自治傳統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大學自治的理念來源于城市自治的興起,組織形式參照城市中的行會制度,其自治模式取決于城市中的神權與王權勢力的差異對抗,大學自治特許權的重要內容是獲得城市居住權。
【關鍵詞】中世紀城市 中世紀大學 大學自治 城市自治 關聯考察
11世紀歐洲的大學是現代大學的雛形已成為高等教育史學界的共識,然而高等教育史學者們關注的是最早的大學為何偏偏就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產生。大量的具有地理意義的中世紀大學的名稱表明了大學與城市的密切關聯,也表明了這些城市必定是大學的誕生地。但更重要的是,中世紀城市不僅是中世紀大學的誕生地,更是中世紀大學自治傳統的發源地。換言之,中世紀大學自治的傳統正是根植于中世紀城市這塊得天獨厚的土壤。
大學自治的理念來源于城市自治的興起
自治的思想和制度在西方社會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自治的英文autonomy是古希臘語autos(自己)和nomos(法律)兩詞的結合。在古希臘思想中,這一術語適用于城邦,表示一種政治概念。古希臘社會的組織形式是自治的城邦國家,如果一個城邦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法律管理內部事務,城邦就擁有了自治權,因此城邦在本質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團體。從古希臘時期開始,西方社會就開始出現了由城邦向帝國的轉變,個人與國家、政府與社會開始疏離。中世紀后期,西歐多個民族、不同文明之間沖突與融合,形成了王權、神權和貴族權等多元權力并存、爭斗與妥協的獨特格局。這種特有的多元權力土壤,為城市的興起及城市自治權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所以歐洲中世紀“每個城市都是一個自治的市民社會。”①城市自治的標志是城市特許狀,現存最早的城市特許狀是967年的法蘭西城市特許狀。從公元11世紀開始,城市特許狀在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以及各低地國家被廣為效仿和傳播。
大學自治的核心是大學有權處理自身的內部事務,免受外力的干預,保障其自由地探求真理。中世紀的城市自治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封建領主的控制,又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領主。例如,中世紀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享有行政、司法、財政和軍事大權,制定自己的法律,依法選舉自己的城市議會,組建行會實行行業自治管理等等。中世紀城市的上述自治舉措對大學自治理念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大學自治的組織形式參照城市中的行會制度
10世紀到11世紀,歐洲封建制度進入鞏固和發展時期,農業生產開始出現穩步上升的趨勢,與農業有關的副業也日漸發達,同時手工業技術顯著提高,手工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進而成為專門的職業。經濟的發展使城市在歐洲大地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發展,有些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由農業轉向了商業和手工業。隨著商人群體財富和人數的增長,其日趨演化成為一個獨立于封建國家的常設機構自給自足的組織。商人組織還著手將從前絕對屬于主教、伯爵或封建國家代理人的政治、司法和軍事職責接管過來,組建成被稱之自治聯盟(commune)的機構。自治聯盟不僅是商人的聯盟,還被擴大為一個城鎮的所有居民的聯盟。在自治城市里,有權處理自己事務的各階層市民還將自治聯盟進一步發展,演變成可以用集體力量維護自己利益的組織——行會制度。
行會制度最早出現在10世紀的意大利,至12世紀遍及法、英、德等西歐國家。行會制度的興起,使得保護自身利益需要的學生或教師自發組織起來,成為城市眾多行會組織中的一員。對此,有學者作過如下深刻的闡述:由于11世紀至13世紀的許多學生是在其他國家接受他們自己國家所沒有提供的教育,就是這種表面上不重要的差別,導致了大學的興起。這一觀點還可以從大學的稱謂universitas中得到證實。13世紀文本中,universitas是一個抽象的古拉丁詞,意為“整體的”和“全部的”,中世紀的法學家初期使用universitas指稱各種各樣的行會,后來逐漸固定用于大學的稱謂。大學的行會特性暗含著大學既是一個組織集體,也是一個精神實體,它能夠以法人名義參與民事行為,自行訂立組織章程并強迫內部成員服從。
大學自治的模式取決于城市中的神權與王權勢力的差異對抗
中世紀大學是在教會勢力與世俗勢力兩元并存的環境中誕生的,大學要獲得自治權既要反抗教會神權,也要對抗世俗王權對大學的干預。在不同的大學內部,由于學生年齡和閱歷的不同,教師和學生兩者之間的權利也不完全對等。正是由于這種復雜的內、外部環境的差異,形成了中世紀大學兩種不同的自治模式:巴黎大學的“教師型自治”和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型自治”。
早在巴黎大學誕生之前,巴黎就以神學的名聲享譽天下,在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周圍建立了眾多的從事神學研究的主教學校,巴黎大學也是由當地的主教學校發展而成的。巴黎大學的成立更是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知識分子,使巴黎成為神學的學術研究中心和基督教的精神首都。因此,巴黎的神學勢力遠大于世俗勢力。巴黎大學爭取自治權的斗爭主要是反對教會對辦學權的壟斷,特別是教會司法官對大學任意干涉的權力。發生在1200年和1229年的學生與市民之間的沖突和流血事件見證了教、俗兩種勢力對巴黎大學的干預。由于巴黎大學學生年齡很小,沒有能力管理大學事務,教師在斗爭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教師也在與教會司法官的斗爭中不斷擴大權利,特別是1231年教皇格雷高利九世頒布的Parens Scientiarum法令進一步限制了司法官的權力,規定教師有權用停課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權利和制定教師協會章程,并且有強迫成員尊重和遵守章程的權利。這樣巴黎大學的教師就掌握了學術準則的制定權和學術許可權,從而使“教師自治”模式最終形成。
與巴黎不同,博洛尼亞是個典型的工商城邦,世俗的權力遠高于教會的勢力。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大多年齡較大,有較強的自治能力,教師由于經濟依賴學生,處于從屬性地位更強化了學生對大學內部的管理權,學生就在與世俗權力的斗爭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就不能享有博洛尼亞市的公民權問題與市政當局展開長時間的斗爭。迫于學生的強大壓力和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博洛尼亞市政當局最終妥協并認可了學生所提出的大部分自治要求,這樣學生取得了對外的自治權,博洛尼亞大學的“學生自治”模式得以形成。
大學自治特許權的重要內容是獲得城市居住權
中世紀是一個充滿特許權的社會,既有封建主、僧侶所享有的特許權,也有城市等社團享有的特許權。所以,大學為了爭取自己的法律地位來保證其生存和發展,其斗爭的最終目標就是獲得特許權。從現有史料看,中世紀大學的特許權主要有三個來源:教皇的訓令、皇帝和國王的敕令、大學特許狀。由于中世紀教會與王權的爭斗始終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大學的特許權也是變動不居的,但獲得所在城市的居住權是大學自治特許權的重要內容。
居住權是大學師生教學和學習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條件,因此獲得所在城市的居住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世紀大學的師生們經常來往于各大學之間講課和求學,不但旅途充滿艱險,而且師生們開始不能享受大學所在城市的居住權。通過斗爭,腓特烈一世的《完全居住法》最早賦予了前往博洛尼亞求學學生的居住權:“他們……可以平安地到學習的地方并安全地居住在那里……保護他們免受任何傷害。”②
值得指出的是,大學所取得的居住權不但賦予師生們基本的公民權利和人身保護,同時還包含了一些普通公民享受不到的優待。博洛尼亞市政當局規定在房屋的租金上,師生們的房屋租金是固定的,由選舉產生的兩名市民和兩名大學師生組成的四人評估團每年一次加以確定。如果師生們住所的租金超過了上述評估團設定的價格,他們可以不必再居住在那里,而那些收取高額租金的房主則要受到相應懲罰。③除了提供房屋和固定租金的優待之外,如果師生們的住所遭到偷竊,可以得到賠償;師生們還擁有可以免受噪音、惡劣氣味等騷擾的學習安寧權。例如,博洛尼亞市政當局規定任何人不得在學校周圍或者學者們的住所周圍經營手工業,因為這可能會干擾教學和學習活動,違反規定者將受到處罰。因此,城市居住權不僅保證大學師生們的人身安全,還保障大學的教學和學習活動可以不受干擾地進行。(作者分別為江蘇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蘇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2009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完善我國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法治思考》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號:09SJD820006)
注釋
①[美]湯普遜:《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74頁。
②[美]E·P·克伯雷:《外國教育史料》,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69頁。
③Pearl 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