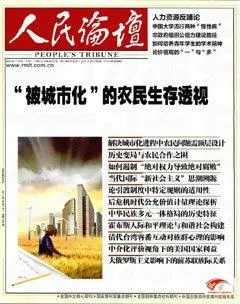兩漢時期貴州民族政策研究綜述
【摘要】兩漢時期是我國民族政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而貴州的民族政策是兩漢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于中央政府處理與貴州民族地區的關系至關重要。目前國內學者對這一內容的研究主要有二:從政治建制、經濟開發、文化影響等角度研究當時中央對貴州的經營;不同時期不同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傾向不同。
【關鍵詞】兩漢時期 中央政府 貴州 民族政策 文獻
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為處理民族關系而制定的方針,它對于多民族國家中各民族關系的健康發展有著極大的作用。兩漢時期是我國民族政策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是史學界研究的重點。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聚集區,貴州的民族政策是兩漢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于中央政府處理與貴州民族地區的關系至關重要,對于今天我國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由于地緣因素,貴州歷史上留下許多“空白處”,古代文獻中有關貴州歷史的記載少之又少,因此,相對其他地區,專門論及貴州的專著、論文較為缺乏,特別是專題研討兩漢時期中央政府對貴州民族政策的成果更為稀少。本文僅就所能查閱到的相關論述作一綜述,旨在為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許參考。
兩漢時期貴州民族政策研究概況
兩漢時期中央政府對貴州的經營。目前學界所關注的兩漢時期中央政府對貴州的經營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建制、經濟上的開發和文化上的影響三個方面。
首先,關于政治上的建制。《貴州通史》(貴州通史編委會,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西漢初年,即從漢高祖至漢景帝這七十余年,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所以在政治上基本無所作為。政治上的大規模建制始于漢武帝。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30年,漢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修“南夷道”,之后漢政府在貴州先后設立鍵為、牂牁二郡,貴州地區正式納入中央統一的行政建制。西漢成帝時,夜郎王反叛被滅,從此夜郎地區直接納入郡縣制體制。王莽時期,改牂牁郡為同亭郡,東漢建立后仍恢復原郡名,重建在牂牁的統治。上述事實,木芹在他的《兩漢民族關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做了詳細敘述。除此之外,木芹還從漢族的內聚力和少數民族的內向力這一角度論述了中央政府政治建制成功的原因。侯紹莊等著的《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專門敘述了漢武帝時期對“西南夷”的開發和設置,并談及兩漢時期中央政府在貴州建制上的特點,一是郡縣的劃分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團及所屬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圍,并適當照顧經濟區域的原則來劃分,二是郡國并存、土流并治。其他如王文光等的《中國西南民族關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尤中的《中國西南民族史》(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對此內容也有涉及。
其次,關于經濟上的開發。《貴州通史》以大量的考古資料說明了漢政府的經濟政策對貴州社會經濟的巨大促進,書中指出:漢初,中央政府雖與貴州地區無官方經濟往來,但民間經濟交流并未斷絕。漢武帝時期,隨著政治上的建制,中央政府也加大了經濟上的開發力度,其主要措施是“募豪民,田南夷”。稅收方面異于內地,僅以貢賦的形式向地方王侯象征性地征收少量地方特產,此政策持續到王莽時期,所以這一時期貴州地區雖有反抗中央政府的行為,但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壓迫和民族歧視所致,而非經濟剝削。東漢時期中央政府曾一度企圖按內地標準對貴州地區征收賦稅,遭到反抗,遂仍沿襲西漢時的政策。《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一書明確指出漢族移民對貴州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西南民族關系史》則從漢族經濟對貴州社會經濟的影響,如鐵制工具的傳入使用、鐵礦的開采等角度來談中央政府對貴州經濟上的經營成效。
第三,關于文化上的影響。《中國西南民族史》一書認為,漢武帝時,隨著中央政府在貴州政治、經濟影響的提高,漢文化已逐漸為“夷”族所接受,其典型代表為舍人和盛覽。東漢時期接受漢文化的人逐漸增多,層次也有提高,其典型代表是尹珍。《貴州通史》指出,東漢是貴州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伴隨著貴州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儒家思想學說也開始傳入,出現了一些熟悉儒家經典的人物,代表性人物也是尹珍。而范同壽的《貴州歷史筆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則對漢三賢中的舍人和盛覽是否真有其人、籍貫是否在貴州提出了質疑。藍勇《西南文化地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認為兩漢時期整個西南地區就是移民文化,移民主要有屯戶、官吏、士兵、罪犯、商賈等。
兩漢時期的貴州民族政策。分兩種方式論述:
第一,整體上論述。胡邵華的《中國南方民族歷史文化探索·中國西南民族史概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認為兩漢時期在西南地區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統稱為初郡政策,包括六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二是對民族首領“厚賜繒帛”,以此拉攏,三是“無賦稅”,四是移民屯田,五是選派廉潔官吏,六是幫助各民族發展生產和文化教育。胡邵華在其《淺析漢朝初郡政策的歷史作用》一文中再次強調了上述觀點。《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提法則不同,它認為兩漢時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的政策政治上是“羈縻”,經濟上是移民墾殖。政治上“羈縻”的實施范圍有個從小到大、不斷擴大的過程:西漢時實施范圍局限于生產相對發達、產生階級分化的地區,對于生產相對落后的地區還不能有效地統治;而到了東漢,整個貴州甚至西南都已在“羈縻”政策的實施范圍內。關于移民墾殖這一經濟政策,書中指出其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漢移民是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實行“羈縻”的可靠支柱。
第二,分階段說明。李正周的《兩漢時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從三個方面,即西漢時期、王莽時期、東漢時期論述了中央政府對西南夷的民族政策:西漢時期漢武帝在位時的民族政策,包括厚賄、武力統一、以故俗治、開通道路等;王莽攝政時的收買政策,即位后采取的降低封號的民族歧視政策;東漢時期的以德化為主、輔以武力,具體包括以夷制夷政策、廉吏政策、征收賦稅政策、武力討伐政策等。該文內容翔實,論述全面,但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缺少制定這些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論依據;其二,某些方面史料說服力不夠。孫長忠的《試論漢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一文著重論述了漢武帝時期的西南民族政策,他明確提出當時實行的是開明的民族政策,論述內容更加翔實,除開通道路、以故俗治兩方面與李正周提法一樣外,還論及了派遣和平使者談判,設置郡縣加強管理,實行“無賦稅”的經濟政策,募民屯墾等內容。關于王莽時期的西南民族政策,湯奪先《試論新莽時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認為只有一點,即民族歧視,包括降王為侯的貶黜政策和軍事打擊的強硬政策。陳金鳳《漢光武帝民族政策論略》一文分析了光武帝在“柔和”指導思想下,針對不同少數民族實施的不同民族政策,對“西南夷”,光武帝認為它屬于中原政權的管轄之下,所以對該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政權內部問題,采用比較穩定的控制措施。陳金鳳的另外一篇文章《東漢明帝民族政策論析》(《貴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認為漢明帝時期的民族政策傾向于同西南加強政治聯系。
從其他角度論述貴州在兩漢時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有:谷口房男的《漢六朝時期的民族官印與民族關系》(《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認為現存的漢六朝時期的民族官印是中央政府對南方少數民族實行有效統治的證明,從側面反映了該時期的民族觀和民族政策;張峻的《論秦漢時期的民族遷徙》(《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則論述了這一時期民族遷徙的狀況、特點和意義,而向西南地區的遷徙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該時期西南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
兩漢時期貴州民族政策研究特點
綜上分析,無論是專著還是論文對兩漢時期貴州民族政策的研究有以下特點或者說不足:
相關研究少,對貴州民族政策的專題性研究則更少。對其論述主要散見于對“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或是對該時期整個民族政策的研究中。這一特點無論是在講述開拓經營的事實或在分析具體的民族政策中都有所體現。如專著中的《兩漢民族關系史》、《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中國西南民族關系史》、《中國南方民族歷史文化探索》,論文中《淺析漢朝初郡政策的歷史作用》、《兩漢時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試論漢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試論新莽時期的民族政策》、《漢光武帝民族政策論略》等都是將其放在“西南夷”這一大的框架范圍內,而鮮有單獨就中央政府對“西南夷”民族政策進行論述的。這就使得,這一時期中央政府對貴州民族政策的研究呈現出分散性的特點,缺少系統性和完整性。
理論性不強。民族政策的制定背后是民族觀,它是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關于民族觀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在上述有關貴州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較多談及的是該時期的民族政策,對其背后的民族思想較少涉及。如李正周的《兩漢時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內容翔實,論述也比較全面,但關于這些民族政策制定的思想理論依據不足。類似不足在其他專著和論文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就使得民族政策的研究缺乏理論上的深度和說服性,也是值得學者們思考的地方。(作者單位:遵義師范學院歷史系;本文系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成果,項目編號:10ZC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