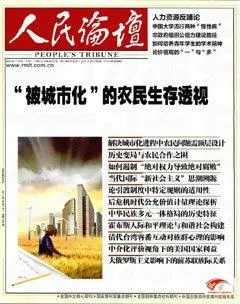孔子的人倫觀及其施報(bào)平衡原則
【摘要】孔子的人倫思想涉及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種人際關(guān)系,孔子的人倫思想就是對這五種人際關(guān)系應(yīng)該如何的道德規(guī)范的闡釋。孔子的人倫思想中始終有一種施報(bào)平衡的原則貫穿其中。這種施報(bào)平衡原則是我國自原始社會到春秋時(shí)代的人際關(guān)系與國際關(guān)系慣例。孔子主張從自己開始主動建立和諧的施報(bào)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孔子 君臣倫理觀 家庭倫理觀 朋友倫理觀 施報(bào)平衡
孔子的人倫思想所涉及到的人際關(guān)系有五種,《中庸》對此有過精辟的概括:“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孔子的人倫思想就是對這五種人際關(guān)系應(yīng)該如何的道德規(guī)范的闡釋。
孔子的君臣倫理觀
如果說可以對孔子的君臣觀一言以蔽之的話,那就是《論語·顏淵》中所載之“君君臣臣”一語。也就是說,君要像個(gè)君的樣子,臣要像個(gè)臣的樣子。那么,在孔子看來,什么樣的君臣才能算得上像樣子呢?概而言之,為君者應(yīng)該“使臣以禮”,為臣者應(yīng)該“事君以忠”。
為君者使臣以禮有哪些具體表現(xiàn)呢?孔子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八佾》)這里孔子間接道出了君主守禮的一般要求,即為君者要對待臣下寬厚,禮敬臣下并起模范帶頭作用。作為臣下,相對的“忠”也有具體的要求。那就是孔子所說的“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說首先要不辭辛苦,勤勞國事。具體表現(xiàn)在面對君主的垂詢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要做到“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即要敢于直諫犯上。其次,要嚴(yán)守君臣之禮,充分尊重君主。在這方面孔子用實(shí)際行動做出了榜樣。《論語·鄉(xiāng)黨》載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踢腥,必熟而薦之。君踢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飯。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由此可見,孔子很重視這些偏重于形式的君臣之禮,而且自己在這些方面也做出了表率。以上兩點(diǎn)就是孔子用自己的言行對忠君所要求的“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最有力的詮釋。
孔子的家庭倫理觀
在家庭倫理方面,父子之間的倫理關(guān)系是孔子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孔子將孝道視為調(diào)節(jié)父子關(guān)系的重要道德規(guī)范。孔子在不同場合和不同語境下列舉了孝養(yǎng)父母的道德行為。首先要奉養(yǎng)父母自不待言。其次,對父母的意志不可違逆。《論語·里仁》載:“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就是說,即使父母的意見有所欠妥,可以適當(dāng)勸諫。但如果父母仍不聽從,也要“勞而無怨”的依父母意志行事。所以,當(dāng)孟懿子問孝時(shí),孔子給出了簡潔的回答:“無違”(《論語·為政》)。此外,孝行還表現(xiàn)在“父母在,不遠(yuǎn)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意思是說,父母在世的時(shí)候,不出遠(yuǎn)門去求學(xué)、做官,萬一要出遠(yuǎn)門,必須有一定的去處。能從言行上表現(xiàn)出孝行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孔子看來,光有孝行還不夠,子女對父母還必須有孝心。如孔子所言:“今之孝者,是謂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是將崇敬之心作為孝行的內(nèi)在依據(jù)和動力來看的,并將其視為人之“養(yǎng)”與動物之“養(yǎng)”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
那么,崇敬之心從哪里來呢?崇敬之心只能將心比心,從父母對子女無私的仁愛中體察出來。《論語·為政》中,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朱子注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帷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jǐn)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獨(dú)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①朱熹對“父母唯其疾之憂”給出了兩種注解:第一種認(rèn)為,為人子者應(yīng)該體會到父母唯恐子女身體生病的無微不至的關(guān)愛,保證身體健康以消除父母之憂也是孝的表現(xiàn)。第二種注釋認(rèn)為,如果疾病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偷盜以致犯上作亂而招致的殺身之禍卻是人為可以避免的。朱熹的第二種注釋可與孔子“其為人也孝悌,而犯上者,鮮矣!”(《論語·學(xué)而》)之論互為印證,所以更合乎孔子的真意。總而言之,孔子所認(rèn)為的孝道不僅僅要求子女從物質(zhì)上贍養(yǎng)父母,而且更重要的還要滿足父母精神上的需要。這就要求子女首先不能違逆父母的意志,其次還要減少父母的為己的擔(dān)憂之心。
在孔子的父子倫理思想中我們似乎只看到了子對父單方面的道德要求,是不是父對子就沒有任何道德規(guī)范的要求呢?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論語當(dāng)中孔子對其弟子宰我的一翻評價(jià)從側(cè)面給出了否定性的答案。《論語·陽貨》載:“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宰我認(rèn)為為父母守喪三年時(shí)間太長。而孔子堅(jiān)持認(rèn)為,“予(宰我)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所以宰我也應(yīng)該守喪三年以報(bào)父母之恩。這里孔子給出了為人子應(yīng)該對父母盡孝的道德義務(wù)的理由,即父母養(yǎng)育子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所以子女應(yīng)該盡心竭力的孝養(yǎng)和禮敬父母。孔子這里也暗含著在調(diào)節(jié)父子關(guān)系中對父親一方的道德義務(wù),也就是說父親有愛自己的子女、撫育他們成長的義務(wù)。
與父子關(guān)系相比,孔子對兄弟關(guān)系的談?wù)摼捅容^少。他只是要求弟事兄以“悌”。《說文解字》將“悌”釋為“善兄弟也”。《四書章句集注》則認(rèn)為,“悌”僅指“善事兄長”。賈誼在《道術(shù)》中進(jìn)一步將“悌”釋為“弟愛兄謂之悌”。由此可看出,“悌”就是要求弟對兄要有親愛之心。雖然孔子并沒有提到兄長的道德義務(wù),但那并不說明孔子認(rèn)為只有弟對兄道德義務(wù),而是如同父對子的道德義務(wù)一樣是一種不言而喻的省略。此外,雖然孔子直接談?wù)摲蚱揸P(guān)系的言論無法征諸史料,但從基本承襲孔子思想的思孟一派的觀點(diǎn)中仍能看出端倪。孟子將孔子五倫關(guān)系中的夫妻關(guān)系闡發(fā)為“夫義婦順”的觀點(diǎn)相信違孔道不遠(yuǎn)。
孔子的朋友倫理觀
除了君臣關(guān)系和家庭關(guān)系外,孔子對朋友關(guān)系也給予了比較大的關(guān)注。《論語·學(xué)而》載:“子曰:‘學(xué)而時(shí)習(xí)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yuǎn)方來,不亦悅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孔子認(rèn)為,要維護(hù)保持良好的朋友關(guān)系就要求朋友之間要以“信”相交。可以說,“信”德是孔子用來調(diào)節(jié)朋友關(guān)系的最重要道德規(guī)范。深諳孔子之道的曾子曾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xué)而》)孔子本人也曾將“朋友信之”(《論語·公冶長》)作為自己人生志向之一。“信”字在《論語》中出現(xiàn)了三十八次。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本的論語詞典中,將“信”的字義歸為四大類:誠實(shí)不欺(24次);相信,認(rèn)為可靠(l1次);使相信,使信任(l次);形容詞或副詞,真,誠(2次)。概而言之:楊先生關(guān)于“信”的四種意義亦可被視為兩大類:其一是從心里真誠的信任別人,其二是用實(shí)際行動取信于人。一種意義偏于心理活動,一種則重在實(shí)際行動。所以孔子的朋友觀重在心行合一,朋友之間當(dāng)以交心為前提,這也許是孔子將“友直”作為益友的首要標(biāo)準(zhǔn)的原因。其次,這種傾心相交之情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落實(shí)到行動中,以此來取得朋友的信任。這與孔子仁內(nèi)禮外的致思方式是一以貫之的。
孔子人倫觀中的施報(bào)平衡原則
綜合觀之,孔子的人倫思想中始終有一種施報(bào)平衡的原則貫穿其中。孔子重視對等施報(bào)的思想在論語中也有明證。《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bào)怨,何如?’子曰:‘何以報(bào)德?以直報(bào)怨,以德報(bào)德。’”所以在孔子的人倫觀中,父慈子孝、君節(jié)臣忠、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都是人倫關(guān)系的雙方對等而言,雙方的道德義務(wù)是雙向的,是一種“投我以木瓜,報(bào)之以瓊琚”的關(guān)系。這種思想后來亦被孟子所承襲,從孟子“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樣論及君臣關(guān)系的言論中我們?nèi)匀豢汕逦吹竭@種施報(bào)平衡原則的影子。
事實(shí)上,這種施報(bào)平衡原則是我國自原始社會到春秋時(shí)代的人際關(guān)系與國際關(guān)系慣例。《禮記·曲禮》所載之“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就是對這種人際關(guān)系原則的高度概括。據(jù)楊向奎先生的研究,在我國的古禮中一直存在被稱為“全面饋贈制”的禮儀活動。“在原始社會中,禮是商業(yè)性質(zhì)的交往,互通有無,有贈有報(bào),有往有來,這就是‘禮尚往來’的適當(dāng)箋注。”②可以看出,孔子保留了這一中國古禮的精神內(nèi)核并在他的人倫觀中體現(xiàn)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固然強(qiáng)調(diào)道德義務(wù)施報(bào)的雙向性,但主張從自己開始主動建立這種和諧的施報(bào)關(guān)系,而不是被動的報(bào)答別人的施與,而是要“反求諸己”,而不是“求諸人”。也就是說,欲正人必先正己。事實(shí)上,孔子的人倫觀是他的“忠恕之道”的具體體現(xiàn)。無論是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還是忠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其落腳點(diǎn)都在己方,強(qiáng)調(diào)己方履行道德義務(w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認(rèn)為人“性相近”的孔子相信,只要付出總會得到回報(bào)的,天下沒有不可教化之人,只要正己最終必能正人。這與佛家“打完左臉,再伸出右臉讓人打”的度人方式頗有些相似,這也許就是儒釋最終走向通融的一道暗門吧。(作者單位: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政治學(xué)院)
注釋
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43頁。
②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7~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