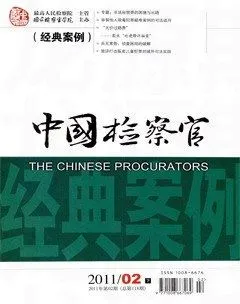印證證明模式在實踐中的運用探析
對于刑事證明的方法,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該條款雖然規定比較抽象,但在實踐中被運用廣泛,一般理解為“孤證不能定案”,即證據之間相互印證才能定案,由此確定的證明模式即為印證證明模式,印證證明模式是刑事司法人員判斷證據和案件事實的一條重要的經驗法則。下文結合實踐案例對印證證明模式的運用作簡要論述。
[案例一]2009年4月17日,被害人石某報案稱4月16日晚上被一蒙面人搶劫手機及現金,后公安機關通過手機信號追蹤到犯罪嫌疑人陳某。經訊問,陳某詳細地供述了搶劫被害人石某的過程,與被害人陳述大致相符:陳某還詳細描述了作案現場,與現場勘驗、檢查筆錄相符。案件移送起訴時,陳某翻供稱未實施搶劫,手機系他人賣給自己的,并稱以前供述是在被刑訊情況下所作。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趙某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駕駛吉普車流竄作案。2009年6月10日凌晨,兩人在盜竊一面包車時,被公安民警當場發現。趙某被當場抓獲歸案,另一犯罪嫌疑人逃離現場。據趙某供述,在逃犯罪嫌疑人為李某,與趙某是同鄉。此外,公安機關還從作案工具吉普車上扣押到李某的身份證及駕駛證各一份,與趙某供述相符。經查,該吉普車也是趙某等人盜竊所得,并非李某所有。
[案例三]2008年11月6日晚,行人劉某被撞死在城區道路。公安機關出警后在離事故現場五公里的田地里找到了醉酒駕駛的翁某并扣押了該白色皮卡車。經訊問,翁某因醉酒不知自己是否發生交通事故;經調查,有兩名證人證實一白色皮卡車撞死劉某的事實,但未看清肇事司機及車牌;經鑒定,翁某駕駛的白色皮卡車前端燈光裝置損壞。
上述三個案例中的證據能否認定各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需要從三個方面審查分析。
一、刑事證明思維模式選擇——口供補強規則模式與印證證明模式
口供補強規則與印證證明同屬刑事證明的思維模式。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口供補強是指在口供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據之一,必須與其他證據一起,相互印證一致后。才能起到認定事實、確定被告人有罪的作用。印證證明模式是利用事物間相互印證的關系,借助這種相互印證關系。判斷某個證據的真偽和某個事實是否存在。案件事實發生后,證據和一定的案件事實,以及證據事實與證據事實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聯系。這樣。為判明一定證據的真偽及其是否具有證明力,就可以把該證據與其他有關的證據結合起來,考察它們之間能否相互證實或協調一致。該模式雖然在我國法律上無明文規定,但在實踐中廣泛運用,而且英美法系國家刑事證據法上的補強證據規則便是對證據相互印證最有力的肯定和強調。而補強證據規則本身就是為了防止錯誤認定案件事實或發生其他危險,法律規定在運用某些證明力顯然薄弱的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必須有其他證據補充說明其證明力的一項證據制度。由此可知,印證證明模式與補強證據規則在思維方式上存在一致性。若對上述三案例用口供補強規則進行分析,案例一存在口供,可以適用;而案例二及案例三并沒有犯罪嫌疑人口供,無法適用。
口供補強規則的局限性表現在法律依據上是《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部分內容,即:“對一切案件的判處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但是對于該條款后部分內容卻沒有正確表達。其局限性表現在司法實踐中是片面強調口供的重要性,忽視口供以外證據的收集,導致刑訊逼供、誘供等非法取證現象的增多。相較而言,印證證明模式并不將證據類型限制在口供,而是擴展至可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全面地反映了《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含義,對沒有口供,但有其他證據證實的也可以認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33條規定:“間接證據可以相互印證的,也可以認定。”因此,對刑事證據分析不宜用口供補強規則,適宜采用印證證明模式。
二、印證證明模式價值定位——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但由于在案件的偵查、審查各個階段,案件的承辦方均承擔了完全的舉證責任,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一旦出現證據不足的情況,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作無罪處理。因此,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在辦案中難免陷入重有罪證據輕無罪證據的誤區。例如,在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情形時,若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確實的證據,則往往認為純屬狡辯,不予采信也不予調查。《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8條規定:“對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應當著重審查與同案犯的供述和辯解以及其他證據能否相互印證,有無矛盾。”因此在運用證據印證模式時,不僅應對證明有罪的證據是否達到印證標準進行綜合分析,而且還應對證明無罪的證據是否達到印證標準進行分析判斷,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如在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陳某在公訴階段翻供。我們就應當仔細審查其翻供的理由,并調查其他相關證據如訊問的錄像、進入看守所的體檢情況或其同監號人員的證言等,審查陳某的辯解與其他證據之間能否印證,以達到排除矛盾、查明真相的目的。印證證明模式將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同等看待、分別審查的價值定位對于端正執法理念、應對犯罪嫌疑人翻供、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印證證明模式證明力判斷——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
證據的證明力,是指證據對待證事實的證明作用,單個證據證明力的大小體現在與待證事實關聯性的大小,而多個證據組合的證明力大小一般體現在證據之間的聯系。印證證明模式作為一種證據規則,其主要作用就是將具有證明力的各單一證據聯系起來,使之形成具有證明力的證據組合,達到證明待證事實的目的。單個證據的證明力大小,按關聯性大小不同,可以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直接證據是可以直接證明犯罪行為是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為,證明力較強;而間接證據則必須與其他證據結合才能證明是否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為,證明力較弱。
印證證明模式一般先以證明力較強的直接證據作為主要證據,然后再分析其他證明力較弱的證據能否與主要證據相互印證,從而達到證明案件事實的目的。如在案例一中陳某的供述系直接證據,而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被搶手機、被害人陳述為間接證據,則應先假定陳某的供述為真,再審查勘驗、檢查筆錄及手機、被害人陳述等證據在細節上能否與供述相印證。案例二中同案犯罪嫌疑人趙某供述為證明盜竊是否李某所為的直接證據,現場扣押的李某身份證及駕駛證、被扣車輛為間接證據,則應先假定趙某供述為真,再審查身份證、駕駛證、被扣車輛的信息內容能否印證趙某供述,排除合理懷疑,達到證明結論的唯一性。案例三中對于交通肇事是否屬于翁某所為并沒有直接證據,但有看見肇事車輛(白色皮卡車)的兩名目擊證人、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出具的抓獲翁某經過及對翁某車輛的痕跡鑒定等間接證據。就單個證據證明力而言。目擊證人證言與待證事實的關聯性較強,則先假定肇事車輛即為翁某的白色皮卡車,再審查抓獲翁某的時間和地點情況及車輛有碰撞痕跡的情況,審查證據之間能否在細節上相互印證并得出唯一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印證證明模式對刑事證明司法實踐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們可以把印證證明模式的一般運用方式歸納為:首先對具有證據能力的單個證據進行審查,區分有罪證據與無罪證據后,對單個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審查,區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再審查有罪證據中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之間能否相互印證,接著審查無罪證據中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之間能否相互印證,最后綜合全案證據,審查最終結論是否具有唯一